吴靖
作为千年一遇的旷世奇才,苏轼在诗词、文赋、书法、绘画、政治等各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更难能可贵的是其人格的伟大。九百多年来,苏轼在政界、学界和民间的深远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林语堂先生在其享誉海内外的《苏东坡传》中将其称为“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我们可亲可爱可敬的东坡形象可谓跃然纸上。

苏轼画像
然而,没有“乌台诗案”的重大转折以及后续一系列的人生磨难,苏轼的人生境界和文学艺术境界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甚至可以说,苏轼的人生是从黄州开始的(东坡这个流传后世的名号也正是始于黄州时期),从这个著名的贬谪之地,真正成熟的苏轼开启了堪称辉煌的创作生涯(恰与其越来越艰难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在生命的最后一年(1101年),苏轼在经过真州(今江苏仪征)游览金山龙游寺时,看到李公麟所画苏轼像,回首命途多舛的一生,一时感慨万千,写下了著名的《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苦涩苍凉的诗句背后,却透露出理解苏轼人生和艺术的关键,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越贬越远的东坡没有被命运击垮,反而实现了政治人生和艺术人生的双重升华,最终成为了那个至今为人们口口相传的男神苏轼。
黄州:一蓑烟雨任平生
元丰二年(1079年),李定、舒亶、王珪等朝中群小合力编织了臭名昭著的“乌台诗案”(可谓中国古代政治生态的一个缩影)。尽管有“不得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有病中曹后“不须大赦天下,只放了苏轼就够了”的殷殷嘱咐,有王安石、张方平、范镇等一众老臣的上书营救,苏轼最终幸免于一死,但仍因莫须有的诗罪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其弟苏辙、其书信往来之友王诜、王巩、张方平、司马光、黄庭坚等20多人均受牵连被贬被罚,曾经风光无限的苏轼可谓一落千丈。然而,正是“乌台诗案”及黄州的苦难经历,让这个天真的乐天派诗人真正走向成熟,走向更加旷达豪迈的人生。
黄州是一座偏僻萧条的江边小镇,任何人走到这里都不免会产生一种被遗忘、被弃置的凄凉感。初到黄州的那些天,作为犯官的苏轼总是在白天睡上一整天,到晚上才敢一个人悄悄地出门,他以这种昼伏夜出的生活来慢慢修复心灵的巨大创伤。一天夜里,他不知不觉间走到了远离寓所定惠院的长江之畔,所见的残月、梳桐、冷夜、孤鸿、沙洲等纷纷化作一个个诗的意象,尤其是那只孤独而高傲的鸿雁,在苏轼心中引发深深的共鸣,它仿佛就是自己的化身:他的悲恨无人领会,他的高致无人欣赏,他的孤独无人理解。于是,一首满纸孤寂的《卜算子》从心头奔涌而出: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以创作为生命第一义的苏轼,如今却不敢轻易写诗作文,即便是写给朋友的书信也往往再三叮嘱“不须示人”、“看讫,火之”,唯恐“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更令人可悲的是,如雪花般纷纷寄出的信札,几乎都如泥牛入海一般,从此杳无音信。从前那些称兄道弟的“朋友”,如今已都作鸟兽散,除了黄庭坚、秦观等寥寥几位挚友外,谁愿意继续和一个差点被砍头的犯官为友呢!
然而,正是这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拯救了苏轼。自幼受到家庭佛教氛围熏习的苏轼,开始真正亲近佛教,试着在静观默照中反思这场人生灾祸。他不怨天,不尤人,而是从自身找原因。以佛学的观念来看,遭馋致毁是因自己屡犯“绮语戒”,“口业”太盛,而又固执己见。他痛切地认识到,“才华外露”是自己做人的一大毛病。由此,他对自己做了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答李端叔书》)这份沉痛恳切的反思,去除的是根植于一己荣辱得失之上的“骄气”,却依然保留着忘躯为国的“锐气”,一种大格局、大气象在这座千年小镇上慢慢酝酿和生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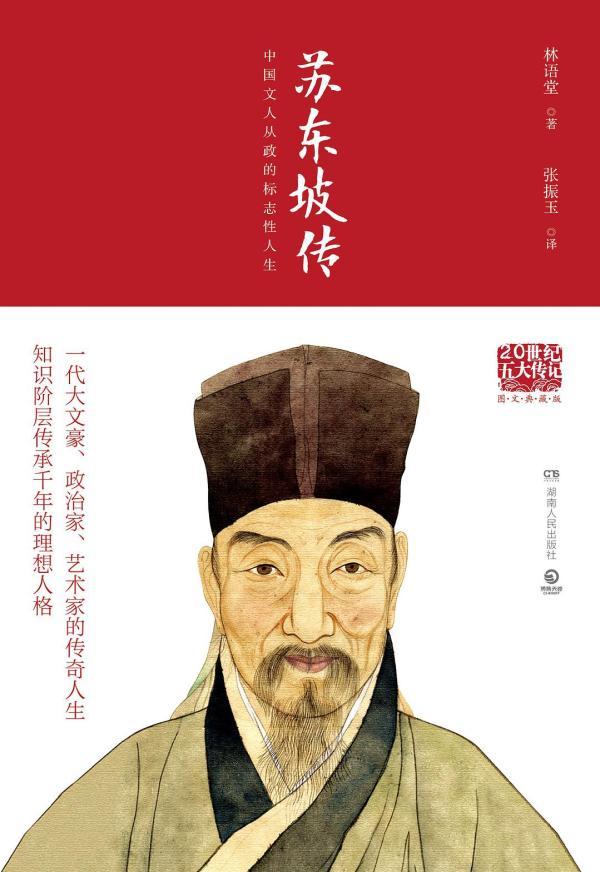
林语堂《苏东坡传》
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七日,苏轼在几位熟识的朋友陪同下前往相田(打算买田置产)。这日天朗气清,大家一边赶路,一边欣赏沿途的景致,没想到倏忽之间风云突变,一阵大雨即将倾盆而下,同行的朋友都觉得狼狈不堪,只有苏轼毫不介意。他仍旧脚穿草鞋,手持竹杖,和着雨打梳林的沙沙响声,一边吟唱,一边行路。不一会儿,雨过天晴。这场倏然而至却又倏然而去的大雨,让苏轼联想到了自己所经历的人生风雨,他将之高度艺术性地化作了这首传唱千古的不朽名作《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窃以为,《定风波》一词正是苏轼在经历大风大浪之后走向真正成熟的标志。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正如被放逐于海利根施塔特的贝多芬),苏轼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从此,正是这份成熟让苏轼在诗词、文赋、书画等各个领域大放异彩。于是,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诞生了,“天下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诞生了,一个迈向人生和艺术至境的坡神诞生了。
惠州:为谁合眼想平生
原以为黄州是苏轼的人生谷底,谁曾想到,更多的灾祸在等待着他。元祐九年(1094年)四月,哲宗下诏改年号为“绍圣”,意即继承神宗朝的施政方针。不久,吕大防、范纯仁罢职,章惇出任宰相大臣。这位重回庙堂的变法派大臣,完全抛弃了王安石新法的革新精神和具体政策,把打击“元祐党人”作为主要目标,尽情发泄多年来被排挤在外、投闲置散的怨愤,苏轼兄弟成为这场政治风暴的首要受害者。仿效“乌台诗案”的故技,朝中一帮小人网罗罪名,横加诬陷,苏轼再度开启贬谪生涯。即使在千里迢迢奔赴贬所的路上,小人们依然心有不甘,屡进谗言,朝廷竟五改谪命,最终将其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经过近半年的艰险跋涉,苏轼最终抵达了当时的南蛮之地——惠州。
两年多的岭南生涯在苏轼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时间并不长,但却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只因为一个人——朝云。绍圣三年(1096年)七月,苏轼的爱妾、一生的知己朝云病逝,年仅34岁。朝云的离去对于苏轼无疑是一个极为沉痛的打击,这位“无可救药的乐天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凄楚之境。自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通判杭州时进入苏家,二十三年间朝云一直跟随苏轼辗转南北,无论升陟贬黜,始终忠诚不二。随着苏轼的贬谪,曾经热闹的歌儿舞女们相继散去,只有朝云随他南迁,成为他悲惨的流放生涯中忠实的伴侣。即便到了瘴疠之地惠州,朝云毅然无怨无悔,泰然自若,精打细算地操持着一家人的生活,闲暇时便读书念经,习字临帖,与苏轼谈禅论道。
据说,朝云的生病和苏轼填的一首词有关。某日,贬居惠州的苏轼和朝云闲坐,正是秋凉时节,苏轼放下手中书卷,见窗外落木萧萧,凄然有悲秋之感,便请朝云演唱自己所填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词。朝云歌喉将转,泪满衣襟,苏轼惊而问之。朝云说:“奴所不能歌者,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二句,为之流泪。”自此,朝云常常若有所思,“日诵‘枝上柳绵’二句,为之流泪。病极,尤不释口。”显然,通晓禅理的朝云读出了词中的言外之意,“枝上”一句,乃无常之象,“天涯”一句,写普遍之意。两句形象地道出了人生无常——恰似苏轼一生的升降沉浮,忽北忽南。正所谓“霁月难逢,彩云易散”,朝云不久后抱疾而终,苏轼也终身不再听这首作品。
难能可贵的是,朝云不只是同甘共苦的伴侣,更是精神相契的知己。想当年,苏轼故意捧着酒足饭饱的肚子问众人:“你们可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一位婢女说“都是文章”,另一位婢女说“都是学问”,直至朝云答道“一肚子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如今,形单影只的东坡先生只能在惠州西湖边徘徊游荡,夕阳斜射的树林间寒鸦盘旋,寺院的晚钟与佛塔的铃语、瑟瑟的松吟相互应和,构成了如此凄迷的意境。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无不令人想起朝云,于是便有了《西江月·梅花》: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
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这首咏梅词,写岭外梅花玉骨冰姿,素面唇红。然而,晓云已散(喻朝云病故),苏轼不能像王昌龄梦见梨花云(雪景)那样做同一类的梦了。句句咏梅,却又字字怀人,于朦胧中寓深情,于哀婉处见幽致。其间之一往情深,不让东坡千古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千载之下,令人动容。

张充和《仕女图》
朝云死后,苏轼遵照其遗言,将她安葬在丰湖岸边栖禅院东南山坡上的松树林间。据苏轼所撰的碑铭记载:“(朝云)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以绝。”四句偈便是著名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因有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之语,又名“六如偈”。后来,寺院僧人在墓上修了一座亭子,取名“六如亭”,亭柱上镌有苏轼亲自撰写的一副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纵观苏轼曲折的一生,幸有几位于他有特殊意义的至亲女性:他的母亲程氏,他的两位夫人王弗、王闰之,朝云是身份更低但更为重要的一位。正所谓诗云:“四弦拔尽情难尽,意足无声胜有声。今古悲欢终了了,为谁合眼想平生。”(张充和《仕女图》题诗)
儋州:兹游奇绝冠平生
本想在惠州了此残生的苏轼万万没想到,另一个更加悲惨的厄运即将降临到自己身上。绍圣四年(1097年)又一个不祥的四月,惠州知州方子容怀着沉重的心情专程前来,并正式传达了朝廷的告命: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据说,朝中群小看了苏轼在惠州写的诗句,诸如“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等等,认为他在惠州还是生活的太舒服,应该贬到更远更蛮荒的地方,于是直接发配天涯海角。要知道,在北宋一代,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轻一等的处罚。
踏上海南岛,对长居大陆的苏轼而言,已没有过去那种“仿佛曾游”的神秘感觉。登高北望,视野所及,只有一片浩淼的海水,四顾茫然,一种异国他乡、永无归路的凄凉感袭上心头。海岛的生活相比黄州、惠州,可以说才是真正的艰难。这里地热海寒,林木阴翳,燥湿难耐,毒物遍布,被中原人士视为十去九不还的鬼门关。初来乍到的苏轼面对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更无书籍和笔墨纸张的艰难窘境,加之语言不通,简直是度日如年。但苏轼之所以是苏轼,就在于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非凡的自信和本领,生生将“地狱”变为“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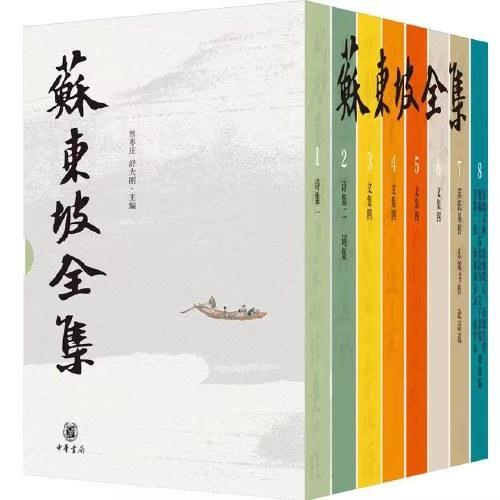
《苏东坡全集》
随着苏轼继续发挥他“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的随和宽容的人格魅力,他逐渐适应了黎民的风俗,也赢得了当地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关怀。尔后,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育学人,以致许多人竟不远千里,追至儋州拜于苏门。北宋一百多年时间里,海南从无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后不久,儋州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曾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至今,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儋州文化的播种人和开拓者,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
同时,这种返璞归真的散淡生活让苏轼迈向人生的更高境界,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陶渊明。对比其岭海前后的诗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超迈豪雄向淡雅高远的转变,正所谓“绚烂至极归于平淡”,艺术史所津津乐道的晚期风格(Late Style)在苏轼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其最显著的例证便是他一百多首“和陶诗”。在惠州、儋州两地,苏轼几乎和遍了所有陶诗。最后,他得出了这个著名的结论:
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
在此,陶渊明成了苏轼晚年打量自己的一面镜子,他承认自己的诗“不甚愧渊明”,但在人生境界上则“深愧渊明”,并表示“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事实上,苏轼和陶渊明两位异代大诗人可谓是相互成全,在陶渊明诗文复兴的漫长之路上,苏轼晚年的极力推崇可谓居功至伟,而在苏轼晚年遭遇一贬再贬的人生困境中,陶诗提供了充分的精神慰藉和美学滋养,对苏诗晚期风格的形成影响巨甚。
风烛残年之际,苏轼迎来了颇具反讽意味的命运反转。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初九,哲宗崩逝,徽宗继位,政局大变。神宗妻向氏以皇太后垂帘听政,形势向着有利于元祐臣僚的方向迅速发展。二月,便大赦天下。待到六月,苏轼终于要离开谪居三年之久的儋州,当地的土著朋友纷纷携酒带菜前来饯行,执手泣涕。在渡海的当晚,苏轼一夜无眠,看着天容海色,他联想起自己多舛的一生,尽管谤诲交加,但高风亮节终将长留天地,一时间诗思泉涌,不禁脱口吟道: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此际,他终于领悟了庄子齐得失、等荣辱的哲理,看透翻云覆雨的政坛变幻,就像孔子所感叹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尽管他已下决心归隐江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轼将出将入相的消息已传遍全国。这时,章惇之子章援惊恐焦虑万分,因为他父亲当年正是迫害苏轼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只能厚着脸皮,专门给苏轼去信替父亲求情(其时章惇已被贬雷州),担心苏轼回到朝廷后,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迈过耳顺之年的坡翁早已跳出了是非恩怨的小圈子,而以了悟人生的智者眼光与悲天悯人的仁者胸怀俯视一切人事。
收到章援来信时,苏轼已身染重病,却仍强支病体回书作答。他十分诚恳地写道:“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居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更说何益,唯论其未然者而已。”不仅如此,苏轼还将自作的《续养生论》一篇及行之有效的养生药方随信寄赠,希望他能借此颐养天年,熬过这人生一大劫难。就这样,苏轼一笔勾销了往日的恩怨,其胸怀是何等开阔,境界是何等高远!据史书记载,章家一直珍藏着这封感人至深的回信,几十年之后,还有人从章惇的孙子章洽那里看到。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在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享年65岁。一时间,举国震悼,山河同悲。苏轼走完了不平凡的一生,这位中国文化史上的罕见全才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文化遗产,包括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4200多篇散文,以及无数书画艺术杰作,人们将苏轼所创造的文化世界尊为“苏海”。更重要的是,苏轼巨大的人格魅力倾倒和影响了无数中国人,人们不仅欣羡他在事功世界中刚直不阿的风节、民胞物与的赤子之心,更景仰他心灵世界中洒脱飘逸的气度、笑看风云的超迈。这位将现实性与超越性完美交融的人生典范,永远令人追慕,惹人怀想,予人启迪。
责任编辑:臧继贤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