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在扎根现当代文学的青年批评家里,黄德海是知识结构和研究兴趣都相对特殊的一位。从2018年的《诗经消息》开始,他似乎对传统典籍越来越感兴趣。他觉得看到了古人在言辞中建立的精美教化系统,并且有维护这系统运转的严密方式,为此振奋不已。
经常有朋友问他:“古代真有你说得那么好?你是否有意无意间有所美化?”他相信自己没有美化,也会跟大家解释这一教化系统只是言辞中的城邦,并非既成事实,这一系统真正对世界起作用,还需要我们根据时代不断有所损益。
“解释虽然能解释,但我自己也不禁生起了怀疑的念头——这一言辞中如此精美的系统,在古代曾经起过作用吗,它在崎岖起伏的现实中会是什么样子?”念头一经产生,就怎么也停不下来。他受启发于金克木的《“古文新选”随想》,从先秦到汉代挑选出《檀弓》《赐南越王赵佗书》《轮台诏》及李斯文章精读,剖析它们连接的历史节点,猜想作者面对时代巨澜的心思,进而由文章探索世间复杂的人心与人生。在写作过程中,他一边对照历史,一边观察自己置身的现实,以此检验自己的所历、所学和所思。

《世间文章》
今年年初,这一批谈论与历史中的现实相关的文章结集成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它们牢牢生长在人世间,便以“世间文章”命名。《世间文章》引的是古文,观的是历史,可“现实”之思无处不在。按黄德海的话说,在某些时候,人们会试着把沉埋在历史深谷里一些熠熠生辉的东西打捞出来,让其重新焕发出动人的活力,参与现今的世界。
“所知和所见有限,我不敢说我是在研究历史,只是尝试着看到那条更广阔的河流,如果有可能小小疏通一下那些淤塞的部分,就更是意外之喜。”近日,黄德海就新作《世间文章》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或许于他而言,这些次写作带来了无数回味,他因此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黄德海,《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著有《诗经消息》《书到今生读已迟》《驯养生活》等。
【对话】
中国思想的特殊基因
澎湃新闻:金克木在《“古文新选”随想》中把李斯的《谏逐客书》、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唐太宗的《圣教序》、朱熹《孟子集注》的最后一段、曾国藩的《求阙斋记》、《文选·序》以及《汉书》中徐乐的《上皇帝书》放入他的“新选”,说这七篇文章“都包含着有中国特色的逻辑思想和文体”,且“秦,汉,六朝,唐,宋,清都有了”。
你这本《世间文章》受到金克木“古文新选”的启发,最后具体写到了《礼记·檀弓》、李斯的《谏逐客书》、汉武帝的《轮台诏》、汉文帝的《赐南越王赵佗书》。但你在后记里也说了,本来还想写诸葛亮的《出师表》、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唐太宗的《圣教序》、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曾国藩的《求阙斋记》等等,只是没来得及。算一算,这里面也不只七篇了。我好奇的是,如果非要你以七篇为上限,选出不同朝代里“包含着有中国特色的逻辑思想和文体”的文章,哪七篇会是你自己的“新选”?为什么?
黄德海:《世间文章》原本想把《“古文新选”随想》提到的七篇文章写一遍,看看金克木言之未尽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没想到,先是不知道怎么脑子里跳出了《檀弓》,读了之后,觉得看到了古人的某种深心,就先写了。然后就是原计划的《谏逐客书》,想从这篇文章看看渗透到民族血液里的开放心态,以及这心态背后的世俗考量。可刚刚分析到《谏逐客书》,关于李斯的部分就超过了预定的篇幅,就只好一边写一边调整结构,最终写了四篇。接下来准备《移让太常博士书》的时候,先注意到了《轮台诏》和《赐南越王赵佗书》,就沿着写下去了。写完这两篇,因为《移让太常博士书》涉及的问题太复杂,还需要结合这些年出土的竹简什么的一起考虑,很难在一篇文章里写清楚,只好暂时停下来,换了另外的篇目。其实金克木选这七篇的时候,有自己的针对性,也并非真的只有七篇,只是提出启发性的读书方式,因此我也就没有逼着自己非按这个选目写文章。
如果非要以七篇为限,不完全照金克木提示的思路,我暂时会想到的是,《春秋》首句及三传之释、《尚书·洪范》、《论语》开篇、《庄子·人间世》、范缜《神灭论》、张伯端《悟真篇·序》、皮锡瑞《经学通论·序》……之所以加了省略号,是因为要试着勾勒形成传统文化的经典篇目,然后要看传统文化在外来思想冲击之下如何选择和变化,又如何延伸到日常的思维之中,里面的起承转合太多,怎么选都免不了挂一漏万——每次选择都在遗憾之中。
澎湃新闻:你的“新选”和金克木的“新选”既有重合,又有不同。你会怎么理解你与老先生的同中之异?在你看来,中国思想的特殊基因是什么?中国文体的特殊形式有哪些?
黄德海:从前面的选目能看出来,金先生关心的是文章在具体历史中的效果,怎样起作用,怎样构成了民俗心态,怎样决定了中华思维的路向。相对来说,我更关心的是,一个思想是如何产生的,是虚拟的还是现实的,二者又是如何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开拓还是限制了思维的发展。其实这不同也并非完全不同,在某种意义上,两者可以结合。从这些文章看中国思想的特殊基因,或许可以说,是始终保持向上的可能,却也不脱离寻常日用。中国文体的特殊形式我说不好,金克木觉得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八股,并且有解释,非常精妙,有兴趣的可以看老先生的《八股新论》。

近日,“金克木三书”《明暗山——金克木谈古今》(黄德海编选)、《续断编——金克木述生平》(张定浩编选)、《梵佛间:金克木说印度》(木叶编选)由作家出版社推出。
给文本“做减法”,推测历史产生的各种可能
澎湃新闻:翻阅《世间文章》,我发现你在比较文本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比如谈到李斯和韩非的关系,你比对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韩世家》《战国策·秦五》的不同记载,撇除了所有可能附有情感色彩、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的情节,只留下各家史料公认的也是最不可能有错的三个基本事实:韩非是韩国贵族、“为韩不为秦”、使秦而死于秦,接着就各种可能性展开推论。这种“做减法”般逆流而上追本溯源的方法和历史文本“做加法”(文本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丰满)的方向恰好相反。你如何看待这两种方法的不同?
黄德海:说不上在比较文本方面下功夫,因为使用的只是基本材料,没有穷尽,也没有什么秘辛。“做减法”(老子所谓的“损之又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因为可以把最基本的叙事支点考察出来,从而推测写作者对这些叙事支点的逻辑串接,看出每个人不同的思路和主张。不过,考察的过程中也不得不注意,那些所谓的基本叙事支点,仍然有可能遭到有意无意的调整或轻微的改动。
相对来说,现在很多流行的所谓“非虚构”历史读物,做加法做得有点多了,把很多可能是记载中断的地方,凭借现代思维逻辑编排起来了。这样做的好处是故事讲得圆满,读起来跌宕起伏,缺点是把历史的各种可能变成了一种或少数可能。更何况,很多这类作品秉持着“现代正确”的思路,把古人已经探索出的更远可能变成了近视的标本,评价起来容易带有现代人的致命自负,从而把开阔的古书变成了狭窄的现代材料。
当然,对我来说,“做减法”只是一个理想,并不是说我就会做减法,或者做得够好了,而是应该恰当地看做一种尝试吧。
澎湃新闻:很多时候,你也没有在文中给出直接的结论或者简单的是非判断,你似乎更想进入历史的细节,呈现其复杂性与可能性,又或者说是打开某种思路,松动我们早已习惯的某些说法。在写这一系列文章的时候,你对自己提出了哪些希望与要求?
黄德海:我对自己的希望和要求,差不多就是你说的,“似乎更想进入历史的细节,呈现其复杂性与可能性,又或者说是打开某种思路,松动我们早已习惯的某些说法”——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个“似乎”(一笑)。如果要补充,我想说,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学习者,去学习那些文章,那些文章中精妙复杂的思考方式,进而去学习书中写到的那些开阔坚韧的心灵,从而有机会来反观自己,检查自己的狭隘和局限,如果有可能(幸运),就在具体情形里稍微调整。
澎湃新闻:你在这本书里也多次用到了“具体”这个词,比如:“要理解或回应首要经典中的问题,就需要尝试回到立法者当时面对的具体情境,看看他们企图引导、纠正和创制的究竟是什么。”[《慎终如始——<檀弓>试读(一)》]“一项政策的成败利弊,不能以固定的抽象标准来评价,恐怕得放在当时的具体之中才能更好地判断。”[《铜罐和陶罐——<轮台诏>的前前后后(上)》]……它们其实都在说:我们在阅读古典或回望历史时不要只纠缠于抽象的原则,而忘记了这些原则生长的环境,那些具体因应的繁复事实。由此推论,我们继承古人的学问、道理,似乎也更应该注重了解他们处理问题的背景,学习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而不仅仅是直接接受那些看似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论。这是否也体现了你历史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黄德海:所知和所见有限,我不敢说我是在研究历史,只是尝试着看到那条更广阔的河流,如果有可能小小疏通一下那些淤塞的部分,就更是意外之喜。具体到“具体”,就正是这个思路的一部分。就像章学诚说的,“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开端意义上的写作,其实是对具体之事的思考和安顿,并非要写得怎样才气纵横或风格卓著。书里引到《朱子读书法》中的一段话,或许可以相应章学诚的话,也可以相应我们谈到的具体:“今来学者(读书)一般是专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说得新奇,人说得不如我说得较好,此学者之大病。”括号里的“读书”改成“写作”,是不是也可以成立,甚至应该更成立一些?

黄德海从金克木生前约30部已出版著作中选出有关读书治学方法的文章50余篇,编成《书读完了》,该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切能被思考的东西,都同属于虚构的广阔河流
澎湃新闻:这本书最长的篇幅给了李斯。解读李斯,“时”是一个关键词,他给我的一种感觉是:成也“时”,败也“时”。读了文章,我也会猜想:你是否对李斯也存有个人的预期和设想?比如你认为司马迁上来就用“上蔡仓中庑下鼠”来打比方,这对李斯而言有点“不像样”。后来“行督责书”中间段落(让君王远离俭节仁义之人,谏说论理之臣等)出于李斯之口,在你看来也可谓“匪夷所思”。你个人更倾向于《史记》中有关李斯的记载(尤其是“沙丘之谋”之后的记载)是存疑的。
在实际研究中,“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其实是难的,最难的就是一旦先有假设,研究者很容易去找那些能够证实自己假设的材料。所以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你会不会也遇到这样的“难处”?如果遇到了,你怎么解决它?
黄德海:那一年在贵州梵净山下,带着李斯的文字辑录,反复看到其中提到“时”,觉得打开了一个理解他的角度,心下欢喜。后来看《傲骨贤妻》的衍生剧《傲战法庭》,里面提到爱因斯坦签证,忽然就想到《谏逐客书》,觉得或许可以写一篇跟李斯有关的文章,来看他的雄才大略如何一步一步施展。等到细读李斯的传记,按照人物格局和性格推测,觉得很多地方无法讲通,于是不得不推究每个说不通的细节,沿着司马迁的思路,看人物如何一点点变成了他呈现出来的样子。
写作中当然会不断遇到这样的难处,遇到了,无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只好尝试着像传记写作者那样去理解人物,寻找其中的细节和标志。比如传记上来先用了“上蔡仓中庑下鼠”的比方,可末尾的赞里,却说他“卒成帝业”“尊用”“知六艺之归”,反差极大。那就不免要揣测,《史记》开头是不是用了“责备贤者”的“春秋笔法”,司马迁写《史记》的志向是不是模拟《春秋》?这样跟着作者去思考,虽然岔路颇多,但其味无穷,是写作时最开心的时刻。
澎湃新闻:有学者认为《史记》开启了中国小说的传统,唐德刚曾说《史记》这样的史学著作实际上就是小说。作为文学评论家,你如何看待历史和文学的关系?你如何看待今天文学逐渐专业化的趋向?
黄德海:如果用史学和小说的概念来区分,我不敢说《史记》是小说源头甚至就是小说。如果把小说换成虚构,或许可以说,虚构正是人类思维方式的特征,或者也是人之为人的关键之一。不用说,文学与虚构几乎天然相关,“只要这部作品是艺术,它就不是现实的东西”。稍进一步,在历史研究中,“任何写作一个叙事的人都是在虚构”。甚而至于,我们不得不承认,“科学理论基础具有纯粹虚构的特征”。或者,“除非以虚构的方式,在我们的头脑中或其他任何地方,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被我们言说或被思考”。从这个方向理解,是不是可以说,历史和小说都是虚构,而历史和文学是某种特殊的共生关系?甚至,历史、哲学、文学和一切能被思考的东西,都同属于虚构的广阔河流?这样看,是不是可以推测,文学逐渐专业化的趋向,是把一条大河变成了小河,从而能够汲取的能量会越来越少?
澎湃新闻:我想,《世间文章》也提醒读者思考“历史、故事、事实”之间的关系:历史是一种叙述,一种文本,但没有一种叙述与文本是绝对真实与可靠的。更多时候,“它们只是一些故事,携带着每个讲述者对这世界不同的失望和期待,看破和困惑,善意和冷漠。”
比如说继承制,殷是“兄终弟及”,周是“父死子继”。在你看来,自周开始成为制度的父死子继制,极可能是殷代之后的大立法者(首要经典的书写者)截断众流的选择,而非本身是确定无疑的历史事实;又比如自《汉书》开始陈说的所谓汉武帝晚年之悔,逐渐在后来的陈述中成为类似“必须这么做”的象征性存在。在讲述与续写之外,有关历史的研究、评价,亦存在着后人对前人的“利用”与“创造”。你如何看待“历史的真实”与“诗的真实”或者说是历史的“真”与“善”之间的关系?
黄德海:关于“历史、故事、事实”之间的关系,已经有很多非常深入的讨论,认为历史写的就是真实的,大概早就有其局限了。如果追溯既往,早期的历史著作也并非所谓客观纪实,而是有着写作者自身的深深考量,甚至部分“创造”,比如希罗多德的《历史》(《原史》)和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书》)。当然,也不能就此把历史和故事完全混为一谈,在谈论时要小心翼翼地辨析其间的差别和可能的融合,否则可能进入一种古怪的虚无之路。
关于真与善以及美的关系,讨论的就更多了,而集中点则往往在三者的分离。徐梵澄曾经说,“诗之美者,命意必善”,也就是说,美和善可以不矛盾,甚至是必然在一起的。那是不是可以从此推导,真和善也是必然在一起的?很多时候三者不在一起,是不是有人垄断了真善美的解释权,或者出于写作者的无所用心或别有会心?还是那句话,不用急着规定抽象的真和善(或美),而是深入每一个具体,从这些具体里发现值得自己深思的东西。
“留在人世间”,古典能在今天焕发生机的关键
澎湃新闻:《世间文章》更特别的一点在于,它告诉我们某处史料记载即使有误,即使存在后人的“创造”,“有误”也有其合理性和意义,“创造”也因对人世深有益处而成就了其特殊之真,甚至于产生了改变未来的可能。是否可以说,我们读历史不仅要通过不同文本的互证,寻找出历史的基本骨架,也要注意那些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发展不断丰满出来的可能并不符合原始“真实”的“血肉”,它们或许更有意义,代表了人心或者说历史秩序与正义的部分?
黄德海:大概是属于现代人特有的骄傲,我们很容易觉得古人这里错了,那里不对。或许真的是这样吧,但我更喜欢校勘方面的一句话,“以不校校之”,不用动不动就想质疑和修改,而是先仔细琢磨这些问题的可能形态。在后记里我写了一句话,“写《诗经消息》的时候,我自认为看到了古人在言辞中建立的精美教化系统,并且有维护这系统运转的严密方式,为此振奋不已”。这本书的着力点则是,“这一言辞中如此精美的系统,在古代曾经起过作用吗,它在崎岖起伏的现实中会是什么样子?”试着把“言辞中建立的精美教化系统”换成“创造”,把“在崎岖起伏的现实中”的样子换成“真实的血肉”,我们是否或许可以说,不存在谁代表人心或说历史秩序与正义的部分,而是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与对这些事的反思与设想一起,构成了丰富的文献系统,可以让我们借此思考无比纷繁芜杂的现实和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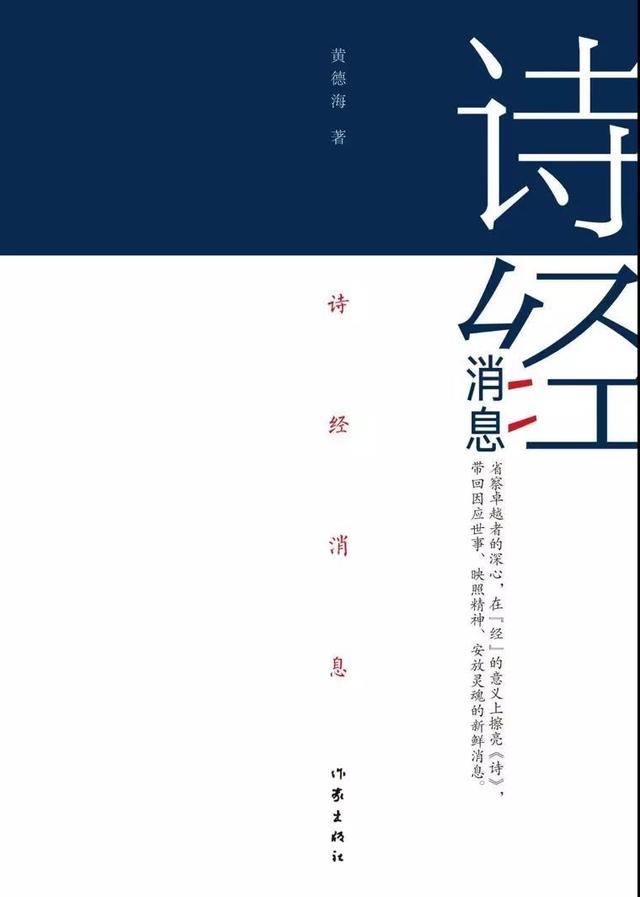
《诗经消息》
澎湃新闻:比如对于“坑儒”,你认为最终的文本形态,有可能是一个被后人不断附加出来的事件,但即便是“附加”,亦有其坚定不移的理由,“从而确切地告诉人们,有些事是绝无丝毫通融地‘不能这么做’!尽管无论如何都无法完全避免凶残之事的发生,但读书人无用的笔墨会在斧钺过处留下无法抹去的痕迹,让它一直作为禁忌留在人世间。如此,历史才不只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成为人群生存的基本条件,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看到“留在人世间”“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我觉得它仿佛回答了你在试读《檀弓》中留下的那个问题——“时至今日,中国古典还能面对西方哲人甚或更强大的挑战而焕发出新的生机吗?”再联想到你在书中提及的两位学者:一位是中国的金克木,“金克木从来不就古代论古代,就古书论古书,他关注的,始终是古代跟现在的相关度”。一位是美国的雅法,“雅法接续了西方古典的史学写作传统——不是以还原事实为目的,而是探究历史的至深根源,从而与现实的社会和人生建立起深切的关系”。我的感觉是,你想通过这本书,串起历史与现实的某些关联。你认为中国特殊思想基因在今天的表现是什么?古典能在今天焕发生机的关键是什么?
黄德海:有人曾问金克木怎么看传统,他反问:“你说传统是什么?”然后自问自答,“传统是指从古时一代又一代传到现代的文化传统。这个‘统’有种种形式的改变,但骨子里还是传下来的‘统’,而且不是属于个人的。比方说,甲骨占卜很古老了,早已断了,连卜辞的字都难认了,可是传下来的思想的‘统’没有断。抛出一枚硬币,看落下来朝上的面是什么,这不是烧龟甲看裂纹走向吗?人可以抛弃火把用电灯,但照明不变。你过去穿长袍马褂现在改穿西服仍旧是你。当然变了形象也有了区别,但仍有不变者在。这不能说是‘继承’。这是在变化中传下来的,不随任何个人意志决定要继承或抛弃的。”
这是不是说,断而未传的不能算传统,只有经过变化传下来的才算。所谓中国特殊的思想基因,大概也应作如是观。有却未传下来,没有在社会中起任何作用的,即使有,怎么算?要算,是不是也要从出现并起作用之后算?有而且经过变化之后传下来了,比如《谏逐客书》里的文化基因,现在是有还是没有了呢?因此,古典能在今天焕发生机的关键,其实就是通过现在的写作,把那些仍然能够参与世界思想(在现在的形势下,是不是可以包括AI?)竞争的基因,通过各种损益表达出来,看看还能否在现实世界里起作用。能,就是特殊的思想基因,不能,就不是(起码这个解说不是)。所以,基因是否能够传递,文化是否焕发生机,需要写作者探究历史的至深根源,并将之尽可能准确地表达出来。
澎湃新闻:从《诗经消息》到《世间文章》,能感到你一直努力在古典传统中汲取感悟与收获。你认为它们给了你哪些面对当下现实的能量?那些古典文献对于我们当下的世界与社会有怎样的启示?
黄德海:我具体的所得,给了我某些切实的安顿,大部分写进书里了,不太值得反复提起。用一句别的话来回答上面的两个问题吧:“每个民族能进入思考序列的作品,在开端意义上就是那些基本经典。这些经典连同仿佛跟它们长在一起的注疏,让一群自然聚居的人,成长为一个自觉的文明共同体。如同古希腊在他们的经典教导下形成了独特的nomos(民俗,宗法,法律),在一个以五经为主的教化序列里,中国也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特殊‘谣俗’——从这nomos和谣俗里,大约能看出此一共同体人的性情、生活方式乃至命运的造型。”
责任编辑:梁佳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