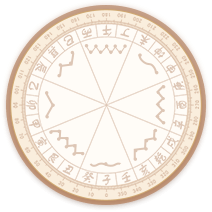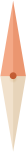「琬琬,好不好?」「不要。」我瞬间明白宋仪亭的意思,赶忙拒绝。御医再三叮嘱,此事最容易复发腰疾,我断然不能在他的病有起色的时候冒这个险。宋仪亭强硬了二十多年的硬骨头在这一刻化成一团绵软,近乎央求着,「我只看看。」他鼻尖轻碰我的鼻尖,像一只讨食的小狗。他嗓音沙哑:「你允了吧?求你。」怒的宋仪亭,笑的宋仪亭,放下身段求人的宋仪亭,在这一夜尽皆展现。不论哪一个,都是我的夫君啊。我不忍他煎熬着求饶般讨要一点好处,点头:「好。」他掌心覆上我的手,浅笑着,暖声:「吾妻甚美。」宋仪亭欣赏不够,挪了挪身子,抱住了我。我想过。但不是欲望,而是憧憬。少女怀春,总有些更隐秘的期盼在细密的心思里头。盼望自己夫婿床笫之上温柔体恤,盼望自己能得夫君宠溺,盼望自己能在夫婿的掌心里化成水、绽成花。而今,我憧憬的,都成了现实。宋仪亭闻言笑了:「娶你那日,我闹了好大的脾气。你知道为什么吗?」宋仪亭抚摸得我筋骨绷直,可是身体又止不住地发软。我不敢侧首,不敢动,问:「为什么?」他说话吐息就在我耳侧:「我记得张大人家的女儿不过是个小丫头。」他回忆往事似的,「我曾在长街上见过你,只是你不记得了。你那时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逢人便害羞,直往你父亲身后躲。所以我怎么算,你也未到嫁人的年纪。而我病入膏肓,娶你就是害你。我不舍一个好端端的小姑娘跳进这个火坑。」「可是我们八字相合,是天定的姻缘。」「你信吗?」我想了想,认真道:「以前不信,可是见到你而今一天天地好起来,便信了。」「琬琬若是信,那我也信。」他揽我入怀:「也许真是天定的姻缘,让我娶了你。」宋仪亭说令人耳红面赤的浑话,「怎的跟蜜桃儿一样润。」他没把我怎么样,却勾起了我的一团火。少女的憧憬变成欲望,我呼吸都乱了节奏。我转身投进他胸膛,不自觉地说话带哭腔:「宋二郎你王八蛋,你欺负我。」他指尖点在我脊柱上,跟数脊骨骨节一样。他笑:「再等等,等吃过了这服药,身体再好点儿,定然欺负得更甚。」
重阳临近,四弟从边塞回来,家中更加热闹。
四弟打小儿最喜爱他的二哥,回来不到半晌便去了东院,说得是家国大事,我听也听不明白,索性来前院跟妯娌聊天。
女眷热闹哄哄,不知怎么的说到了子嗣之事上。
而今宋仪亭的病好起来,婆母不再为这事担忧,不少精力放在了我们几个儿媳的生养上。大嫂有个女儿,好歹还能应付婆母两句,我和三弟妹沈月如就少不得挨说。
许是我年纪比沈氏小,婆母撇开我直接说沈月如,一点儿也不似平日里怜惜:「老三不似老四在外头,他天天在院里,怎么你俩就没点动静?」
沈月如最怕婆母说这个,面上笑着,背地里攥着我的手直挠我手心。
婆母愁眉苦脸的:「那日我那远房堂姐来,硬给你房里塞女使,我都不知道怎么给你挡回去。」
沈月如一点儿也不委屈:「不劳母亲烦心,儿媳心里有数。」
「有数就生啊。要不然老三天天晃院里,我都看着碍眼。」
大嫂偷偷笑,我也跟着抿嘴。
沈月如一看着急了,不好意思说大嫂,拿我出来当挡箭牌:「母亲偏心,要生,按顺序也该是二嫂先生。」
我愣了,还有这样出卖同袍战友的?
我琢磨着回去后怎么好好骂一顿这个小没良心的妯娌时,她接着道:「二哥如今身体大有好转,眼瞅着就可以痊愈了。而且东院里的人都在说,二哥和二嫂越发如胶似漆,比新婚时还腻。」
她不顾我拧她,心虚地松开我的手,一脸讨好的样儿:「母亲您肯定不知道,这天越冷啊,二嫂越爱往二哥房里钻。什么分房睡,都成幌子喽。」她还撒上娇了,「母亲,你快问问二嫂呀。」
显然,比之三弟和三弟媳妇的事儿,婆母更关心我们东院的。
她老人家径直看我:「老三媳妇说的是真?」
「我……」
「我倒是想起来了,中秋那日去送暖胃汤的丫鬟说,你宿在老二的房里。」
我站起来,紧张死了:「母亲,我以后不敢了。」
太医吩咐不能行房事,我还往宋仪亭身边凑,不是明摆着让他逾矩吗。
「什么敢不敢的,你想睡哪儿随你。老二的倔性子,自小我就管不住他,而今娶个媳妇,叫他自己管,我才懒得管。」
我不敢抬头,听不出婆母这是生气了还是没生气。
「母亲还是替我管着吧,这小猴子调皮得很,儿子管不住。还得有劳母亲费心。」
宋仪亭的声音蓦地从身后响起,屋内所有人循声看过去,看到宋仪亭坐在门口的轮椅之上。
椅子是木质的,前些日子做好后取回来,他嫌麻烦,赌气不用。
没想到现在不光用上了,还在四弟的帮助下来了前院。
婆母起身,又惊又喜地上前迎宋仪亭,激动得话都说不完整:「儿,我……」三两个字间就落泪了。
宋仪亭进屋,好一阵安抚婆母,而后看着我笑了。
沈月如扯我衣袖:「哎,给你撑腰的来了。」
我低语:「等出了这门,我就好好罚你。」
「罚我什么?」
我没想好,只在宋仪亭的目光里红了脸。在众目之下,他这样宠溺地瞧着我,还是头一遭。
「我针线活儿好,给你孩儿做双虎头鞋吧?」她杵杵我,「还说你俩没有恩爱似蜜,老二看你看得眼睛都直了。我看这孩子,你得比我早生了。」
我不搭理她,羞涩地垂下了脑袋。
晚饭在前院吃,第一次全家人聚在一起吃这么大在阵仗的团圆饭。
听闻宋仪亭也在,公爹特意从宫里提早回来。饭间其乐融融,我仗着公爹心情好,替宋仪亭讨好处:「父亲,您那几坛御赐陈酿,还有吗?」
「御赐陈酿?父亲您宝贝着一直不肯给二哥喝的那几坛吗?我也想沾沾光。」四弟嚷嚷。
「我也想尝。上次没喝够。」三弟开腔。

屋里七嘴八舌,公爹无奈,差人去取。
宋仪亭在桌下悄悄攥我的手,低声道:「我喝不了。」
我冲他眨眼:「喝得了。」
他不明所以。
我反手牵住他:「我昨儿问过太医了,这服药吃完,可以停药半月。这半月你可以尝点儿你平日贪嘴却吃不到的东西。」
宋仪亭看着我不说话,一本正经的模样。
「怎么了?」我与他十指相扣,耳语,「能喝到馋了许久的酒,开心坏了?」
屋里热闹,他趁着没人搭理我们,又说浑话:「可是我最馋的是你。这个今晚也能尝吗?」
我一口茶下肚,憋红了脸。
宋仪亭说话轻声细语:「御赐陈酿还没喝上,我娘子的脸倒先红了。今儿你可是红了数回了。」
……
家宴结束已晚,天黑了下来。房中床褥准备整齐,不知道是哪个丫鬟当值,粗心大意的,床头又错点了一对儿鸳鸯红烛。
我懒得骂,吃了酒后脑袋晕乎,直想往宋仪亭的床上躺。
宋仪亭酒量本就好,再说那几口跟尝味道似的,他没有一点醉意。
我睡不着的时候折腾他,而他兴致好的时候则会折腾我。我侧身睡着,他单臂环着我,轻吻我发鬓:「琬琬,我想沐浴,想更衣。」
我困得不想睁眼,揪着他的衣衫闻了闻:「今晨刚换洗的,干净。而且身子我给你擦过了,明天再洗。」
「就今晚。热水我已经命人备好了,你就替我洗洗,」他软声讨好,「好么?」
我睁开眼,鸳鸯红烛晃得眼睛酸涩。
我打个呵欠:「好吧。」
给宋仪亭沐浴已经成了我的日常之事。婚后他完全不让下人着手自己的贴身事,全依仗我一个人。
好在他泡在浴桶里时就会格外乖顺听话,泡得舒服了,唇红齿白,外加皮肤本就白皙,俏丽得不似个遭受过边关风霜的男子。
他乖顺时会给我讲许多他之前从不提及的故事。尽管他从不自夸,可是他的骁勇与智谋,总在这些故事里慢慢显露。我好爱故事里的他。
他在重拾过去,也在憧憬未来。
给他洗完夜已深,我拖着疲惫的身躯爬上床榻,窝进他身侧。
我嘀咕:「不回隔壁了,那屋太冷了。」
宋仪亭发丝还是湿的,靠坐在枕上翻那本没看完的兵书,看我嘟囔着往被窝里钻,低首:「也没打算让你回。」
我迷瞪着眼抬头:「额?」
「厢房的床褥我叫人撤了,以后你宿这儿吧。秋冬夜里凉,你这手脚总是冰冷冰冷的,让人总惦记着你睡好了没。」
我抱着他的手臂谢他:「有劳夫君。」
灯下,宋仪亭目光炯炯地看了我好一会儿,将书放在枕侧,伸手拨我搭在额前的头发:「我担了夫君的名,却没有能力保护你,遑论为你出生入死,就是在夜里给你暖暖手足都是奢望。」
他的语气里难掩伤心,我心疼,主动伸手环上他的腰,安抚他:「你已经对我很好了。锦衣玉食,荣华富贵,这都是我之前不敢想的东西。」
他抚着我的眉眼,笑道:「你与我在一起,原来是图这个啊?」
「不是。」我抬眼看他,「图你这个人。你呢?你如此待我好,是为什么?」
「为了什么?」自问一句,他微微侧着脑袋,想得极认真。好一会儿后,他答:「为了活着吧。」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眨着眼看他。他的指腹在我眼睫上,睫毛快要蹭在上面。
「久卧在此,数年间没有一日是开心的。我总觉得这一辈子哪怕不是征战沙场博得功名,也好歹得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可是遇见你之前那些年,我活得毫无人样。躺在这里任人摆布,哪里会有尊严,哪里又会有活下去的信念。」
宋仪亭话说得沉,却没有像往常一样叹气,而是扭头看我:「可是你来了,我就得活下去。」他眼里带笑,「我不能让我新进门的小娘子守寡,是不是?她还小,要是真守了寡,保准天天跟在新婚夜似的,哭鼻子。」
我否认:「我没哭。」
「那怎么红眼睛了?」
「那天太饿了,饿红了眼。」
宋仪亭被我彻底逗开心了,指腹挪开半寸,打量我:「那我看看,今日眼睛红了没?吃饱了没?」
我搓搓日渐圆润的小肚子,答:「饱了。」
「那既然暖了,也饱了,我们做点其他的事情?」
「不要。」
宋仪亭哪容得我否决,说话间抚在我眉间的掌心覆盖下来,遮住了我的眼睛。
他像中秋那夜一样吻我,半湿的发丝垂在我颈侧,就跟吻我的脖颈似的。
他说话轻喃:「琬琬,我命人点了红烛。洞房夜相欠的,今夜补上。」
尽管早被他脱过衣衫,看过身子,可是我还是害羞。我的脸在他的掌心里发烫,从吻里挣脱出来,深喘不止。
他取开手,烛光映在眼前。
他生得好俊,一如在洞房夜初见他时那般清朗俊逸,只是比当时胖了些。
我紧张得不敢动,发憷间被他褪去了衣衫,我才反应过来,猛地担心他:「小心旧疾。」
「我有分寸。」宋仪亭掌心托着我起身,教我与他相对而视。
我又羞又臊,不敢直视宋仪亭的身子。我结巴:「可是……我忘了。」
「忘了什么?」
「忘了教习嬷嬷教的了。」
宋仪亭温柔至极:「我教你。」
……
我有两次洞房夜。
一次和衣睡在宋仪亭身侧,醒来后天还没亮,听见他沉沉叹气,心里满是淫欲。
一次不知羞地趴在宋仪亭怀里,闹了一宿。他不再叹气,因着不小心弄疼了我,所以柔情蜜意地哄了我一宿,说了一宿的情话。
醒来后天大亮,宋仪亭安稳躺在我身侧,呼吸匀称舒缓,早没了重病时的深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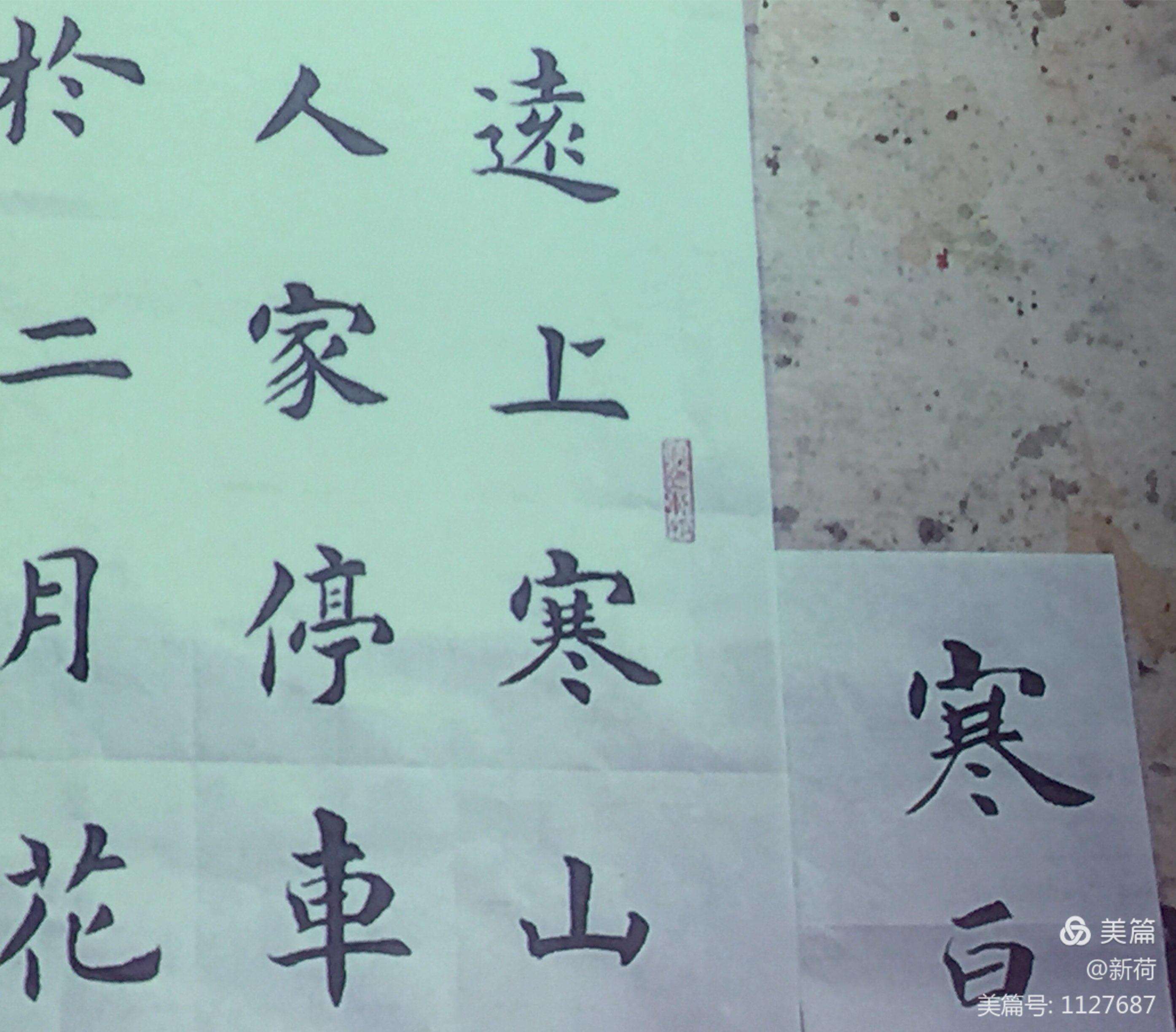
眼波似水,眉峰攒聚,他的五官如画般美丽。
我忍不住伸手描摹,欣赏美景。摸到唇边时,实在好奇:「相公,你儿时得有多好看,才能长成现在这般容颜?」
宋仪亭唇瓣殷红,齿尖想咬我的手指时被我避开,咬了个空没咬到。他不失落,反而笑言:「想知道我儿时的模样?」
「嗯。」
他伸手摸上我的小腹:「咱们生个儿子,不就知道了?」
雪来得晚,小年那天,才洋洋洒洒下下来。
张琬裹着厚厚的衣服从沈月如院里回来时,在门口迎面撞上屋里的丫鬟。丫鬟说小少爷去了前院,贪祖母身边的宫廷糕点,一时不想回来。
张琬觉得挺无奈的。三岁半的儿子不算大,可是贪嘴这个毛病跟她如出一辙。只是娘俩长得不同。
儿子越大,模样越似宋仪亭,尤其那口鼻简直一模一样,鼻梁挺翘,唇瓣殷红,白嫩嫩的皮肤惹得沈月如都替自己的女儿眼馋。
她还未进东院门,便听到院里有人叫她。叫的是闺名,温温柔柔的:「琬琬。」
张琬恍惚以为自己听错了。
这么叫她的只有一人——自家夫君。
可是宋仪亭出征一年了。前些日子还传言说不班师,宋仪亭兄弟二人得在边关过年。
「琬琬?」
又是一声,叫得真真切切的,张琬错愕不已,猛地推开了门扇。
院里廊下,宋仪亭长身而立,看到张琬进门,一步三阶跨下去,淋着大雪拥住了张琬:「去哪儿了?我找了许久。」
张琬恍惚,以为自己做梦了。
宋仪亭抱着怔愣的人:「我回来了。」
他说话间吻上张琬的发鬓,吐息是热的,身躯也是热的。张琬才慢慢知觉,真是自己朝思暮想的人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不是说在边关不回来过年吗?」
宋仪亭亲吻张琬的眉梢,想吻上唇瓣时碍于还在院里,忍了又忍:「皇上说我们兄弟二人只留一个在那儿就行,四弟不想回,所以我便回来了。」
张琬觉得自己欠四弟的人情挺多:「他又照顾我们夫妇。」
「哪是照顾?他巴不得不回来呢。」宋仪亭鼻尖轻碰张琬的鼻子,「塞上姑娘美,四弟被佳人留住了心。」
「那你呢?佳人怎么没留住你?」张琬玩笑道。
「留住了啊。我的佳人在我院里。」
张琬抿着唇笑,桃李之年,越发美丽,惹得许久不曾见的宋仪亭看直了眼。
张琬被看得不好意思,往宋仪亭怀里躲:「去见过母亲了吗?」
「见了。」
「儿子也在母亲那边。」
「见着了,长得颇快,就是见到我认生,往人后躲。」宋仪亭轻抚张琬的发丝,「跟你小时候一般胆小。」
「他胆儿大着呢,只是许久不见你,猛地见到给唬住了。前儿夜里我哄入睡时,他还在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委委屈屈地跟我说,他想你了。」
「那你呢,想为夫吗?」
张琬含羞,脸靠在宋仪亭胸前不说话。
宋仪亭不等张琬回答,自顾自言:「琬琬,我好想你。但凡有所闲暇,就止不住地挂念。」
张琬抬头:「不是见到了嘛。」
抬眼间,看到白雪落了宋仪亭一身,黑亮的青丝上沾染白羽般的雪花,一瞬白头。
张琬觉得自己嫁给宋仪亭似乎太久了,夫妻二人恩恩爱爱,恍惚已过百年,就此双双白了头。
可是又觉得短暂。
大婚就跟发生在昨日似的,将军府的聘礼流水般往张家送,张琬坐在花轿里懵懵懂懂,袖中藏着一颗被体温焐暖了的饴糖。
那颗饴糖是张琬留着果腹的,却在新婚夜被自己的夫君吃了去。
许是饴糖太甜了,滋润得婚后的日子也甜得如蜜。
张琬轻轻为宋仪亭抚去额前的雪,轻声:「回屋吧,这儿冷。」
宋仪亭道一声「好」,打横拦腰抱起张琬,朝屋内而去。
……
沈月如后脚跟着张琬过来,手里拿着早早绣好了的虎头帽。
东院门开着,院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雪地里有一行快被雪掩盖了的脚印。
她倒一点都不好奇,以为张琬又跟以前一样,贪睡晌午觉忘了关门。
沈月如在廊下收起伞,准备敲门时被骇在了原地。
门内动静不小,宋仪亭哄着说些令人面红耳赤的浑话,惹得张琬哭得更凶。
沈月如犹如被雷轰顶,往后退了三步,惊在当地。
不知什么时候,院里的丫鬟轻手轻脚过来,低声恭顺询问沈月如是什么时候来的。
沈月如杏眼瞪得浑圆:「我……」
丫鬟解释:「二爷回来了。」
沈月如把手里的虎头帽往丫鬟怀里一塞:「给二奶奶,她刚忘了带过来。」她说罢扭身就走,大冷天的,被吓出了一身汗。
出了门撞上自家夫君,沈月如当即要哭了:「相公,太可怕了,我……我……」
「怎么了?」宋仪恒揽着沈月如,「听闻二哥回来了,我来看看他。」
「别看了。」沈月如惊魂未定,抱着宋仪恒低声道,「里面鸳鸯戏水呢,去了臊你出门。」
宋仪恒:「…………」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