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轻人们来到寺庙,诵经、吃斋、念佛,但不出家。为了躲避现实苦楚的他们,在寺庙早起早睡,有吃有住,不为金钱、绩效和晋升所忧虑,没有竞争,没有内卷,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代的寺庙托住了这些年轻人,允许他们暂时过上一种清净,但又不至于完全远离世俗的生活。
文 | 谢婵
编辑 | 金匝
运营 | 月弥
1花已经枯萎了,从佛祖的供奉台上拿下来后,它们又在寺庙图书馆的花瓶里待了几日。毕竟是供养过的花,万物有灵,弘鑫和两位同事舍不得就这么扔掉,于是决定为它们举行一场“葬花”仪式,在《大悲咒》的背景音乐里,大家把花整整齐齐地放进浅坑。
弘鑫今年26岁,本名杨林鑫,两个月前,他辞掉北京一家知名报社编辑的工作,南下来到浙江的一家寺庙做图书管理员,法号弘鑫。
按照计划,他至少会在这里待上一整年。常有人问他,是不是真打算剃度出家,从此不问凡尘俗世,他总是摆摆手,“那不至于”。这更像是一种“半出家”的生活,在寺庙,弘鑫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打工人,图书馆的工作每天两班倒,早上七点半到下午两点,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月休四天——这也意味着这四天可以“还俗”。至于以后,是回到俗世,还是去佛学院进修,他也还没想好。
弘鑫来的这间寺庙,四周分别是生活小区和即将建成的古镇景点,走上一两公里,就有大的商场和超市,离红尘近得很。但和其他寺庙又不太一样的是,这里没有卖旅游纪念品和鲜花香烛的商业街,不提倡烧高香,周围小区里的孩子,甚至周末会来这里的图书馆写作业。寺里的人引以为傲的是,相比寺庙,这里更像一个市民社会里的公共社区:流动,包容,开放。
弘鑫工作的图书馆倒是幽静,明亮的大落地窗外是竹子和草,整个更像是一个现代的茶楼,有榻榻米,有wifi,能打坐,能喝茶,比很多图书馆都要惬意。图书馆里的书很多,但佛经其实只是其中一部分。刚来的时候,弘鑫就惊讶地发现,有一个橱柜里,佛教典籍旁边居然就摆着基督教的书籍。这里甚至还有很多经管类的畅销书籍,全年的《第一财经周刊》和《三联生活周刊》,还有《资本论》和金庸小说。
书是寺庙里的方丈法师挑的,大家称呼他为大师父。大师父今年五十出头,从佛学院毕业之后,又去大学读了硕士。他喜欢听书,一个人走路的时候耳朵上总挂着耳机,过去一两年里,他一共听了2000本书。他也喜欢笑,一笑起来,五官就变成标准的笑脸线条。
他似乎永远保持着一种年轻的状态,温和,不说教,当被问道,“怎么看待像弘鑫这样辞去大城市的工作来寺庙的年轻人”的时候,大师父摆了摆头:“我没有看法,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觉得年轻人要多经历世事,但从来不会去鼓励或者告诫他们这样做,“成为自己就好。”

▲ 寺庙图书馆里供人抄经的书桌。图 / Sam
2在寺庙,弘鑫的一天被拉长。凌晨四点半是起床时间,天还黑黢黢的,钟楼和鼓楼的声音相继响起,五点整,他从宿舍出来,穿过廊桥,来到寺庙大殿前,等着跟寺里的师父一起行禅。
行禅,其实就是走路,在大殿前的广场上,从这头走到那头,十来米的距离反反复复走上二十分钟,师父会说:“慢慢走,放轻松。”但每次听见这句话,弘鑫瞬间觉得自己不会走路了,他站在师父身旁,快速瞟一眼,看师父先迈哪只腿,想努力跟上师父的节奏。
或许是感受到弘鑫并没有完全静下来,师父对他说,明天行禅的时候,可以感受一下头顶蝙蝠翅膀震动的频率,他当即就懵了,抬头望去,头顶居然真的有一只蝙蝠。
刚来图书馆的时候,弘鑫还没有学会“静下来”这种节奏,老想着要干更多的活儿。但师兄们一齐干活的时候,干一会儿要歇一会儿,喝点茶再继续干,今天做不完的工作明天再做,明天做不完就后天再做。这和他在报社高强度、快节奏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之前作为报社评论部的夜班编辑,他通常在凌晨三四点入睡,下午两点起来上班,把自己负责的一个版面填满,报上印的东西不能有一点儿差错,得始终保持那种紧绷的状态,“太憋闷了,不是忙着改稿走流程,就是忙着想标题”。
为了方便上夜班,弘鑫的房子租在了距离报社10分钟路程的地方,但当他走出报社大门的时候,并没有回家的欲望,只想在附近转几圈。北京深夜的街头只有麦当劳还开着,他会进去吃个套餐。有时候去便利店,售货员早认识他了,过了12点以后剩下的关东煮不能卖了,就全部打包给他。
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睡在三轮车上的拾荒老人,遇见的多了,弘鑫都会给他们留下一包火腿肠和一包糖,想让他们尝尝“肉滋味和甜滋味”。
上夜班会带来许多问题,完全没了社交是其中一个,“别人上班的时候我在睡觉,别人社交的时候我在上班,别人睡觉的时候我在刷手机”。紧随其后的是失眠,一开始,他觉得放轻音乐有点用,能解决问题,但慢慢就失效了,他又买了个香薰机,再后来,干脆买了个小鱼缸听水声。
后来报纸人员削减,弘鑫不用再上夜班,白天反而更忙,如果来了热点,不管什么时候,都得追起来,要抢时效,要抓着作者写稿,来不及吃饭是常态——在北京,这家报纸评论部的工作节奏是以忙碌两个字著称的。
工作的4年里,他的体重从160斤增长到190斤,一起增长的,还有焦虑感。纸媒的黄金年代早就过去,许多人跳槽去了互联网公司,包括他在报社里的一个好朋友,他是为数不多还在原地的人。就在这一年,他和恋爱的女朋友也分手了,变成无牵无挂的单身状态。
除了本身对佛教有兴趣,上述这些过往生活里的压力,也推动着弘鑫做出了去寺庙的决定。
他觉得目前可能是最好的时机了:今年26岁,仍然保持着年轻人的活力,还没有成为丈夫或者父亲,最后是,父母身体也健康,没有什么负担。他想,再不去完成这个愿望,未来可能就很难有机会了。最重要的是,寺庙图书管理员的岗位,今年7月份就会空出来,以前他也问过寺庙里是否招人,得到的反馈都是只需要“帮厨”“水电工”一类的工人。
甚至这期间,弘鑫还拿到了一个大厂的offer,对方开出的薪资可观,是他在报社工作的倍数,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事实上,那也是他大多数同事的去处,他原本也心动了。但经历了一番“斗争”后,他想清楚了,大厂好像随时可以去,但寺庙是要讲缘分的。他回绝了这份offer。后来他自己琢磨:“难道这是佛祖对我的考验?考验我的心诚不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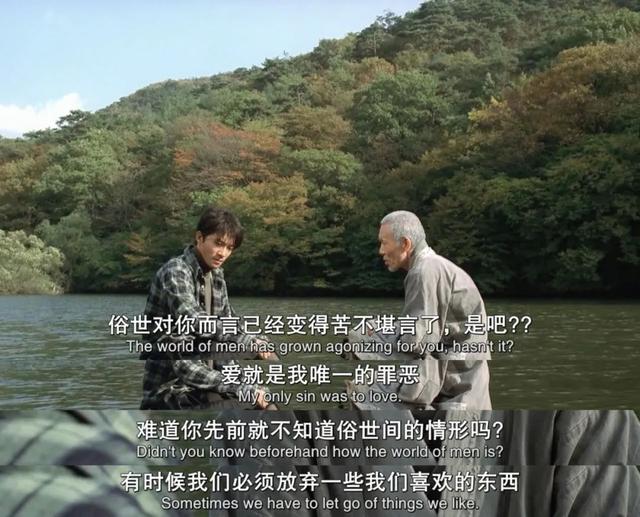
▲ 图 /《春夏秋冬又一春》截图
3像弘鑫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寺庙,成为义工或者寺工,短暂停留,他们诵经、吃斋、念佛,但不出家。为了躲避现实苦楚的他们,在寺庙早起早睡,吃住不愁,没有竞争,没有内卷,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也不为金钱、绩效和晋升所忧虑。
当代的寺庙托住了这些年轻人,允许他们暂时过上一种清净,但又不至于完全远离俗世的生活。工作遇到瓶颈了,人生走进迷雾了,他们因为不同的理由来到寺庙。对被困在系统里的年轻人来说,寺庙是一个理想居所,一个世外桃源。
弘鑫在寺庙有一位流动的义工室友,名叫罗一黑,他在上海从事广告设计行业,自从去年8月第一次来过寺庙后,他前前后后又来了5次,工作不忙的时候就待上半个月,忙的时候就待个两三天,帮寺里干干活,念念佛经,不用管上海那些难缠的甲方和难搞的工作。
项目上的事情是最磨人的,罗一黑遇见过最可怕的甲方,会一整夜一整夜不睡地改方案,那时他脑子里永远同时装着十几件事,一刻不停思考和工作有关的事情。相比那种时刻,寺庙里的生活简直是天堂,一日三餐定点定时,连每天做什么都是被安排好的。
同为上海人的义工张橙也是因为差不多的原因来到寺庙,她前阵子刚辞职,还没有从高压的工作环境里缓过来,在网上刷到了很多寺庙义工的帖子,“早起早睡,逃离城市”,她心动了。“我也是一个在大大的社会热炉里想自我解救的人,这种安静的环境,或许能让我静下心想想未来应该去做的事情。”
今年26岁的荣晰第一次接触到佛学还是两年前,当时他念大四,在美国上学,他所在的大学里,佛学是非常受欢迎的课程,每年他和同学们都需要使用自己的学分,像竞标一样选课,分高者得,而佛学的课程,需要投四十多分才能选中。
他刚经历过一段意外,打篮球的时候被队友误伤,确诊了脑震荡,篮球不能再打了,学习和申研也近乎停滞。从小,荣晰接受的就是“精英教育”,落后是不被允许的。他童年的周末是被兴趣班填满的,书法、奥数、英语、乒乓球、围棋、日语、画画……以至于他最喜欢的其实是上学日,只需要在学校里好好上课就行。
如果从更长远的生命跨度来看,留级,下一年继续申请也不是什么难事,但他觉得父母不能接受,那也是一种他从小到大始终保持的念头——不能放松,不能让父母失望。
成为“赢家”的渴望和不能落后的念头,在漫长的年岁里塑造着他。在大四那一年,打篮球过程里的小意外引起了他人生里的大动荡,他焦虑,继而开始便秘、失眠。人生的第一堂佛学课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开始的,他形容不出来那种感觉,学习的过程里他想了很多事情,想到自己成长过程里的种种不对劲和紧绷,直到结束的时刻,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这么舒盛,不再想着“赢”这件事。从此,荣晰开始越加频繁地学习佛法,直到他真正来到了寺庙。

▲ 图 /《朝5晚9》截图
4其实,和年轻人的想象并不完全一样,寺庙里的生活,也有另一套必须严格遵守的规矩。
开餐前,要先诵读《群书治要》和《供养词》,师兄们会提着桶走到食客面前打菜,吃斋的时候不能说话,每样菜要多少,要不要,想要浓粥还是稀粥,全依靠专门的手势,复杂难记。寺庙里还有一套自己的语言习惯,打招呼的时候要双手合十,微微低头,寺工们无论男女,统称师兄好,表达谢意的时候要说感恩,晚上告别的时候要说“夜寐吉祥”。
虽然节奏慢,但寺庙里消耗的体力一点也不少。从前弘鑫在报社,出门一天,微信步数显示几千步,寺庙里虽然也只有那么大一块地方,但他逛来逛去,每天的微信步数都在一两万步上下。
弘鑫对诵经好奇,也去体验,一开始,师父们的语速还算正常,到后来速度越来越快,字也更加生涩难懂,天热的时候,弘鑫用手帕擦了擦汗,就不知到师父们念到哪里了——那时他才感受到,原来诵经也需要体力,他还没适应南方的炎热天气,中途差点儿中暑了。
更重要的是,时间被一段一段划分好并填满。出发前,弘鑫跟朋友们说过:“你们天天嘴上喊着躺平,这回是我去寺庙,真躺平了。”在他的想象里,在寺庙,会有大把的时间用来发呆、打坐、喝茶,但真来了,这些想象最终幻灭了。
他发觉自己不但没有“躺平”,反而更加“支楞”。上班的时候,他打扫卫生,擦榻榻米,擦书架,洗茶杯,消毒,给抄经人倒墨,图书入库,对账,事情细小又繁琐。不上班的时候,寺庙里的时间也是要被精确到每分钟,一天的时间被起床、早斋、午斋、晚斋、打板熄灯隔成了四块,在这些碎片的时间里又填满了更多密密麻麻的事情。
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年轻人在寺庙的半天是如何度过的:
4:30-5:00 起床
5:00-5:25 行禅、听钟声,和师父交流
5:25-6:10 早课
6:10-6:50 自由活动、学习文稿
6:50-7:30 早斋
7:30-9:30 打扫图书馆卫生
9:30-10:10和师父们诵《妙法莲华经》
10:10-11:15 受邀旁听禅修办内部培训
11:20-12:00 午斋
义工张橙也有这种感受,即使没有早课的时候,也要6点起床,白天,她被安排去钟楼拖地,又干了许多体力活,她有些吃不消,“平时哪里做过这些呀,在家扫扫自己的小房子了不得了哦”,等到了晚上,终于回到宿舍,才发现人是可以连刷手机的时间都没有的。
在寺庙里,最明显的改变是饮食。弘鑫以前最爱吃肉,胖了以后有意克制,但还是得半个月吃一顿炸鸡。来寺庙两个多月,他只在下班的时候出去吃了三次肉。他发觉,自己似乎对以前喜欢的事物没那么大的欲望了,也解释不上来为什么,只能归因于寺庙的道场影响了人。
饮食和作息带来的变化体现在他的身体上,来了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有天他穿裤子,突然发现腰带上的孔要往前扣几个了,图书馆的同事开玩笑,说他来了之后肯定瘦了十几斤,他不信,上秤称了一下,果然瘦了23斤。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有用手机软件监测睡眠质量的习惯,后来发现,自己睡觉已经很久不打呼噜了,因为豆制品吃得多,他之前缺乏的蛋白质含量也达标了。
几乎每个受访者也都提到自己进入寺庙后的改变,不只是身体上,还有心境上,变平和了,变得没有那么卷了。
罗一黑以前脾气有些暴躁,早些年在昆明工作的时候,有一年在外面出差,老板说了他不爱听的话,他连夜冲回昆明,也要讨个说法。来了寺庙,他觉得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规训自己的言行。而弘鑫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评价别人的时候不要有分别心。在寺庙里,几乎人人都克制着自己的言行,这是一种不成文的默契。
在寺庙里,荣晰感受到的是一种不需要竞争的放松。去食堂吃饭不需要比谁吃得快,早课晚课也没有人会在意谁念得更好,那是一种和他过去成长过程截然不同的环境。他过去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争”,小时候争考试的名次,争谁能当上班干部,长大了争篮球比赛的成绩,争男人的面子,争着领先同龄人,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
还有一些说出来有点离谱的小事,在出差的飞机上,只要旁边座位上是一个男性,他发现两个人就一定会在中间的扶手上用手肘顶来顶去,谁都不想认输。直到他在佛法里学到“忍辱”,才意识一个被“争”束缚的人,到底有多可笑。
离开寺庙的时候,荣晰算了一下,自己在寺庙里住了8天,期间上了两天课,课程报名花了450元,全程包吃包住。寺里的师兄送了他许多佛经、收音机、杯子、茶叶……他提着满满当当的行李回到昆明。见惯了压榨员工的老板和机构,他被寺庙布施的爱所打动了。
过去,荣晰做任何决定都喜欢做思维导图,计算利弊,择业的时候,他和社会里大多数人一样,看重收入,工作时长,最重要的是别人的评价,他曾经的理想时薪是500-1000元,一个月得有60个客户,收入会很可观。
但在寺庙里,所有的活动都是以直觉和感受为基础的,人不用思考什么,感受当下就行。从寺庙里出来,他开始有一个念头,未来找一份自己直觉上喜欢的工作就行。当所有的事情都被极简化,只剩下衣食住行,他才发现,人是可以压缩欲望,以极少的成本生存的。
(除弘鑫、荣晰外,其他人物为化名)

▲ 图 / 网剧《棋魂》截图
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