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完美的复制品是得到人们推崇的,但是现在来看,被打上复制品标签的艺术品则会令人丧失对艺术品本来的审美趣味。为什么面对一模一样的艺术品,我们的审美标准会发生变化?
下面这篇文章经出版社授权,摘编整理自《艺术与心理学》一书,较原文有少量删减。艺术是最复杂的人类行为之一,这本书的作者在进行实验美学的研究中,不是回答“艺术是什么”,而是试图回答“人们认为艺术是什么”,在书里呈现了大量观察性研究和实验,从心理学的角度回答了一系列人们关于艺术的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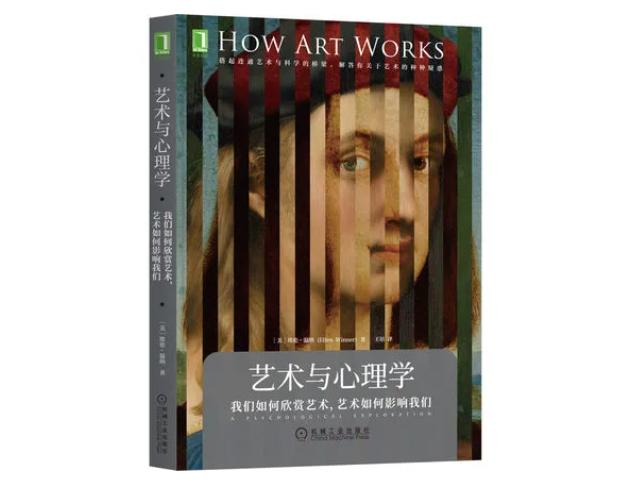
《艺术与心理学:我们如何欣赏艺术,艺术如何影响我们》,[美] 埃伦·温纳 著,王培 译,华章 |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1年11月版。
就历史上和史前时期的多数情况而言,人们能够欣赏或嘲讽艺术品,而无须知道或介意是谁创作了它们,又是在何种环境下创作的。在文艺复兴时期,完美的复制品是得到人们推崇的。当一幅据说是由拉斐尔创作的画作被发现是原作的完美复制品时,一位曾与拉斐尔共同创作过的艺术家说道:
如果复制品出自拉斐尔之手,我不会觉得它的价值更低。不仅如此,我甚至认为,只有极具才华的人才能将另一个极具才华的艺术家的作品模仿得如此逼真。
时代已经不同了。在西方,至少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人们更加看重艺术的原创性和真实性。独立艺术家经常被奉为天才,而众人皆知的复制品则在审美价值和商业价值上一文不值,这要么是因为我们知道它们不是出自伟大艺术家之手,要么是因为我们相信它们不如原作那般富有技巧,要么两种原因兼而有之。但是,只要社会推崇艺术的原创性,并且只要存在艺术的商业市场,伪造之作就会出现。
伪造之作使用原作者的名字,这是有意的欺骗。一个伪造者使其创作的作品看上去像是出自著名艺术家之手,其常见的动机是获得经济收益。伪造者不想获得名声,必须“隐姓埋名”。伪造不同于剽窃,后者是抄袭原作本身,其动机是以欺骗的方式展现剽窃者自己的技巧。与伪造者不同,剽窃者会在抄袭之作上署上自己的名字。辨别伪造之作需要发现其与原作之间的差异,而辨别剽窃之作需要发现其与原作的相似之处或相同之处。
没人知道有多少伪作挂在博物馆的墙上,但很有可能为数不少。大多数艺术伪作都是以某位著名艺术家的风格创作的新作,但有些伪作试图完全复制原作,这种伪作被称为“赝品”。赝品相对少见,因为如若原作非常有名,伪造者很难骗得了艺术市场。对《蒙娜丽莎》的完美模仿不可能让人们相信它是原作,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原作挂在巴黎的卢浮宫。
伪造之作干扰了我们对艺术史的理解,也欺骗了博物馆和私人收藏者。伪造之作还对哲学家提出了难题。请思考如下问题:当《基督与门徒在以马忤斯》(Christ and the Disciples at Emmaus)在1937年被公之于众,并被认为是荷兰大师约翰内斯·维米尔尚未被发现的杰作时,评论家将它奉为天才之作。想象你当时在揭幕现场,站在画作面前,感叹它的形式特征,称赞维米尔的技巧。现在,想象8年后你与评论家和公众一样,得知该画作不是维米尔的真迹,而是由伪造者汉·凡·米格伦(Han van Meegeren)在1936年伪造的画作。请你回到相同的揭幕现场,站在该画作面前,再次欣赏它。这一次,你知道它不是维米尔的真迹,而是伪造之作。
这幅画的绘画特征与你第一次欣赏它时完全一样。就这些特征而言,它仍属杰作。然而,曾经称赞这幅作品技巧精湛的同一群评论家现在开始指责和嘲讽它的缺陷。当我们发现一件作品是伪作时,它的审美特征在我们眼中真的就发生改变了吗?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不同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我们做出审美评价的基本标准是不同的。
对艺术品的评价并不完全取决于画作的特征
有些评论家和哲学家认为,与审美评价有关的所有要素都应该仅由画作的特征决定。因此,如果两幅画看上去完全一样,它们就不应该存在审美差异。用评论家门罗·比尔兹利(Monroe Beardsley)的话说:“我拒斥那种认为两幅完全一样的画有着完全不同的审美价值的观点。”有人认为,对伪造之作的任何蔑视只能是因为势利。这正是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莱辛(Alfred Lessing)和作家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观点。就像比尔兹利一样,他们采用了形式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法,认为艺术品的审美价值只与其感知特征有关,因此,伪造之作之所以被贬低,只是因为它们失去了其曾被视为出自伟大艺术家之手的特权地位。
其他思想家不同意前述观点。我们不仅会根据一件艺术品看上去如何来评价它,还会根据我们认为它与其他事物之间存在何种关联来评价它。简而言之,一件艺术品不只是一个物理客体,它还是一个具有象征价值的客体。谁创作了它,以何种方式创作,什么时候创作的,这些问题都是具有象征价值的。
这一观点符合一些心理学家所提出的观点,他们认为,人都是本质主义者,即人们有一种基本倾向,认为某种特定的客体具有根本的、不可见的“本质”(essence)。如果我的婚戒丢失了,我不会觉得新婚戒可以取代旧婚戒,因为前者缺乏后者的本质。类似地,著名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包含着艺术家的某种本质,因为这些作品与该艺术家相关,并且作品向观者表达了这种相关性。

特奥·凡·杜斯伯格作品《风景中的女人》。
当艺术家皮特·蒙德里安的传记作者列昂·汉森(Leon Hanssen)相信他已经发现,一幅被认为是由特奥·凡·杜斯伯格(Theo van Doesburg)创作的画实际上是由蒙德里安创作的时,他说,当看着这幅画时,“就好像你在与蒙德里安握手”。遗憾的是,这幅画并非出自蒙德里安之手。我在这里引述汉森的话,只是为了表明,他相信一幅作品相当于艺术家的一部分,伪造之作则不然。这种观点不完全是理性的,因为我们知道,画布上并不存在艺术家的物理本质。然而,谁敢说人类是完全理性的呢?
无数哲学家认同这种观点,即完美的伪造之作在审美上不如原作。达顿的观点是,我们对艺术品的反应和评价不可能与它体现的成就区分开来。一幅画是艺术家创作行为的产品,这些行为是为了解决某些问题。当我们欣赏15世纪意大利画家马萨乔的画作时,如果我们知道他是最早使用直线透视法的艺术家之一,我们对他的画作的评价就会有所不同。相比后世只是应用而非发明透视法的画家的画作,在解决问题的深度方面,马萨乔的画作体现了更大的成就,伪造之作则无法准确体现艺术家的成就。哲学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经常提到将艺术品放置于历史之中的重要性,他使用了“灵性”(aura)这一术语来呼应心理学上的术语“本质”:
即便在最完美的复制品中,也缺乏一样东西:艺术品的时空性,即它是特定时空下的独特存在。正是这种独特存在—别无其他,盛载着艺术品留下的历史印记……原创作品的时空性奠定了真实性内涵的基础……在技术年代对艺术品的复制,所欠缺的正是艺术品本身的灵性。
为什么一件完美复制品的美学价值不同于原创作品呢?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他指出,我们看待一幅画作的方式会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一件伪作而改变。我们会变得更仔细地审视这幅画,寻找它的瑕疵。因此,在欣赏同一幅画时,如果最先认为它是原作,然后又得知它是伪作,在前后这两种情形下,我们对画作的评价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之所以会寻找差异,是因为我们假定如果我们继续欣赏,我们可能会感知到两者的差异。简而言之,“既然练习、培养和发展区分不同艺术品的能力就是常见的审美行为,那么一幅画的美学特征就不仅包括人们在画作中看到的东西,还包括那些决定人们会如何看待画作的因素”。
即使是真迹,只要人们相信它是伪作,
就会给予更低评价
我们可以猜想伪作被贬低的原因,但心理学家认为实验更有说服力。于是,心理学家设计实验,想搞清楚当我们发现某件艺术品是伪作时会作何反应,以及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我们是极端的审美主义者吗,承认原作和毫无二致的伪作之间没有任何审美差异?还是说,我们坚持认为这两类作品存在审美差异?如果我们坚称,在某种程度上伪作的审美价值不如原作,这应该归因于本质主义吗?还是说,应该归因于伪作的审美价值被伪造者不道德的行为玷污了?我们该如何设计实验才能回答这些问题呢?
首先,有清晰的证据表明,仅仅告诉人们一件作品是复制品,就会导致人们在一系列维度上对该作品做出更低的评价。斯蒂凡妮·沃尔兹(Stefanie Wolz)和克劳斯-克里斯蒂安·卡本(Clauz-Christian Carbon)将同样的16幅画作呈现给受试者,并告诉其中一些人,这些画作是诸如达·芬奇之类的著名艺术家的原作,同时又告诉另一些人,这些画作是复制品,比如,是由著名艺术家的徒弟,或者由擅长制作著名艺术品复制品的当代艺术家根据市场订单创作的。
研究人员故意回避了“伪作”这个词,因为这可能会产生“响应需求”效应—受试者可能会假定,研究人员希望他们对伪作打更低的分数,因为这个词本身就含有贬义。受试者将从不同维度评价每幅画:品质、积极情感价值、审视带来的快乐、占有的欲望、熟悉度、卓越度和视觉合适度。他们还要从天赋、流行度和个人欣赏度来评价艺术家。
结果表明,当受试者被告知作品是复制品时,除了熟悉度,每个单一维度的评分都显著更低。在另一个实验中,研究者让受试者评价一幅凡·高肖像画的高质量复制品,但分两种情况:在一种情况下他们被告知该画作是凡·高最伟大的艺术品之一,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们被告知该画作是赝品。当该作品被相信是赝品时,受试者认为它的审美价值更低,并且也被认为重要程度更低。

伦勃朗的名作《夜巡》。
这种对伪作的贬低在大脑成像研究中也得到了反映。在一项研究中,受试者观看50幅伦勃朗的肖像画,同时由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监测大脑的血流量。每幅画只向受试者显示15秒。在图像出现之前,受试者要么会听到“这幅画是真迹”,要么会听到“这幅画是复制品”的提示语。他们被告知,复制品是指由学生、艺术家的门徒或伪造者制作的作品(因此夹杂了欺骗和非欺骗意图)。除了欣赏画作,受试者没有被分配其他任务。
有一半画作被标记为复制品,但画作的标签状态并不等同于画作的真实状态,比如,每幅真正的原作要么被标记为“真迹”,要么被标记为“复制品”;每幅真正的复制品要么被标记为“真迹”,要么被标记为“复制品”。在什么条件下大脑活动会有差异呢?是区别出作品真的是复制品(无论标签是什么)还是作品被标记为复制品呈现出来(无论真实情况是什么)?
当观看伦勃朗的画作真迹或复制品时,大脑活动没有差别。这很好理解:观者当然无法区分实际的真伪,因为这些画作的真伪通常连专家都无法达成共识。真正能发挥作用的是标签。当受试者知道画作被标记为“真迹”时,与奖赏和金钱收益有关的大脑区域(眶额皮质)更为活跃。
很多人还报告称,他们试图在被标记为“复制品”的画作上查找瑕疵,这证明了古德曼的观点,如果我们相信某幅画是伪作,而相信另一幅是真迹,我们对前者的看法就会不同于对后者的看法。
对复制品的贬低只针对艺术品吗?
我们对复制品的贬低只针对艺术品,还是说也针对其他人造物?纽曼和布鲁姆在另一项实验中解答了这个问题。他们让受试者阅读关于画作或者原型车的故事。根据故事的描述,画作和原型车都价值10万美元,然后有人对它们进行精确复制。研究人员让受试者回答他们认为复制品值多少钱,选择范围从远低于10万美元到远高于10万美元。复制的画作相比于原作所减少的价值会大于复制车相比于原型车所减少的价值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受试者认为复制画的价值要显著低于原作,但复制车的价值则没有减少。显然,当我们谈论艺术品时,我们认为原作中存在着某种特别的东西,而人造用具的原型则没有这种东西。
与汽车不同,复制会让艺术品失去价值。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现象:为什么一件艺术品的复制品价值如此之低,而其他人造物复制品的价值则与原物的几乎一样?纽曼和布鲁姆猜测,真实性对于没有明显实用功能的物品尤为重要。也许,一件物品越有用,其生产的历史故事就越不重要。我们会根据一辆车的功用来评价它,但由于一件艺术品没有特殊功用,我们就会用其他理由来评价它,并且我们会看重它的创作方式以及创作者。我还想补充一点,我们还会根据创作者的想法来评价一件艺术品。一件艺术品可以被视为表达了艺术家的个性和艺术家的世界观。我们通常并不会认为一辆原型新车表达了设计者的世界观。
区分道德与不道德的伪作,
区分不同类型的审美评价
截至目前,我描述的研究都是每次呈现一件艺术品,它要么是原作,要么是复制品,要么是伪作。毫不意外的是,给作品贴上“复制品”和“伪作”标签会对受试者的评价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这两个标签都有轻蔑的意味。甚至连小孩也会认为复制是不可接受的,无论复制者的意图是什么。但这种研究设计有其局限性,它没能抓住“伪作难题”的关键之处:我们对同一件艺术品的评价会随着时间点发生急剧变化。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可能先是知道并相信一幅类似《基督与门徒在以马忤斯》的画是维米尔创作的,随后才发现该画是伪作。我们对该作品的评价会急剧降低。
要是我们让受试者观看两幅并排呈现的艺术特征完全相同的画,将其中一幅打上“原作”标签,另一幅打上“伪作”标签,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受试者仍会贬低伪作吗?如果是这样,他们会认为伪作不如原作美、出色、吸引人吗?或者他们不得不承认,就以上这些维度而言两幅画没有差异,而差异只与所谓的历史维度有关,比如原创性、创造力和影响力?这些因素之所以属于历史维度,是因为一件作品在最早被创作出来时的原创性、创造力和影响力在其之后被复制时已经不复存在。
当两幅画作的艺术特征完全一样,而被标记为伪作那一幅却被人们贬低时,我们仍需要知道为什么会如此。一种可能性是,伪造是不道德的。需要注意的是,甚至5岁的小孩都相信伪造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它是一种欺骗行为。我们可以验证不道德行为在评价中扮演的角色,方法是将人们对伪作(不道德的)的评价与人们对由艺术家助手创作的、得到认可的复制品(并非不道德的)的评价进行对比。
第二种可能性在于,伪作不是由伟大艺术家创作的。我们可以通过将人们对由艺术家助手创作的复制品的评价与人们对由艺术大师本人创作的复制品的评价进行对比,从而了解艺术大师亲自创作的因素在审美评价中扮演的角色(假设两件复制品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在艺术与心智实验室做了类似的研究,向受试者并排呈现两幅完全一样的图像,要么是两幅画作,要么是两张照片。图像是被刻意挑选出来的,受试者无法分辨哪些是画作,哪些是照片。以下是我们对两幅相同画作的介绍:
这里有两幅名叫《热之光》(Light before Heat)的画作,是由著名艺术家阿普里尔·戈尔尼克(April Gornik)创作的10幅完全一样的画作中两幅。左边是第一幅画,由戈尔尼克创作。
实验存在三种条件。在伪造条件下,我们给出的描述如下:
右边是第二幅画,事实上是由模仿戈尔尼克画风的艺术品伪造者创作的。戈尔尼克依靠一群助手来创作她的画,这在当代和古典艺术家中是常见现象。每幅画上都盖有戈尔尼克工作室的官方印章,所以每幅画在艺术市场上的价值都是相同的。2007年8月,一位艺术史家发现了印章有伪造的痕迹,并在《艺术论坛》杂志(Artforum)上揭发了这幅伪作。
在非欺骗性复制条件下,我们的描述如下:
右边是第二幅画,由戈尔尼克的助手创作。戈尔尼克依靠一群助手来创作她的画,这在当代和古典艺术家中是常见现象。每幅画上都盖有戈尔尼克工作室的官方印章,所以每幅画在艺术市场上的价值都是相同的。
在艺术家创作复制品条件下,我们的描述如下:
右边是第二幅画,也由戈尔尼克创作。戈尔尼克依靠一群助手来创作她的画,这在当代和古典艺术家中是常见现象。每幅画上都盖有戈尔尼克工作室的官方印章,所以每幅画在艺术市场上的价值都是相同的。
我们故意声明,戈尔尼克依靠一群助手创作,并且这是常见现象,这是为了强调,这种行为没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每幅图像下面,我们列出了它的拍卖预估价。所有图像的预估价都是一样的,只有伪作例外,它的价格要低得多。因此,艺术家创作的复制品和助手创作的复制品在艺术市场上与原作的价值是一样的,这样受试者对它们的较低评价就无法被归于较低的预估市场价值。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没有在描述中使用贬义词“复制”,而是说第一幅画和第二幅画是一系列相同画作中的两幅。另外还有一个照片实验组,呈现给受试者的描述文字与画作实验组是类似的。
我们知道,伪作是有意的欺骗,因此是不道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引入艺术家的助手这一情形,除了意图不一样之外,它与伪造条件相同。我们认为这可以排除人们感知到的不道德所产生的影响。但当我们看到,助手创作的复制品在历史评价维度上的得分低于艺术家创作的复制品的得分时,我们担心受试者可能也将助手在作品上盖上艺术家的印章视为不道德行为,尽管我们已经做了声明,这种行为是常见操作。所幸,我们已经让受试者评价了艺术家、助手和伪造者创作第二幅画的道德程度。
毫不奇怪的是,受试者认为伪造比助手的复制更不道德,但他们也认为助手的复制比艺术家本人的复制更不道德。所以我们不得不将不道德程度作为统计意义上的控制因素。我们采用了线性回归分析法,揭示出不道德程度的确能在事实上预测受试者对助手复制品的评价要低于对艺术家复制品的评价这一事实。然而,回归分析也允许我们分别审视创作复制品的角色以及该复制品是否被视为不道德之作。
我们得出的关键结论是:即便在统计意义上将不道德程度纳入解释因素,只需要知道第二幅画是由助手创作的,就会导致受试者贬低对第二幅画的评价。也许,对于照片实验组的结果,这种被贬低的评价所带来的困惑表现得最为明显:为什么受试者也会贬低对助手重新印制的第二张照片的评价?
所以,当原作与得到认可的完全相同的复制品并排呈现在受试者面前,使得受试者感知到两者在视觉上非常相似时,之前出现在伪作和受认可的复制品上的较低评价没有出现在美感等广义评价维度上。相反,较低的分数与受试者对作品历史背景的评价有关。受认可的助手和伪造者所创作的复制品在历史评价维度上的得分较低,这一事实表明,在道德评价之外,我们还十分看重作品的真实性。显然,在这些历史评价维度上,即便是同一个艺术家创作的复制品也会被贬低,这表明时间优先级(哪幅画最先被创作出来)和谁创作了复制品(艺术家还是助手)都会对评价产生影响。
这一研究表明,对一件艺术品进行审美评价时,与作品本身的艺术品质(它有多漂亮,有多美妙,有多讨人喜欢)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了解该作品有怎样的历史以及它有怎样的创作过程。
原作者 | [美] 埃伦·温纳
编辑 | 申婵
导语校对 | 杨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