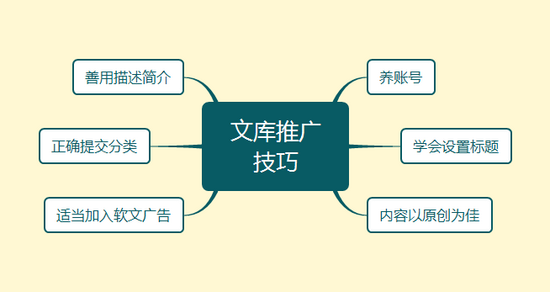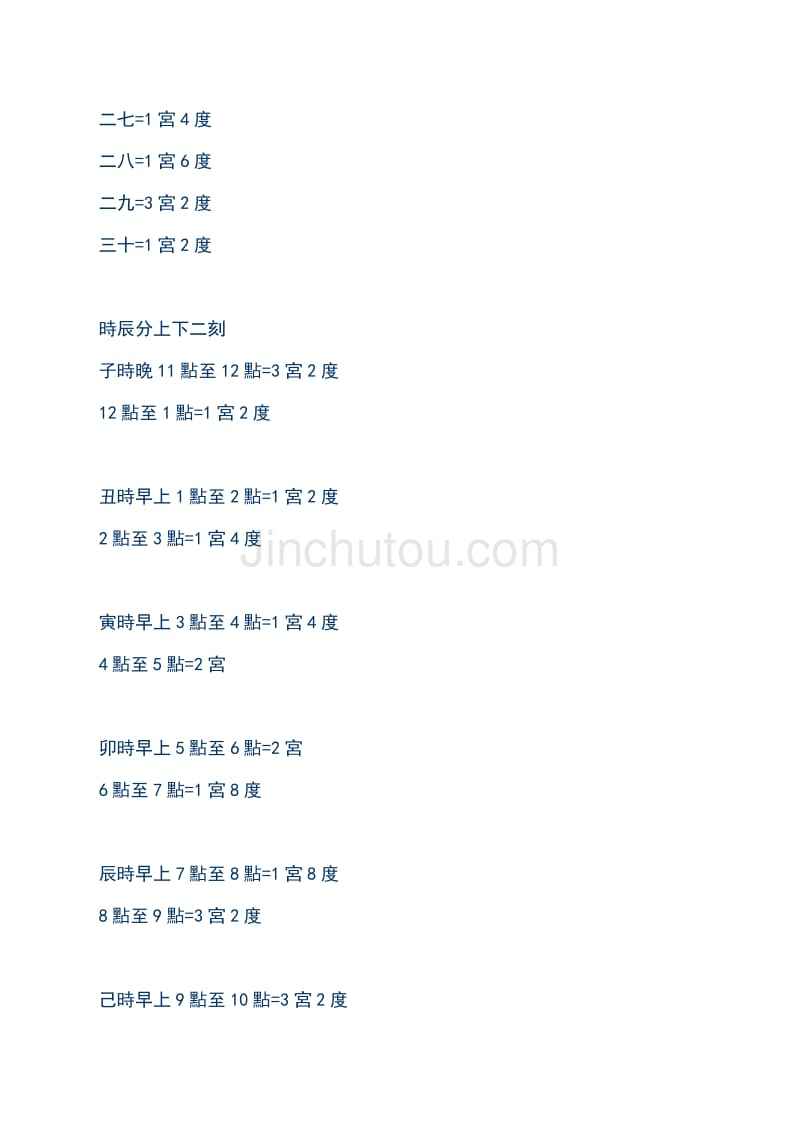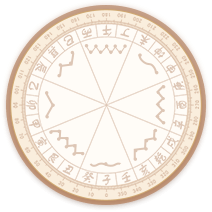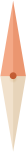八字精批2024运势命中贵人八字合婚
本文来源:《中国比较文学》2021年第4期
转自: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摘要近十几年来,海内外学界对中国古典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之研究持续升温,但翻译底本的问题总体上较少获得重视和仔细考证,尤以《西游记》的英译为甚。作为译本研究的初步环节,讨论厘清底本问题有助于对后续问题的正确全面认识,包 括译者对小说主旨的理解和对小说版本的意识,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等等,也 可为今后《西游记》英译事业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和方向。 本文利用一手档案,结合《西游记》英译史和学术史的发展脉络,详述传教士翻译时期( 1854- 1929)、通俗化翻译时期(1930-1976) 和学术性翻译时期(1977-2012) 三个阶段各自涉及的底本问题。关键词: 《西游记》英译;翻译底本;《西游记》版本史;翻译史作者简介: 吴晓芳,翻译哲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翻译及语言学系访问学者。 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英译、西方汉学史、中国古典小说。一、 引 言近十几年来,海内外学界对中国古典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之 研究持续升温,研究者们或是侧重英译文献的稽考整理,或是探究译者的 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分析译本的语言问题、文化问题乃至译本所呈现的中国形象等等。 然而,除了《红楼梦》之外,中国古典小说英译的底本问题总体上较少获得重视和考证,尤以另一部四大名著《西游记》为甚。《西游记》成书于晚明时期,在明清两代拥有众多繁简不一、评点各异的古本,到了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陆续有学者从海外或是民间探 得失传的古本,市面上又出现许多整合一种或多种古本的读本。《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最早可追溯到 1854 年,其英译的历程跨越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阶段。① 因此,处在不同时代的译者一般依据不同时代的版本进行翻译,而绝无可能使用出版时间晚于其译本的《西游记》版本。 现有《西游记》英译研究大多忽视底本考证的环节,往往以某个现代整理本作为参照,来对比出版时间早于它的英译本,或者随意 采用距离译者生活年代比较接近的某个《西游记》版本,如此张冠李戴的研究所得出的一些结论犹如沙子宫殿,一推就倒。作为译本研究的初步环节,厘清底本问题有助于对后续问题的正确全面认识,包括译者对小说主旨的理解和对小说版本的意识,译者的翻译动 机和翻译策略等等,更可为今后中国古典小说英译事业的发展开辟新的道 路和方向。 笔者在拙文“ 两个世界的对话:《西游记》的英译与《西游记》的研究”(2019a) 已略有提及翻译底本问题的重要性,但限于篇幅,无法展开深入讨论。现利用一手档案,结合《西游记》英译史和学术史的发展脉络, 详述传教士翻译时期(1854-1929)、通俗化翻译时期(1930-1976) 和学术性翻译时期(1977-2012) 三个阶段各自涉及的底本问题。②二、 传教士翻译时期的底本问题从 1854 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 Joseph Edkins, 1823-1905) 在《北华捷报》( The North China Herald) 上发文介绍《西游记》开始,至 1930 年英国女作家海伦·M· 海耶斯( Helen M. Hayes, 1906 - 1987) 出版其节译本《佛徒天路历程》( The Buddhist Pilgrims Progress) 之前,是《西游记》英译史的早期阶段。 这一时期共有 13 位英美人士将《西游记》译为英文,①但尚无出现华人译者。 因来华传教士是这一时期译介《西游记》的主力军, 首个节译本也是出自传教士之手,故笔者称此一阶段为传教士翻译时期。前人研究在讨论这一时期的《西游记》英译文( 本) 时,常以明代的百回繁本或清代的第一种版本《西游证道书》作为底本参照,然而却未意识到,除了收入在《四游记》的杨志和简本以外,现知的明代绝大部分版本在清末已湮没不传,而清初的《西游证道书》在《西游真诠》问世后也被盖过风头,渐渐失传。 根据孙楷第、郑振铎等学者的观察和记载,清末民初通行的《西游记》版本主要是《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西游原旨》这 3 种清刊本( 孙楷第 134)。1931 年,孙楷第在日本访书时才发现世德堂本( 以下简称“ 世本”)、李卓吾评本、朱鼎臣简本等 5 种明刊本和证道书这一清刊本。 因此,受文献失传的制约,清末民初的在华西人难以目睹到早于《西游真诠》的版本,如福开森( John C. Ferguson, 1866-1945) 在“ 关于西域之行的书籍”( Books on Journeys to Western Regions) 一文中就谈到,他见过的最早的《西游记》版本是康熙丙子( 1696) 刊本《西游真诠》( Ferguson 65), 该本也是现存最早的真诠刊本。事实上,《西游真诠》作为清代最流行的本子,被这一时期的不少译者选为翻译的底本, 如前述艾约瑟在《北华捷报》刊登了“ 论佛教在中国”(Notices of Buddhism in China) 一文,该文首度向英语世界读者介绍了以玄奘的生平和历险为蓝本创作的长篇小说《西游记》,介绍其又名《西游真诠》( Si-yeu-chin-tsuen),是当时广为传阅的小说。1905 年,英国传教士惠雅各( James Ware, 1859-1913) 在《亚东杂志》( 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 上发表了“ 中国的仙境” ( The Fairland of China),也是以《西游真诠》为底的概述性译文;惠雅各还引用尤侗的序言和陈士斌的点评,阐述了《西游记》的主旨和思想。 虽然清末民初市面上流行的《西游记》版本不止《西游真诠》这一删本,尚有繁本《新说西游记》等,但传教士翻译时期的绝大部 分译者并无意识到版本之间的具体差异与版本问题的重要性。正因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版本流传情形比较复杂,翻译研究者在判定某 一译本的底本之前,必须对《西游记》本身的版本史,乃至与小说相关的戏剧、宝卷等其他形式所载的西游故事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过去,学界通常将《西游记》 的最早英译文归于 1895 年美国传教士吴板桥( Samuel I. Woodbridge, 1856 - 1926 ) 翻译的《 金角龙王, 又名皇帝游地府》 ( The Golde-Horned Dragon King or The Emperors Visit to the Spirit World),认为吴板桥选译的片断出自《西游记》通行本第十回和第十一回。 经笔者考证,吴板桥并非根据《西游记》译出,而是江苏南通僮子戏唱本“ 十三本半巫书” 之三《袁天罡卖卦斩老龙记》( 吴晓芳 2018c:147-152)。 将《金角龙王》对比《西游记》通行本相关章回可发现,吴板桥的译文增加了许多小说 中并不存在的情节,人物的形象也有很大的改变,例如:龙王在卜雨一事上 以头颅与算命先生打赌;龙王赌输后,在算命先生的提议下,用奇珍异宝贿 赂唐王,后者见财起意,收宝许诺;后来,因龙王冤魂状告阎王,唐王魂游地 府,而地府的判官却偷换龙王和唐王的阳寿,使唐王得以还阳。 诸如此类差异在僮子戏唱本皆可找到源头。 学界一般认为,巫书中的西游故事产生在“ 世本”《西游记》之前,作为素材被后者吸收,反过来又受到后者影响。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金角龙王》不能当作《西游记》的译文,将其视为小说以外的“ 西游” 故事的译文是比较妥当的。 虽然吴板桥不是据《西游记》翻译,但据笔者分析,他在翻译巫书之前已阅读过《西游记》,并且参考 小说相应的情节补充译文,令叙事逻辑紧密勾连( 152-155)。 同样是包括唐太宗游地府的神怪故事,相比在西人中间知名度更高的四大奇书之一《西游记》,《袁天罡卖卦斩老龙记》这部地方性的祭祀仪式剧本最终吸引吴板桥提起了译笔,原因不仅仅是译介中国的神怪故事有助于西方人了解 中国人的思想状态,更重要的在于,这个在唐王和冥判的形象上存在巨大 落差的神怪故事有利于向传教士读者营造一个负面的中国形象,从而达到 激励传教士传播福音、宣扬其正当性和紧迫性的深层目的。 在展开故事之前,吴板桥在“ 前言” 就对中国人的思想状态定下消极的基调,在正文中一面强化唐王在巫书中被颠覆的形象,一面以司法不公的冥判场域暗讽晚清 腐化之官场,此外还配合巫书情节频繁加注,批判愚昧落后的中国民俗和 中国人的排外倾向,由此,通过译文和副文本( paratext) 向西方读者建构了一个“ 政治腐败、道德堕落、思想愚昧的中国形象”(156-163)。既然吴板桥翻译的并非《西游记》,那么最早将小说译为英文的是何人?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西游记》的正式英译始于 1884 年,美国传教士小波乃耶( J. Dyer Ball, 1847-1919) 将其父波乃耶( Rev. Dyer Ball, 1796 - 1866) 生前译作整理加注,于是年发表在《中国评论》( The China Review) 上,其中有一篇题名为“ 海龙王和算命先生” ( The Sea Dragon and the For- tune Teller),讲述的同样是龙王触犯天条被斩、唐太宗游地府的故事。 波乃耶父子均未说明译文所据何本,据曹原考证,波乃耶使用的底本不是百回本《西游记》,而是杨志和“ 编” 的 41 回简本《西游记传》,选译了第十回“ 魏征梦斩老龙” 和第十一回“ 唐太宗阴司脱罪” ( 15 -18)。 尽管波乃耶的译文不是根据百回本译出,但仍可视为严格意义上的第一篇《西游记》英译文。自 1884 年始,《西游记》的片断英译文不断出现在近代在华英文报刊上,或是以英文撰写的中国文学史或故事选集里。 但迟至 20 世纪初,也就是在 1913 年,《西游记》的首个英文节译本才问世,为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1845-1919) 翻译的《出使天国》( A Mission to Heaven), 由其所主持的广学会(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在上海出版。 该译本近年来逐渐引起学界重视,研究者们集中讨论李提摩太如何运用基督教的教义和思想解读《西游记》,特别是如何通过文本叙事制造阿弥陀佛、如来佛和观世音这 3 位佛教圣者与基督教的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关联。① 遗憾的是,前人对译者采用的中文底本并没有仔细考辨,对此长期存在错误的认识。 笔者借助新发现的档案和古籍等资料,从译本的插图和文字两方面对照原书的版本系统,考证出李提摩太使用的底本为清末上 海广百宋斋校印的《绘图增像西游记》②,该版本实际上也是《西游真诠》的一种翻刻本( 吴晓芳 2019b:3-22)。 值得指出的是,李提摩太对底本的选择与他将小说的佛教元素基督教化的翻译策略有深层关联。 译者从《绘图增像西游记》所配的大量插图中选取了 25 幅人物绘像和故事情节图收入译本,唯独对如来和观音 2 幅绣像进行巧妙的改造,将两位佛教圣者的护法动物大鹏鸟和白鹦鹉统一替换为象征基督教圣灵的鸽子,以此建立如来 与耶稣、观音与圣灵的关联; 同时, 他明智地弃用原画师误写为“ 阿弥陀佛” 的弥勒佛绣像,选用来自日本的阿弥陀佛画像,以匹配基督教的上帝(25-37)。 要之,李提摩太通过增插图像和修改原图细节,令译本的图像叙事紧密配合文本叙事,力图证明《西游记》是“ 建立在深刻的基督教理念之上”( Richard 343),体现了基督教“ 三位一体” 的核心教义。李提摩太具有首创之功的节译本对后来的一些英译者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英籍加拿大女作家丽莉· 亚当斯· 贝克( Lily Adams Beck, 1862-1931) 在 1923 年根据李氏的节译本而非中文原本,将《西游记》编译为英文,收入其东方民间故事集《彩虹的芳香及其他故事》( The Perfume of the Rainbow and Other Stories) ①。 贝克不仅在《西游记》诗词的翻译上借用李氏的译文,在佛教语汇的翻译上也沿用李氏某些“ 以耶释佛” 的译名, 比如将“ 观音” 译为“ Holy Spirit”( 圣灵),将“ 如来” 译为“ the Incarnate”( 道成肉身的那位),将“ 弥勒佛” 译为 “ Messiah” ( 弥赛亚)。 正如下文指出,身为贝克在日本旅居期间的私人秘书,海耶斯在 1930 年出版《西游记》节译本时,也借鉴利用了李提摩太的译本。在传教士翻译时期,有不少译者注意到“ 西游” 故事的宗教意蕴,但惟有吴板桥和李提摩太这两位译者比较清楚地表明了对《西游记》及相关叙事所蕴含的宗教( 主要是佛教) 思想的态度。 这两位均是在 19 世纪后期入华的新教传教士,他们继续开垦第一代新教传教士的未竟事业,并且在华 活动时间都长达 40 余年,亲历了晚清至民国的风云变幻。 有趣的是,他们对待“ 西游” 故事和中国宗教文化的态度、翻译“ 西游” 故事的动机截然不同,背后也反映了 19 世纪末期开始在华基督教基要派和自由派在神学立场和传教路线上的差异。② 吴板桥走的是偏向福音传教的路线,即把传播福音当作中心,把灵魂的拯救放在首位。 他倾向于将巫书中的“ 西游” 故事看作一面反映中国宗教信仰、民间习俗和道德观念的镜子,并将译作当作批判异教信仰和习俗、激励传教士以福音拯救中国的方式。 而李提摩太走的是偏向文化传教的路线,在传播福音的同时也注重社会责任,试图推 动中国社会的改革与进步。 他倾向于将《西游记》看作大乘佛教和基督教乃名异实同的注解和诠释,并将译作当作联合佛教徒和基督徒解决中国乃 至世界的种种问题、最终在人间实现上帝之国的途径。 有一点相同的是, 这两位译者均通过选择合适的翻译底本、操控与改写文本( 包括插图) 来实现自己的传教目的,两者对“ 西游” 故事和佛教元素的翻译均是具有强烈功利性和政治性的文学利用。三、 通俗化翻译时期的底本问题自 1930 年海耶斯的节译本出版开始,至 1977 年芝加哥大学余国藩教授( Anthony C. Yu, 1938-2015) 的全译本第一卷问世之前,是《西游记》英译史的中期阶段。 这一时期共有 11 位中西人士将《西游记》译为英文,① 其中多达 6 位是华人,与前一时期西方译者一枝独秀的情况迥然有别,甚至出现了华人与西人合作的译本。 在以往占有群体优势的传教士译者在这一时期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学者、作家和职业翻译家。 这一阶段不仅有不少载于故事集、文学杂志和文学选集的片断译文陆续问世, 而且出现了多部针对一般读者的通俗化节译本,如海耶斯的《佛徒天路历程》、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 Arthur Waley, 1889-1966) 的《猴》( Monkey) 和捷克翻译家乔治· 提纳( George Theiner, 1926 - 1988) 的《猴王》( The Monkey King)。 综合以上因素,笔者将这一阶段称为通俗化翻译时期。②正如笔者在拙文“ 两个世界的对话:《西游记》的英译与《西游记》的研究” 中指出,《西游记》英译史的通俗化翻译时期与《西游记》学术史的现代阶段正好相合。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先驱,胡适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叶对《西游记》的考证开启了《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型,在《西游记》的成 书、作者和主题等问题上发表了一些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观点。 这是胡适提出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一个具体实践,其另一实践就是指导亚东图书 馆用新式标点重印一批包括《西游记》在内的经典白话小说。 需要说明的是,胡适在《西游记》上的研究成果是渐次累积而成的:他先于 1921 年 12 月作一篇“《西游记》序”,收入同年亚东图书馆发行的《古本西游记》;1923 年 2 月,胡适搜集到更多的材料,整理成“《西游记》考证”,发表在当年《努力周报·读书杂志》第 6 期,确立明人吴承恩作《西游记》之说,但因篇幅所限不得不删去文章一部分;同年,胡适乘亚东图书馆再版付印《古本西游记》之际,把前述两文“ 合并起来”, 遂成今日所见之长文“《西游记》 考证”;该文后又被收入 1924 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文存二集》( 竺洪波2006:110-112)。 在胡适的背书下,亚东版《西游记》 在民国时期的众多《西游记》读本中自然脱颖而出,风行一时,截至问世 12 年后,也就是 1933 年,该读本已再版到第 8 版。 不过,民国时期出版的《西游记》读本中,绝大部分是以清代的《西游真诠》或《新说西游记》为底本进行排印,如亚东版《古本西游记》依据的是《新说西游记》,而 1936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系列出版的《西游记》读本依据的则是《西游真诠》③。前人研究在讨论这一时期的《西游记》英译本时,也常以明代的百回繁本、清代的某一删本或是现代的某一整理本作为底本进行参照。 但正如前文指出,《西游真诠》之前的明清珍本在国内失传已久,直到 1931 年才被孙楷第在日本寻得。 然而,这些明清珍本因庋藏于中日少数图书馆或私家手中,对一般人来说不易经眼。 特别是“ 世本” 这部今见百回本《西游记》最早的足本,虽已于 1933 年由北平图书馆( 下文简称“ 平馆”) 从日本购回,但在日军侵华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该本在“ 七七事变” 之前已随其他平馆善本书籍迁至上海租界区保管,1941 年又被送至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 直到 1965 年才运返台湾( 谢文华 54 - 56)。 包括“ 世本” 在内的这批善本于“ 珍珠港事变” 之前运抵美国后,国会图书馆曾协助将之摄制微缩胶卷, 并赠送中国图书馆 3 套( 钱存训 65 - 75)。 下文提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年出版的整理本《西游记》,即是根据此套胶片版“ 世本”,并参考当时所能见到的 6 种清代刻本会校排印而成。 迟至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幸而有大陆和台湾一些出版社采用原本影印的方式,“ 世本” 等一些明清珍本《西游记》的原貌才能进入学者和普通读者的视野,如台湾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系列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系列分别在1985、1990 年推出了“ 世本”、李卓吾评本和《西游证道书》的原版影印本。故此,在 1954 年之前,海内外人士实属难以接触到《西游真诠》之前的版本而据此翻译。作为开启《西游记》通俗化翻译时期的译本,海耶斯译本的重要性在过去长期为学界所忽视。 在笔者发表相关研究之前,学界仅有 2 篇简单的文章讨论此译本,在底本问题上也未能做出确切的考证。① 笔者利用在日本、英国和美国等地发现的大量一手档案,考证出海耶斯的身份与生平,还原了她翻译《西游记》的缘由和经过:海耶斯出身于加拿大一个普通的英国移民家庭,被崇尚佛教的贝克夫人聘请为私人秘书,跟随其定居在日本 京都,与山边习学(1882-1944)、铃木大拙(1870-1966) 等京都佛教学者交流颇为密切;受贝克著译佛教题材作品的启发,海耶斯提笔将《西游记》这部取材自佛教徒取经故事、在东亚广为流传的中国小说译为英文;由于海耶斯的中文其时尚处在初学阶段,故而在翻译《西游记》时一面参考李提摩太的英译本,一面在有汉文功底的山边习学帮助下,使用附带胡适考证 长文的《古本西游记》( 吴晓芳 2018a:248 -268)。 海耶斯在译本导言里对作者吴承恩的生平、小说成书的过程和孙悟空原型的简介,皆参考自胡适所写的考证长文,可以说是最早引用胡适研究成果的西人。 和贝克的情况很相似,海耶斯的译本在部分地方也直接袭用李提摩太的译法或者稍加修 改,最明显的表现在诗词①、专名和《圣教序》全文的翻译上。 甚至其译本护封上的唐三藏画像也是选自李提摩太译本的插图,而后者实际上翻刻自 中文底本《绘图增像西游记》。 尽管海耶斯借鉴了李提摩太的译本,但并不认同后者对小说佛教元素的基督教诠释, 而是正面对待和处理《西游记》的宗教元素,扬弃和发展了李提摩太对《西游记》佛教思想的欣赏和重 诠。 她将小说视为一出“ 寓庄于谐” 的佛教寓言,并在禅宗大师铃木大拙的影响下突显《西游记》的禅宗思想,乃至将“ 道在尿溺” 的一面原原本本地展示给西方读者(269-301)。在通俗化翻译时期,另一个有代表性的节译本当属韦利翻译的《猴》, 其至今广受赞誉。 同海耶斯一样,韦利也视胡适为《西游记》研究的权威学者,并且与胡适是亦师亦友的关系。② 韦利在译本序言里明确说,他“ 使用的底本是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1 年出版的《西游记》,该书附带驻美中国大使胡适博士所作的长篇学术性序言”( Waley 10);与海耶斯一样,韦利也采纳胡适的研究发现,在译本序言中较为简略地介绍作者吴承恩的生平、小说的演化历史等问题。 正如上文所分析,胡适在为初版《古本西游记》所作的序中,尚未提出吴承恩作《西游记》之说,但他在 1926 年欧游期间, 曾拜访韦利并赠之一本《胡适文存二集》( 胡适 2001:444)。 因此,韦利除了使用初版《古本西游记》进行翻译之外,在撰写译本导言时也参考了收入在《胡适文存二集》的“《西游记》考证” 长文。海耶斯在 1930 年翻译《西游记》时,孙楷第尚未发现“ 世本” 等明清珍本,故而海耶斯未能知晓这些珍本的存在。 及至十余年后,韦利在二战时期英译《西游记》时,在时局动乱的情况下,他也未能接触到“ 世本” 等明本;但作为当时中国典籍方面的权威译者,他已经意识到版本对小说研究 的重要性和对翻译的潜在影响。1941 年,韦利曾致函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提到正在以亚东版读本为底本英译《西游记》,并表示听闻孙楷第在日本发现了一些明代版本,但不知具体内情,想请教胡适明本与亚东版所依据的清本是否差异很大。① 虽然胡适答复韦利的信可能已不存,但是大概可以推测,胡适应该会提到,孙楷第发现的几种明本除了朱鼎臣简本以外, 概无清本所载的第九回唐僧父亲陈光蕊的故事,因为第九回这一重大的问 题最早已由孙楷第在《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中指出(148),而该书的序言正是胡适所作。值得说明的是, 韦利在翻译《西游记》 时, 手头上除了亚东版读本以外,还有同一时期出版的其他现代读本。② 而韦利之所以选择以亚东版为底本进行翻译,而非手头上的其他读本,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胡适对亚东 版《西游记》的背书和作序。 实际上,韦利截至 1940 年的藏书中不仅收藏有一系列胡适指导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古典小说,③而且他本人极为崇敬钦 佩胡适的学问,即使胡适后来就任驻美大使,韦利在前述请教胡适的信中, 仍然将其视为一位“ 学者”,而不是一位“ 外交官”。④ 另外,在《西游记》的英译上,胡适对韦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韦利对翻译底本的选择上,更体现 在韦利对小说情节的节选和诠释上。 胡适在为初版《古本西游记》所写的序言中,极力反对明清评点者对《西游记》的儒释道寓言解读,力主小说并无“ 微言大义”,主要是一部“ 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 ( 1921:22 -23)。 韦利在译本中也选择尽量淡化原作的宗教意味,删除与“ 修心” 有关的重要情节( 如浮屠山玄奘受《心经》一事) 和比喻,不译宣扬佛教思想和渲染佛教法力的情节,并剔除与五行炼丹有关的内容。 同时,韦利又彰显孙悟空无所畏惧、智勇双全的正义英雄形象,将译本命名为“ 猴”,迎合了二战时期读者对个人英雄主义作品的喜爱和需求。四、 学术性翻译时期的底本问题从 1977 年余国藩陆续出版 4 卷全译本开始,至 2012 年余国藩完成修订版全译本,是《西游记》英译史的成熟阶段。 这一时期出现了余国藩和詹纳尔( W. J. F. Jenner, 1940- ) 各自完成的 2 个全译本,并且余国藩在初版译本问世 30 余年后,又于 2012 年推出了 4 卷修订版。 该译本是典型的学院派译本,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发行;首卷前有堪比学术论文的长篇 导论,在前贤时秀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集中阐发他对《西游记》 的本源、版本、作者、诗词来源、主题等基本问题的看法;每卷末又附带详细的译注,充分体现了他的学术见解。 故笔者称此一阶段为学术性翻译时期。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不断有学者从海外或民间探得一些失传的明清《西游记》珍本,但由于这些版本多以刻本线装或摄影胶卷的形式庋藏于海内外少数图书馆和私家手中,学者和一般读者难以接触到,故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了多部根据明清多种版本整合校勘而成的普及本《西游记》。1954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副牌“ 作家出版社” 之名义出版的读本( 后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以下简称“ 人文本”) 率先以“ 世本” 为底本进行校对整理,充分肯定“ 世本” 作为最接近作者原本之善本的价值,“ 世本” 之重要性由此为世人所知。 而在这之前,唯一能目睹到“ 世本” 的学者只有孙楷第和郑振铎两人,他们最早对《西游记》 第九回的问题以及“ 世本” 与其他 2 部简本的产生先后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 作为 1954 年“ 人文本” 的主要校订者,黄肃秋认为,《西游记》作者的原本中可能有第九回陈光蕊的故事,“ 世本” 之所以删去此段,原因可能如孙楷第指出:“ 嫌弃亵渎圣僧”(177)。 故为使整个“ 西游” 的故事完整,“ 人文本” 根据“ 书业公记” 本《新说西游记》补出了第九回“ 唐僧出身的故事”,将原来“ 世本” 的第九回至第十二回合并调整为第十回至第十二回,而第九回至第十二回的回目 改从《西游真诠》回目。1969 年,英国学者杜德桥( Glen Dudbridge, 1938- 2017) 却提出,《西游证道书》及此后的版本之所以含有第九回“ 唐僧出世的故事”,可能始自朱鼎臣之笔,后《证道书》或直接或间接承袭之,而非出 自原作者之手。 故杜德桥主张,嗣后若有出版《西游记》整理本,应忠实于“ 世本” 这部“ 最接近于任何原本《西游记》的版本”,将清代通行本的第九回删去( Dudbridge 170-184)。1980 年,“ 人文本” 进行了第一次较大的修订,出版社除了使用“ 世本” 复校之外,还首次利用另一个明本,即李卓吾评本进行校核;发现李评本与“ 世本” 一样删去了第九回的故事,考虑到该回“ 不像是吴承恩的原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5),便将其移出正文,排在第八回后作为“ 附录”,第九回至第十二回恢复“ 世本” 的原貌。2010 年,“ 人文本” 进行第二次修订时,李洪甫等整理者在处理第九回的问题上延续了 1980 年版的做法。余国藩在首版译本卷一的导论中即写明,其采用的翻译底本是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副牌“ 作家出版社” 之名义出版的整理本( Wu 1977:14)。 余国藩之所以选用“ 人文本”,是因为该本所依据的底本“ 世本” 有两大显著优点:其一,余国藩同意杜德桥的结论,认为“ 世本” 早于杨志和本与朱鼎臣本这 2 部简本,是“ 最接近于任何原本《西游记》的版本”,而且是远超任何前本的“ 顶峰之作”( 同上);其二,也正是因为“ 世本” 最接近于原本的面貌,它不像清代的各种刻本任意删改小说的正文,削去原书许多风 趣的韵文。 在余国藩看来,《西游记》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寓言,小说的诗词是整体的一部分,不可缺少;这些诗词除了用于描景状人和展示对 话之外,更用于“ 评论情节进展与人物个性,并时常用到宗教主题和修辞方式,有时还掺和着寓言技巧” ( 24)。 因此,余国藩对韦利译本去宗教化的解读和抹杀原文诗体的多样性颇有微词,推出一字不漏、诗词应译尽译的译本,正是为了扭转胡适对原著有偏颇的批评取向,纠正韦利译本展现给 读者的失真面目( Wu 2012: ix)。 不过,在“ 世本” 缺失清本第九回的问题上,余国藩却不从杜德桥提出的取消第九回内容的建议,按照作家版补入 了唐僧父亲陈光蕊的故事。 因为在他看来,陈光蕊故事即使并非今见百回本《西游记》最早的刊本———世德堂本———之一部分,也不能脱离于《西游记》整体的叙事,而且恰恰符合佛教“ 善恶有报” 和英雄人物注定历经磨难的传统主题( Yu 295-311)。 尽管“ 人文本” 先后于 1980 年和 2010 年进行了 2 次较大的修订,将第九回陈光蕊的故事拉出正文作为附录,恢复世本原貌,但 2012 年余国藩在修订译本时仍维持 1954 年“ 人文本” 初版的处理方法。从 1982 至 1986 年,北京外文出版社陆续推出了英国汉学家詹纳尔翻译的《西游记》3 卷全译本。 虽然詹纳尔的译本在出版时间上晚于余国藩译本,但实际上,在 1963 至 1965 年就任中国外文局译员时,詹纳尔在外文出版社的邀请下,早在 1964 年底就着手翻译《西游记》,而余国藩晚于其 6 年才动笔。① 1965 年,詹纳尔带着未完成的《西游记》译稿,回到英国利兹大学中国研究系执教。 然而 1966 年“ 文革” 发生后,外文出版社要求詹纳尔停止这项翻译工作,而当时他已完成前 30 余回的译文。 “ 文革” 结束后,外文出版社在 1978 年才再度邀请詹纳尔重启《西游记》的翻译,詹纳尔于1979 年回到北京,专事修改前 30 余回的译文,并于同年将译稿作为全译本的第一卷提交给出版社( Jenner 2016)。 迟至 3 年后,即 1982 年,第一卷译本才正式出版。 接下来,詹纳尔见国内政治形势好转,便利用 1982、1983 年 2 个暑期回到北京专事翻译第二卷,以及 1984 年和 1985 年 2 个暑期翻译第三卷,此 2 卷先后于 1984 年和 1986 年出版。 詹纳尔的翻译过程跨越了 20 余年,虽然中间“ 人文本”《西游记》在 1980 年进行了较大的修订,但詹纳尔一贯采用 1955 年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的作家版进行翻译,即便在 1980 年代续译《西游记》余下的 60 多回时,詹纳尔也没有使用修订版的“ 人文本”《西游记》。 这一点外文出版社在詹纳尔译本卷一的“ 出版说明”( Publishers Note) 中已向读者明确交代, 同时也说明选择“ 人文本”《西游记》为翻译底本的原因,即它所依据的“ 世本” 是今见百回本《西游记》最早的足本。 由于詹纳尔是根据未修订之前的“ 人文本” 进行翻译,在第九回问题上,他也遵照此本将第九回陈光蕊的故事植入正文,而非依修 订版“ 人文本” 将第九回拉出正文作为附录。自出版至今 60 多年来,“ 人文本” 可以说是“ 最通行、最权威和最具影响力的本子”( 竺洪波 2015:132),对《西游记》的普及做出重大贡献。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未久,古籍整理工作尚处于探索建设阶段,有些今天能见到的早期版本在当时或不易经眼,或尚不为世人所知,因而 1954 年“ 人文本” 初版在底本使用、文字校勘等方面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近年来,随着一些稀见版本的逐步刊布,竺洪波、曹炳建、李洪甫等学者利用这些版本,先后撰文指出“ 人文本” 在诸多方面存在不少讹误,其中就包括因疏忽而造成的低级错误,以及因校 勘材料不足而造成的失误。① 后者主要是因为当时“ 人文本” 所依据的底本,即现今保存在台湾故宫的“ 世本” 不仅有缺页和字迹漫漶等问题,本身也有不少讹误;当年整理时未能见到日本的其他 3 部“ 世本” ②和李卓吾评本等明代版本,而若有这些早期版本作为参校材料,“人文本” 的讹误应能减少。 由于余国藩与詹纳尔使用的翻译底本均是初校的“人文本”,这些讹误译者有时能够意识到,但多数情况下还是不可避免地带进了译本。 在因疏忽而造成的低级错误方面,比如第 17 回有“ 小怪巡山言祸事,老妖发怒显神威” 一句,“人文本” 误将“巡” 写为音近字“寻”,余国藩和詹纳尔分别译为“The small imp on patrol announced mishap”(Wu 1977: 357)和“When the junior demon on mountain patrol announced a disaster” ( Wu 1982: 328) ①,显然 2 位译者均主动改正了“ 人文本” 的讹误。 又如第 48 回叙唐僧遇阻通天河,有一首长篇咏雪诗上下阙之间有夹批“ 好雪” 两字,人文本却将其排入正文,余国藩的译本( 包括修订版) 和詹纳尔的译本也跟着将夹批“ 好雪” 植入正文。 在因校勘材料不足而造成的失误方面,例如第 81 回有镇海寺僧人之语为“ 一任他莺啼燕语闲争斗”,“燕” 字台湾“ 世本” 不清,“ 人文本” 作“ 鸟” 逻辑不通,因“ 鸟” 为“ 莺” 的上位词,而浅野“ 世本” 作“ 燕”,当是。 余国藩跟随“ 人文本”,将此句译为“We leave those orioles and birds to chatter and bicker by themselves”( Wu 1983:93),而詹纳尔译为“ Let the orioles sing and other birds chirp in idle strife”( Wu 1986:269),显然詹纳尔意识到“ 莺” 与“ 鸟” 不能作为类义词并用,但又未能参考到其他早期版本,于是处理为“ 莺” 与“ 其他的鸟儿”,以使逻辑成立。五、 结语正如苏珊·巴斯奈特在“ 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 ( 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 一文中指出,20 世纪 70 年代埃文·佐哈尔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 the polysystem theory) 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然而对这一研究路径的批评集中在“ 将研究者的注意力转移到目的语系统,而过于偏离源语文本和语境”( Bassnett 128)。 的确,在文化翻译理论家乃至功能翻译理论家的模式中,源语文本遭到了“ 罢黜” ( dethrone);理论家们皆强调以翻译文本为中心,着重探索译本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功能,或目的语的社 会、文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笔者认为,翻译研究不应漠视源语文本和源语文化,落实到《西游记》英译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古典小说英译研究中,就是应该重视翻译底本的考辨,厘清原本版本 之间的承继和差异,以及学术史和英译史的关联。 只有建立在这一扎实的基础上,研究者们才能正确且全面地认识后续问题,例如译者对小说主题 的理解和对小说版本的意识,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等等。深化对源语文本版本史的认识,意义不仅在于探究译者使用何种底本、为何以及如何使用该底本,更在于为今后中国古典小说英译事业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和方向。 正如曹炳建指出,“ 版本研究不仅对认识一部作品的作者和成书时代具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还在于版本研究是文本研究的学术基础,对我们认识一部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成就也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 曹炳建 2012:7)。 对翻译界而言,版本研究自然也是未来《西游记》英译事业发展的基础,有助于深化英语世界读者对《西游记》 创作背景、文本内涵和艺术特色的认识。 随着日后新资料的不断发现,选择何种善本作为翻译的底本、如何规避整理本的讹误,应该可以作为今后《西游记》新译本的努力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