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条新闻引起了网友的关注:来自中科院国家天文台FAST项目部的消息称,俗称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首次探测到快速射电暴多次重复爆发,捕捉到目前全世界已知数量最多的脉冲。科学家称,这个“宇宙深处的神秘射电信号”距离地球约30亿光年,目前已排除了飞机和卫星等干扰因素,后续交叉验证正在进行之中……
据了解,FAST由我国天文学家南仁东于1994年提出构想,历时22年建成,于2016年9月25日落成启用,是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绝对是值得每一个炎黄子孙骄傲和自豪的“大国重器”。
最近读狄葆贤的《平等阁笔记》时,恰好看到几则百年前的“天眼”故事,虽然与FAST毫无可比性,但却让人深切地了解并感受到百年来国人在接受科学的过程中经历的种种曲折和走过的条条弯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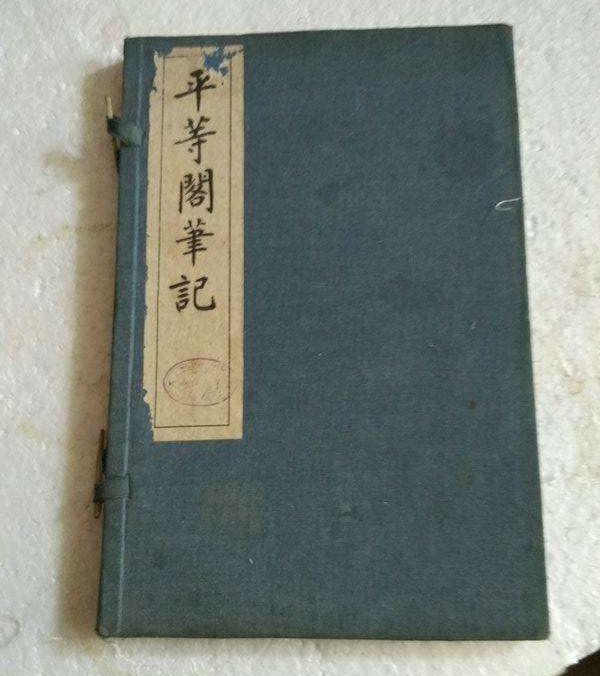
《平等阁笔记》
一、“指壶为鸭”有原因
毋庸置疑,中国近代史是一段饱含血泪的屈辱史,但同时也是一段逐渐向世界先进科技和文化敞开怀抱的开放史。从晚清民初的笔记不难看出,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对西方的一切都是好奇的,渴望从新鲜事物中汲取养分的心情是那么炽烈,以至于不分良莠与真假,对很多“伪科学”也是开门纳之,其中就包括“天眼通”。
“天眼”本是道教和佛教用语,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修行,可以在印堂那个地方再打开一只可以看见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第三只眼睛。从宗教和哲学的角度,这样的理念无可厚非,但是晚清颇有些笔记中记载:一些俗世奇人突然开了天眼,从此变成了能隔墙观物、千里闻音的先知,只是多了一个听上去非常“科学”的名字,叫做“通脑术”。
当时对此迷信最深者,是著名学者严复。“欧洲有通脑术者,如吾人在复室内画一物,此术者在外室,能照式画之。”《平等阁笔记》记他曾经偕友人同往试其术。友人在室内画了一把银壶,通脑术者在室外说:“是一只银光闪闪的鸭子。”严复说这不是错了吗?友人说不然,我画银壶时觉得它很像一只鸭子,所以通脑术者才有此误会,却也愈发证明这奇术真的可以“通脑”。
著名报人汪彭年亦信此术,他有个朋友,在江南候补道那里做司事,此人能燃香在空中作画,然后其子就可以娓娓道来乃父所画为何物。汪彭年将这位朋友带到里屋,让他画上海的青莲阁,出屋后朋友未发一语,燃香画画,“小儿曰:见有三层高大之洋楼,有多人吃茶,有‘青莲阁’字样。”这让汪彭年惊诧不已。
通过新闻纸的传播,狄葆贤得知,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还有很多此类奇人。比如比利时有个名叫鲁恩登的,“一煤矿夫也,素不识字,现年六十六岁,忽得千里眼,能视人所不能视,信仰者已有十六万人,几如一派之宗教”。据说鲁恩登每天只睡两个小时,然后就起床在园子里溜达,“视四方甚为明燎,凡眼所瞩之处,如有电光随之云”。在日本还有一个名叫千代鹤子的女人,以通脑术而闻名,“举国学者争起研究其理由”,把个大和民族搞得如痴如狂。但狄葆贤却认为这事不足为奇,“其实即佛典所称之‘天眼通’,一为推阐其蕴,亦无他奇也……凡学佛者,修道得力时,则通能自现”。
二、玄奇更有“天耳通”
据《清稗类钞》记载,光绪年间,浙江慈溪有个很有名的“天眼通”。他的奇术乃是“于无意中得之”。他的天眼可不只隔墙猜物那样简单,而是“凡未来景象,荒远动作,如在目前”。有一次他坐在家中,恍惚间见到屋子突然烧起了大火,火势很大、赤焰蓬勃,一家老小“仓皇急遽奔避号啕”,左邻右舍“呐喊鸣锣奔救”。清醒后,他看到自己的居室并无一星半点儿要着火的迹象,但还是跟家人说了,让全家急图远避。家人当然是嗤之以鼻,不成想没过多久,屋子果然着起了大火,“其一切情状,与先所内视者无稍异”。于是人们都惊以为神,确信此君是开了天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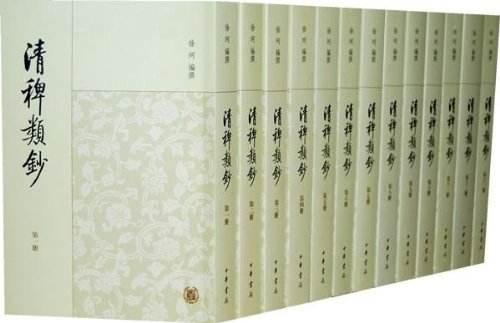
《清稗类钞》
这位“天眼通”从此名声大噪,找他算命的人不在少数。其中有个人,一向为非作歹、横行乡里,为邑人所侧目,有一天他去找“天眼通”问前程,“天眼通”送给他封好的一卷纸,说危急时才能打开。后来此人害死邻居老妇,被逮于官,自知无生理,突然回忆起“天眼通”所赠那一卷纸,赶紧让家人打开观看:“则是案之供词批语,六绅禀稿,按察详部文卷,以及部中钉封,一一皆在。”他才知道,自己的犯案和受惩乃是命中注定之事,“乃惊蹶移时,待死而已”。
不久后,“天眼通”突然看到了庚子年的事情,先是义和团运动,之后八国联军侵入京城,两宫西幸,北中国陷入空前的灾难……“天眼通”不免伏案恸哭,没多久他就病死了。家人在他的枕畔捡到一篇文章,都不解其中之意。不久庚子国变果然爆发,家人将他的遗文再次拿出细看,原来就是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下的罪己诏。其时廷谕尚未到达省里,等到达后取来一对,“非特字意无异,并其款式、行数、纸色,亦无一少差”。人们对“天眼通”身前预知死后事的“技能”感到无比的膜拜,从此他的墓前永远有香花供奉,岁时不绝。
据《平等阁笔记》记载,还有一位比“天眼通”更加厉害的高人,名叫魏寂甫,他是近代著名佛学家杨仁山的禅友,此人“习禅定数年,一日忽得天眼通”,不仅能隔墙观物,而且连数十里外发生的事物也能得见。更加重要的是,他还能听见画面的“同期声”,也就是说在“天眼通”之外,还有“天耳通”的异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特异功能就像泡在水里的木耳,越发越大,“渐则数千里外事物,亦能见而闻矣”。结果此君看到了一场从广西发起,“由鄂而皖而苏,所有人民被杀戮之惨状,历历在目”的景象——正是太平天国运动。魏寂甫惊恐至极,见人就哭,一边哭一边喊:“大乱至矣,众生可悯,为之奈何?”人们都以为他疯了,于是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癫居士”,此人一直到死都疯疯癫癫,没有好转。
三、奇童曾入军机处?
论及“天眼通”们最露脸的一件事,大概是《平等阁笔记》里记录的“奇童侦查中法战争”了。这件事依然是杨仁山讲给狄葆贤的。说是山东巡抚奏报入京,“谓得一奇童,目能远视无碍,恭亲王奕訢下令将此童送到北京,“军机等亲为试验,问以墙外物,皆能言之历历”。当时正值中法战争期间,军机处就让这奇童面朝广西方向观测军情,小童说:“见一山,已为蓝衣兵所夺,青布包头兵败走矣!”蓝衣兵是法军,青布包头兵是清军。一听此言,军机处大惊,从此以后每天让小童观测。突然有一天,小童说:“此山已为青布包头兵夺回矣。”后来等前方战报送到京城,计其时日,一一核对,才发现小童所见,正是收复谅山的一幕。
也正是这则笔记,让笔者认定:所谓的“天眼通”只是好事之人杜撰出的故事。除了正史对此事绝无记载外,还有两个原因:第一,军机处从雍正七年设立那一天开始,就逐渐成为处理国家重要军务和政务的中枢机关,至晚清,虽然部分权力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分流,但依然是威严肃穆的权力核心。在笔记中所谈的与中法战争相近的恭王掌权期,军机处有包括恭王在内的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等五位军机大臣,抛开恭王的英明不说,这其中李鸿藻和翁同龢都是当过帝师的饱学鸿儒之士,“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圣训是一刻都不敢忘的,遇到旁门左道斥之唯恐不及,怎么可能会允许把什么奇童带到军机处这样的地方来考察?更加重要的是,编造这则故事的人,显然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当时政坛上的一件大事,那就是“甲申易枢”:慈禧将以恭王为首的军机处全班尽行罢斥,逐出权力中枢。据《清通鉴》记载,甲申易枢发生在甲申年(1884年)农历三月十三日,而收复谅山是乙酉年(1885年)农历二月的事情,就算小童是恭王招来的,被罢斥后由新任军机大臣的礼亲王世铎等人接着“款待”,等于在国家权力中枢养了一个旁门左道之士近一年——真要有这种事,新的军机班底恐怕早就被清流派的御史们参得底儿朝天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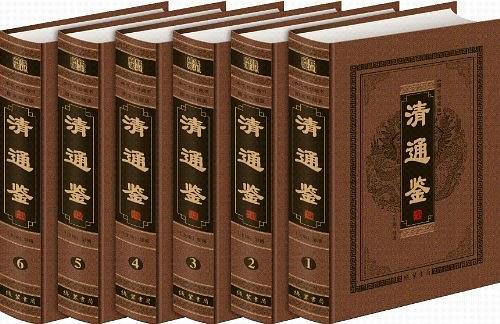
《清通鉴》
事实上,所谓的“天眼通”(这里指世俗意义上的隔空观物和对未来世界的预知能力),乃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伪科学,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参与者中的“托儿”事先向“开天眼者”泄了底,比如那位“指壶为鸭”的友人,很可能就是“通脑术者”的托儿;还有就是为了掩饰患有精神病的家属的症状,避免乡里乡亲的戳戳点点,而编造出的一套子虚乌有的胡说八道,把“事后诸葛亮”变成“事前刘伯温”,比如魏寂甫和那个预言庚子国变的人……著名反伪科学斗士詹姆斯·兰迪曾经拆穿过大量“天眼通”的骗子,他指出,有个名叫泽内尔的心理学家设计了一套卡片,在卡片上标记了圆圈、乘号、波纹线、方块和星号,在严谨的条件下测试“天眼通”们的透视能力,可是几十年中的无数受试者,每个的正确率都跟瞎猜差不多……
至于那种预知能力,简单地说,读者只要记住“概率”两个字即可,由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发生的事件层出不穷,所以任何人只要随便说上几句模棱两可、语意含糊的话,都不难在未来的一年、两年、十年内得到“验证”。如果再把时间的长度无限延长,那么你预测的事情能“对上”的机会将会更多,比如笔者现在随便敲上几句:“西方有怪鸟,衔日月当空”、“遥见一人火星来,竟是邻家第二子”、“返老还童应无恙,巨城宛在海中央”……不出一百年,都能找到应验的事或物——不信,每个读者都可以试试看,你也能成为诺查丹玛斯的,只要大家都能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