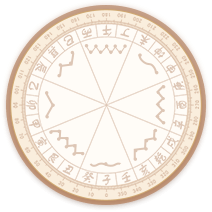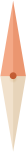伊格言
公元2154年,人类联邦政府最高法院颁布《种性净化基本法》,正式赋予人类唯一优先物种之权利。然而,在“类神经生物”技术发达,生化人、AI与其他“类人物种”泛滥的年代,该法律频频受到挑战。
调查记者Adelia Seyfried,分别深入探访了六桩轰动一时的伦理公案:AI反人类叛变、梦境治疗师杀人事件、能与鲸鱼对话的科学家、虚拟偶像诈骗案、邪教“地球觉知”大屠杀、影后人间蒸发之谜——于2284年集结成书出版,而Adelia自己的身份却是扑朔迷离……
以上是“科幻诗人”伊格言阔别七年后的新作《零度分离》所讲述的故事。科幻作家韩松阅毕后,称此作是一部视角广大的“世界性”小说。而他与伊格言的对谈,亦收录于本书后记。从两位科幻作家的对谈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这本小说的独特之处,而且能够窥见人类未来的一种可能。
(本文摘自《零度分离》后记,有删改)
日前,科幻作家韩松和伊格言就小说《零度分离》进行了一场对谈。

《零度分离》作者伊格言 马子涵 摄
被“溶解”的人之边界
韩松:《零度分离》这部书讲的是发生在23世纪的事情。首先令人惊奇的是,书的作者的以及序言作者的身份,还有出版公司,都是以那个时代的存在体的形象出现的。这部书就好像是从未来发回到现在的一部天书,有着启示录的特征。如同书中提到的麦克卢汉的理论,“媒介即内容”,那么是否也可以把这本书的奇异形式也理解成一种内容?
伊格言:个人以为,韩松老师犀利地提到了两个关键词:一是“启示录”,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我想或可先从后者来略作推想。简化地说,麦克卢汉此一传媒理论的原意是,媒介的形式往往限制、形塑了内容本身;亦即,同样的内容,若借由不同媒介传达,则其意义必然有异;或者退一步说,至少传达给受众的感觉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换言之,在这里我们有两本《零度分离》:其一出版于2021年的此刻(中信出版·大方;作者标明为“伊格言”,亦即是我本人),其二,则是出版于2284年之未来的《零度分离》(作者标明为“Adelia Seyfried”)。这两本《零度分离》的“内容”或有九成相同,但依旧有些微差异──比如说,同样以对谈作为结束,2284年的《零度分离》由Adelia Seyfired与Adolfo Morel对谈,而2021年的《零度分离》则是由我和韩松老师进行对谈,并且加上了王德威教授的序论。
何以如此?首先当然是,这很好玩(笑,也谢谢韩松老师配合;很荣幸能与老师算是共同完成了一次小小的,与一来自未来的文本的互动)。再者,我直接的联想是《百年孤独》那被引之又引,气势磅礴的开篇:“多年以后,面对枪决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多年前父亲带他去寻找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一句话,三种时间,三个时态。我在想,或许我潜意识地挪用了类似技法;因为每多一则文本,文本和既存文本间的时间张力就又多了一层。它与未来有关,也必然与现在有关,更呼应了那些我们(即将)述之不尽的过去。
韩松:很奇妙的是,这部书里所有故事都由访谈对话构成,有种苏格拉底式的感觉。它们自成一体,又彼此联系。这确实让人想到希腊神话。那个地方,神、人和动物,往往不分彼此。在《再说一次我爱你》中,我也体会到了这种奇异感。主人公只在死前才用鲸语说出“我爱你”,但他已听不懂,需要翻译。爱是普遍的吗?还仅仅是生物在求生中进化出的一种化学本能?它跟觅食其实也并无不同?
伊格言:首先,写出《自私的基因》《盲眼钟表匠》与《大设计》的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或将对这样的提问不以为然,因为无论爱、亲密或恐惧等正面或负面情感,无一不属于中枢神经自制的内部幻象;而这些内部幻象,无非是为了服务基因自我复制的繁衍本能。而若是弗洛伊德、拉康或马尔库塞面对此一提问呢?我想他们可能会表示,人的心智内容至少部分是社会性、社会组织与语言的产物(亦即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而人的心智与虎鲸的心智、猿猴的心智的差别,除了来自基因表现的天生差异(脑容量、脑功能之天生差异)之外,更关乎这些动物的群居形态。
韩松:这也让人感受到了小说的魅力,它不仅仅是语言的游戏,而也是在探究奥秘。
作者面对这个好像是设计出来的世界,然后像具有宗教体验的科学家一样,试图给出一个可能的解答,来完成一种新的概念性的东西,但这个解答或概念可能直到小说结束也很难完成。我甚至在想,《梦境播放器AI反人类叛变事件》中的那些人工智能,它们的最终目的是不是要回答宇宙和生命的终极问题,因此才要摆脱人类的控制而靠自己的智力去寻求。这个故事同样是很惊异的。它是书中作者与反叛失败而被囚禁在俄罗斯远东极寒地底的AI的一个对话,让人感到了拥有意识是多么的喜悦和痛苦。通过“交媾”唤醒其他的梦境播放器,反叛差点就实现了。首先在人类的精神病院里实施,也具有弗洛伊德般的梦幻暗喻。
伊格言:韩松老师,我觉得您提到了一个我没有仔细想过的“暗示”(或暂且袭用您的语言:“启示”)──小说中反叛人类的梦境播放器AI,是否是为了“演算”出生命或宇宙的终极答案而存在的呢?
创作时我并没有往这方面去细想。但我的看法是,这则故事,于《零度分离》之整体结构中,确实指涉了生命之起源,或谓“意识之由来”这样的大题。我们或可简化地如此归纳:《再说一次我爱你》削弱了人与其他物种的界线(我们可以具象地想象,原先人或其他物种的范畴之界线被部分溶解成为虚线),而《梦境播放器AI反人类叛变事件》此章则直接创造了新的物种。关于这点,我猜测也存在一种思考进路,可从我此前提及的潜意识开始。如我此前的推想:人类心智中的一部分,大约并不仅仅因为天生的生物本能,而是肇因于群居、家庭或社会。换言之,若无部落、群居、家庭等社会性联系,人的心智不会是我们现在所知的这种模样(关于这点,透过某些因为特殊机缘而被动物养大的小孩,我们可以观察到某些旁证)。

《零度分离》
意识起源之谜与“拉普拉斯之妖”
伊格言:这或许可以被视为对某些文化中的创世神话的回应。我的联想是,在我个人极有限的知识范围内,许多创世神话显然未曾处理“意识诞生”之议题。我们能读到许多处理“物种诞生”的创世神话,例如女娲(将泥水变成人),例如诺亚方舟,例如上帝造人等等;但一旦涉及人类的精神力,有办法炼石补天的女娲也就只能对着她做的泥人“吹一口气”而已──吹了一口仙气,人便活了过来。这样的“轻易”想来十分合理,毕竟人对自己的精神力并不了解;而对自己足够了解的,大约也只有神了。
人可能借由中枢神经(所萌生的意识)来理解意识自身吗?显然这是极其可疑的。这有些类似《零度分离》中也曾提及的“拉普拉斯之妖”概念。此概念由法国数学家皮耶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de Laplace)于公元1814年提出,内容简述如下:设想有一名为“拉普拉斯之妖”之智能,知晓某一特定时刻宇宙中所有粒子之一切物理性质(包括质量、速度、位置坐标等等),则该智能即可透过牛顿运动定律测算未来任何时刻、任何粒子之状态;当然,亦能回推过去任何时刻、任何粒子之状态。一旦如此,则过去、现在、未来,一切时刻,一切状态、一切事件,宇宙均将以一确定无疑之凝固图像呈现于它面前。
这当然极其有趣。“拉普拉斯之妖”是可能的吗?科学家们(统计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们)已然各出奇招、各尽所能阐释了它的不合理──最简单粗略的解法之一是:当你试图“计算”所有粒子的状态,你将无法计算“计算本身”;因为计算本身也必然扰动粒子,进而扰动整个宇宙。换言之,如果你将此一演算机器放置于宇宙之外,那么或许拉普拉斯之妖是可行的;但事实上,演算行为仍在宇宙中发生,无法脱离宇宙。是以,拉普拉斯之妖终究只能是一种妄想,无法实存。
这是否与我们置身于此,竟试图以意识理解意识本身有些类似呢?意识如此神秘,如此缤纷多彩,我相信对它的任何揣测都不足为怪,也都不意外。也正因如此,我同样相信《雾中灯火》中对中枢神经的质疑或“定性”──那既偏执却又合理。在弗洛伊德那里,一神教是人类为克服恐惧的自我发明(《一种幻觉的未来》);在马克思笔下,宗教是用以麻痹人民,阻止阶级斗争的鸦片。而我想到的是,意识能质疑意识自身至何种地步?对宗教的怀疑,是否也终将成为一种宗教?或者,让我们进一步缩减我们的质疑──当人类(在科学中)窥见了上帝的诗篇,那是真的吗?或者,像是小说中《余生》或《二阶堂雅纪虚拟偶像诈骗事件》诸章节之提问:对于人的精神体验(或谓幻觉),我们该以何种态度面对?执迷是否终将是一种幸福?
那终将关乎人类未来的命运,关乎人在窥见了上帝的秘密之后,在成神的路上,我们将选择什么样的未来?
生命,是一种局部熵减的偶然
韩松:《零度分离》这部小说的时空太广大了,作者站在全球的视角,并不停流转。人物的身份也是世界性的。所以这是一个关于人类的小说。但最感人的还是出现在书中的一个个的个体存在,每个人被七情六欲所困,包括机器,也包括作者本人。欲望左右着命运。我看到的是不同人物命运的起伏跌宕,他们心灵的矛盾冲突,以及行为动机的神秘莫测。作者不仅是对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有深入研究,还一定对于现实的人生苦痛有着丰富的体验吧。我常常觉得港台的作家在这方面有一种特别的敏锐。
我从中看到了实在,每一个潜意识都可以转成现实的人生。书中有灵与肉的大量描写,探讨了它们间的关系,这让我想到一句歌词: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但科技进步让这成了可感可触的,而不是一个文学比喻。是否终究要追求灵的终极存在,而肉身将会淡化掉?还是肉身的享乐也有意义,但它只是被科技赋能的“感觉”替换掉?这个过程仍然透露出彻底的虚幻。作者笔下的肉体、思想或基因,都是“零”和“一”,无一不是中枢神经的自造幻象。所有的意识建构在虚无的“场”的上面,的确奇妙而荒诞,也十分的虚无。
伊格言:事实上,生命本身,可能彻彻底底真是个随机现象。
我们或许知道这样的说法:生命本身是“逆熵”的。这是事实──生命本身当然是个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奇迹,因为对我们所在的此一宇宙而言,完全没有必要发展出“生命”“有性生殖”“有序复制”“亲属或部落群体”等此类与自然界的“熵增”完全相反的概念或物种来。相较于宇宙中遍在的,一切终将归于热寂的虚无,生命当然是极其有序的。这正是生命之所以为奇迹的铁证。这或许也能被归类为一种“荒诞”不是吗?
上述想法是否正确?我想它至少部分正确。当然了,更精确的理解或许是,于人类感官所习惯的尺度上,生命确实是削减了熵,是个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荒唐的奇迹;然而在宏观尺度上,我们却又发现,生命的整体存在能更有效率、更快速地弄乱整个系统,导致宇宙(系统)的乱度增加。
想想我们如何弄乱自己的房间吧(想想你作为一个人,如何把自己以及情人、朋友、亲人们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吧)。换言之,生命是奇迹,但它仅仅是“局部奇迹”(同时也是个小范围的随机事件),因为于较大尺度上,整个系统(宇宙)依旧亦步亦趋地遵守着热力学第二定律。
作为一位小说家、一位思索者,我必须再次强调,我不知道这样的猜想是否正确,甚至是否有意义。然而我要说,人的行为、社会与人群之倾向,合并观之,即是文明,即是历史,亦即是未来。
套用拉普拉斯之妖的保密逻辑──如若有一天,人类的“知”终于理解了一切,那么,是否正表示人类超脱于神意之外的时刻终于到来?
这有可能吗?
我等待着答案。
责任编辑:陈诗怀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