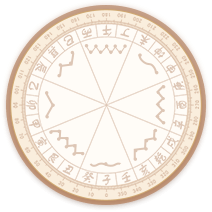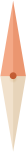(图源:IC Photo)
傅北宸/文
李开元在《汉兴》中,对当下汉朝初中期的研究和理解有两大不以为然。一是对卜相迷信说,一是对汉各种现象的儒学解释。他就学北大后久居海外,沉浸于秦汉之间,以文化传承为家乡,大环境的不同使其别具只眼,他山做石一攻而玉。上述两种他都给出了例证:后者说前武帝时代的汉朝基本上无儒学之用,无论陆贾策术还是贾谊政论,都是黄老之学;前者说明卜相在中国传统社会广泛存在于各个领域和阶层,野有卜者朝设卜官,将之归为迷信才是真正的愚昧,甚至于是对生命的轻忽。
一
一直以来,史学界以元史料所载的霸陵在白鹿原上的凤凰嘴作为公论,并立碑为证。去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线上会议公布,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霸陵,李白《忆秦娥》中“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中的“灞陵”即是霸陵(灞是霸的异体字),陵寝的主人即汉文帝。
汉文帝(代王)刘恒本人就和大多数王公皇帝一样,是一个狂热的占卜控。
楚汉战争的时候,其母薄姬还是个战乱里的姑娘,女相士许负为她看相,直接说她将来“当生天子”。为此,魏王豹娶了她,挟帝囊以证身份的意思,而且放心大胆地做变色龙:时而跟刘邦时而跟项羽,后来被韩信掳身灭国,薄姬没给他生成天子不说,还被俘虏到汉宫做了纺织女奴。各种曲折之后,被刘邦纳为姬妃,不幸的是,后宫佳丽之中,她跟刘邦只有一次同房,就怀上了刘恒。刘邦内外嫡庶共有八个儿子,刘恒排名靠中间,时称中子。从继皇帝位的考量角度看,立长立嫡立贤和他都不沾边,所以只好乖乖的去张家口的代王城做代王。
但事情总会变化的,高祖嫡出太子是老二刘盈,继位是为惠帝,长子刘肥、三子刘如意、五子刘恢、六子刘友先后死去、八子刘建早夭,到诸吕之变之后,该掷色子决定谁做皇帝的时候,刘邦的儿子只剩下他和弟弟刘长了。刘恒最终还是从代王城到长安,做了汉文帝。
陆贾所撰《楚汉春秋》载,这个女相士许负,被刘邦封为鸣雌亭侯,时年19岁。这种最牛原始股的因由即来自相术。刘邦还是大秦朝股级干部泗水亭长的时候,娶了吕雉生了一女一儿,在背儿携女下田干活的时候遇到了许负,许负给吕雉看相说她相貌主贵,又看了她的儿女说贵就贵在这一儿一女身上。后来见到股级干部又补充说,夫人和孩子的贵都出在他身上,他的命相“贵不可言”。后世有推想说许负是拍马屁,但事实上看相的时候,刘邦只是虾皮一般的行政级别,兼之四十多岁事事不成的光景,吕雉也只不过是一个带俩娃下地干活儿的农妇,许负的马屁轮不到拍这两类人。
自是之后八年,刘邦从一个村氓一跃而成开国皇帝,不能不算是一个异数。准确的相术或许是刘邦能封侯许负的原因之一,但如果因此认为刘邦作为一个政治家仅因为该个案就封赐爵位,那即是小看政治家也是小看史书,合理的推断还应该有其他相术相关的重大事件,虽然受封前许负没有其他记载。但无记载并非是没有事实。
许负被记载的还有给周亚夫看相。周亚夫是刘邦治期大将周勃的儿子,文景之治时期的大将,许负相周说其“法令纹入口”,将来会饿死,事实果如其言。
如果史载中只有许负,应该还不足以代表相士的认同普遍和社会地位,恰好大名鼎鼎的大结巴周昌亲历一事,周的老友方与公(楚国薛郡方与县,今山东鱼台的长官)以相术知名,跟周说要关照好下属赵尧,他将来会接替周的御史大夫之职。
后来周昌离京辅佐刘如意,刘邦召见近臣,拿着御史大夫印绶把玩造设问句“谁能当这个御史大夫呢?”看了一圈说“我看除了赵尧谁也不行啊。”
臧荼是汉初最早的反王之一,臧荼反叛也是汉朝诸侯王问题的开端。因为是历史的入口处,所以很难看得清楚。而事实上,臧荼的具体死讯和身后事几乎是模糊一团,唯一有载的是《史记·外戚世家》中说臧荼留有一个叫臧儿的孙女。臧儿二嫁,育有三男二女,她去算命得到的判词是“两女皆贵”,而彼时长女已出嫁且看起来低庸之至。为了响应卦辞,臧儿执意令长女离婚送至太子宫中,长女无名,史称王夫人,入宫后为太子生育了三女一男。这位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景帝刘启,而生的一男则是后来的汉武帝刘彻。行文至此,作为历史学者的李开元大为感叹“命运的转折,竟然在于臧儿的一念之间。古往今来的相命占卜,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依然神秘而不可言喻。”
《左传·成公·成公十三年》述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思是一个国家只有两件大事,即祭祀先人神祇和战争——这种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行为主线,而“祀与戎”的前提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必然进行占卜和祭祀的仪式,如《新五代史·伶官传序》所载“(庄宗)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方其……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尽管一千多年有古今中外预测、卜筮、相术甚至通灵术的无数记载,但遗憾的是,无一例外被现代主流文化“不予采信”,通斥为迷信妖祟,原因是近于谄媚跋扈的“不科学”。科学的对象是物质,而人文的对象则是思想,而社会科学的称谓本身即不科学——人文社会礼仪传统,不是科学所能涵盖和解释的。科学无所不包,已经是一种霸权。
二
中国儒学传统源远流长,但这不代表汉朝特别是初中期的汉朝儒学占统治地位,相反文化本身是一种化合、萃取和衍变,董仲舒学说确立为国教之前,汉朝推崇的是黄老之学——即黄帝老子之学。而两千年来,受独尊儒术的浸染,几乎所有的政论,都以儒家、儒学、儒生来解释汉朝的施政,而实际上陆贾所提倡的“以文守天下”的“文”是彼时盛行的黄老之学。对黄老之学,李开元表述为“以老子的道论为哲学基础,融入刑名法度思想,成就兼容并包、经世济用的思想流派。其精要可概括为:守道、依法、均衡、知变、求无为”。即便后来儒学视为正统,在统治术方面,对黄老之学都无一例外地秉承,如后世总结的“外示儒术,内用黄老”。
萧规曹随被认为是文景之治的源流和基础,文景之治的核心在于“随”,在对萧何国策不做重大更改下的修枝剪叶。随的核心执行者是曹参,而曹参就是黄老之学的承钵者。曹参在任齐国丞相期间,正式拜入盖公门下,而盖公正是黄老之学(亦称黄老道)的第六代传人。《史记·乐毅列传》中对黄老道学统这个分支做了简单的梳理,自河上丈人起历经五代,按顺序分别是河上丈人——安期生——毛翕公——乐瑕公——乐臣公——盖公,传到曹参是第七代,李开元考证除了二乐有史证,之上都是口述师承。关于口述则很难完全采信,如樊哙鸿门宴上的闯帐及对话乃至“鸿门宴的故事之所以得到流传,都是出自这位樊市人(劫后余生的樊哙庶子)的口述。”
千百年来,黄老之学的典籍佚失殆尽,后世对其认识基本是一片空白。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黄帝四经》和《老子》同时出土,而这两部书正是黄老之学的典籍,至此揭开了这门引领一个时代潮流的学科的神秘面纱,其历史意义也一步步展示开来。之前的史书中关于“盖公以黄老说曹相国”的细节是没有的,有的只有19个字“盖公为言,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李开元以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旨》为形而上之纲,以这两部新出土的书籍为形而下之目,结合萧规曹随的历史真实概况,推想并呈现了这一场景——而这种治史手法,和海外的陈舜臣、黄仁宇甚至刘子健有神似之处,而在中国学界却闻所未闻。创意和学问无分新旧,均来自历史,所以林语堂说求新学问要读古书。对此李开元落脚点是一个原理式的解释:“如何基于有限的史实,以合理的推想去填补巨大的历史空白,成了历史学家的永恒追求。”他推想的盖公说大略如是:
天下学问无外六家即儒、墨、道、法、名、阴阳,阴阳家重自然而多忌讳、儒家重伦理而博琐少功、墨家重节俭而无尊卑、法家重规责而少恩德、名家循名实而失本真、道家事功大而理深难。相比而言,治国用道家最为便捷,而黄老之学像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一样,出于道家又高于道家,是出自道论的,要旨在于“守道、依法、均衡、知变、求无为。”道就是万物之母而成万物之理,而法出于道,是道之理,道柔而无穷,法则坚而有限,所以要讲均衡;而变是道的精髓,把握了以上则自然就无为了。所谓无为不是无作为,而是基本不用作为,因为“法正道备则圣人无事”,上不折腾下不添乱,各守本分,和谐运转。由于曹参和盖公的这番晤对,曹参才彻底接受盖公的黄老之学。综观曹参在任期间的汉朝,确实是在黄老之学的统摄下顺畅运转着的,所以李开元把萧规曹随的表征扩大到整个汉朝社会,升格到文景之治的高度,称之为萧曹之治。
三
和当代中国的不结盟主义不同,公元前一世纪的中国汉朝,采取的是结盟主义。事实上是不得已,刚立朝的大汉隐患实在太多。
内部的疑肿尚未病变但需要剔除,同时外部的大患有二,一是南面赵陀的南越国,一是北面冒顿单于的匈奴。这其中陆贾居功厥伟,内部提出的不能马上治天下被刘邦采纳,这决定了大汉里程碑式的建国转折点;外部出使南越,以一人之力说服赵陀愿意成为大汉附属诸侯国。像爱哭的孩子多吃奶一样,兵不血刃虽然可贵但不易得名,后世和彼时最为关注和称颂的还是费了牛劲取了驴效的事功,这就是安抚匈奴。
史书上白登山之盟是用以代替白登山之围的,《史记·高祖本纪》里记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只有12个字“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和平要以各种形式支付代价,刘邦采取的便是歃血为盟,于是中国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和亲”一词。付出与和亲贡献的约定是:匈奴不事侵犯,不援反叛。后来陈豨反叛,匈奴并未给予援助,就是盟约的结果。这份盟约对汉朝到汉武帝为止时期的北境和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没有不带血的联盟,汉匈的血盟双方基本都算是耿直,换言之,不带血的联盟就是儿戏,有说了不算的可能——这就要说到内部最大的肿块:诸吕之变。
事变从高后八年吕雉去世开始,刘邦系的功臣勋将采取内外结合的办法解决了吕氏外戚集团。最富传奇性的情节是在内,即南北军大营的武装解除上。南北军分别负责防卫宫廷和城市,勋臣陈平等决定先解决北军,而北军的统领者是吕禄。勋臣方面找到吕禄,劝其交出兵权,平安富贵的许诺即可以盟誓兑现。然而,吕禄当然没等到许诺人的血,没等到盟誓,甚至没等到事变完成,事变突发不久他就被杀了,单方面流尽了血。诸吕之变的首起发难是齐王刘襄,打的旗号正义凛然:捍卫白马之盟,而白马之盟就正是极其郑重规范的歃血为盟,杀掉一匹白马,以血盟誓——非刘姓不封王、非军功不封侯,违反此盟,天下共讨之。
非刘氏不能封王,是毫不掩饰的家天下思想。事实上,从有封建社会至清朝完结,每一个政权无一不是家天下,故而梁启超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也。”这里暗含着一层意思是,凡坐稳皇位的都是正统,而正统记注修史,所以一切的核心和原则乃至是非评判,都以正统书写的正史为圭皋、为准绳、为绝对正确。这同时也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明显是不对的该怎么办?那只有人为删改记录,以保证正史的呈现结果正确。
诸吕之变正式名称的提出者,是北宋的司马光,在他编著的《资治通鉴》中,以标题的方式把这次政变定性为《汉纪·诸吕之变》,依据自然是刘邦正统的白马之盟中的“非刘不王”。实际上,这次政变的始作俑者不是吕氏集团,而是在京的功臣勋将联合齐王一系的皇族,为从吕氏外戚手中夺回权力而发动的政变,结果他们胜利了,胜利者掌握和接续了正统。所以,李开元基于事理,把诸吕之变改称“诛吕之变”。
历史地看,篡改历史并非汉朝的发明,历朝历代几乎所有的正史都有不同程度不同次数的篡改,而所谓信史从来都是刻板天真的愿景。这种正史的立场,即使改朝换代之后也不会动摇,诸吕之变就是典型中的典型。毛泽东评论《水浒》中宋江的一句话,最为一针见血——“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因为皇帝的正统问题是不容谈判的。
吕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帝,她不是垂帘听政,也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实实在在堂堂正正地坐在皇帝座位上施政,以高后纪年。高后四年,也同样出现了删改历史的事情:废幼帝。幼帝在历史上是没有名字的,这显得尤为诡异。史载对此事只有两句话“帝废位,太后幽杀之”和“立常山王义为帝,更名曰弘。不称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
当然,这个刘弘在诛吕之变后,也被汉文帝指认为是野种而杀,但起码有个名字。幼帝再废再死,也是一个皇帝,不应该至少有个名字么?李开元博览史书,也参与历史的编撰,知道了历史是怎么编撰出来的同时,也明白修正篡改历史的种种门径,对于这件诡异事件,他笃定地说“一句话,完全是人为抹消涂改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