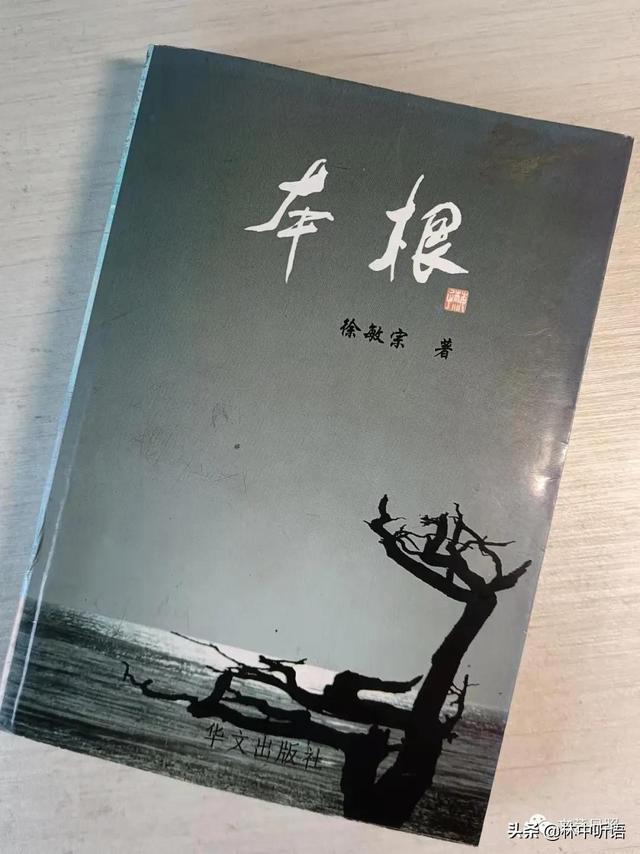
七、八十年代以计划生育为背景,以养儿防老为主题反映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本根》曾广受好评,并获得“日照文艺奖”。至今人们还记得书中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情节,而在茶余饭后津津乐道。还有多人向作者索书也有人要求再版。是的,那是一段不堪回首又多么值得回味的岁月啊!今天重看当年社会生活的艺术再现。对我们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大有裨义。因此,本公众号征得作者同意,决定开辟专栏,分期连载《本根》,每个周二四六发布以飨读者。
第 七 章
姓甚名谁
一
卢家岔小学是在雁家祠堂里开张的。
祠堂大门口两边的垛子上各挂了一块长条形木牌。一边木牌上写着:“卢家岔高级合作社”;一边木牌上写着:“卢家岔初级小学校”。白条杨木牌子虽然有些粗糙,其中一块经了一场雨后还有些变形,但上面的毛笔字写得还蛮不错,题字者显见是有些功底的。
如果“六老汉”在世,人们肯定会认为是他的手笔无疑。然而“六老汉”虽被称为“四眼”,还是没有看清世道,不相信共产党的政策,上吊自杀已经辞世九载了。那么,“高级社”和“小学校”的牌子究竟是谁的手笔呢?这在卢家岔周围的四庄八疃乃至整个慈河一带的牌牌匾匾上的题字中,是绝对可以称魁的啊!起码它可以与吕家店区公所的大牌子上的字体相媲美。
它们出自一位高人的手笔。他就是卢家岔小学的第一任教师,姓孙,名云得。此时,孙云得老师正和村支书兼高级社社长神石头高喜兴在祠堂里对小学开张作着最后的布置。
祠堂的两间西厢房一间做了合作社的办公室;一间做了民兵的夜间值班室,区里来人,也偶尔在这里过夜。神石头早已不在这里住了,他已经有了新窝,而且娶妻成家,搬到他土改时分的果实房里,像其他庄户人家一样居家过日子了。祠堂的东厢房也早已不是“六老汉”当年用来课读子孙的私塾。中间砌了一道墙,明间做了小学老师的办公室,里间正好做卧房。
祠堂正厅,如今改做了小学的教室。大厅里想当年的那些摆设,早已不见了踪影。香几上的花瓶早在土改复查时被摔碎,几上的谱册和书籍、墙上的祖谱图系以及各种字画均在那时被付之一炬。幸存下来的那张花梨木香几,后来做了村公所的文案。如今又被神石头高支书指挥着人们从西厢房里抬回祠堂正厅,做了学校的教桌。讲台下边,依次排列着用土坯支起的十几条白茬子木板,只是在尽后边放了几张白条子木桌,算是小学校的课桌了。
墙上贴有几幅红红绿绿的标语:“反对‘小脚女人’!”、“积极领导,稳步前进!”、“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等等。这是去年冬成立高级社时召开村民大会,为宣传党的有关政策贴上去的。
有人要把墙上的标语揭下来,神石头不同意,他说:“不能揭,不能揭,现在是小学堂,到时候,开村民大会,还得做大会堂,不能揭,不能揭。”
孙老师也说:“保留着也可,让学生们知道党的政策,也好做些宣传。”于是便把标语留了下来。
早有人把孙老师带来的一口铜钟,挂在了祠堂大门口的一棵老松树上。待一切布置停当,“可以开门进人”的钟声就敲响了,同大街上招呼人报名上学的锣声遥相呼应,回荡在卢家岔的上空。
二
已是初秋时节,天气有些凉,人们不得不在早晨傍晚披挂了春、秋都得上身的穿戴。
村支书高喜兴和孙老师并排坐在讲台上。他把毡帽头脱下来,在脸上抹着汗水。刚才的一阵忙碌,已使他浑身燥热,头上出汗。他要等村民们(不管入社的和未入社的)来齐后,做一下动员:“读书识字,是大好事,天大的好事!咱贫雇农不光要在政治上翻身,还要在文化上翻身。如今入了社,大家伙都富裕了,缺的就是文化。如今好了,区里给咱派来了孙教师,帮咱们孩子学文化,大家伙要拥护,大小孩伢,能上学的都要来,可别见了元宝当坎拉——不识好歹!老师同工作的一样,吃派饭,有学生的人家轮着管……”
这不,“腹稿”都打好了。
孙老师虽然也觉燥热,但他仍没有摘下来那顶解放帽。自打春上来卢家岔筹建村小,不管天凉天热,也不管忙着闲着,即使到了五黄六月,也是帽子不下头的。人们都感到奇怪,只有几个村干部见怪不怪。因为他们听区里的领导说过孙老师的身世,知道他头上有六颗怕见人的戒疤。
孙老师就是当年那位曾在莲花山青云寺主持百子殿法事的慧通小师傅。自打那次尽了“借种”的义务,从此便荒芜了向佛的心肠。特别是被贬到西禅院之后,更是破罐子破摔不再着调。这样以来,虽得养父智海法师的多方庇护,还是常挨寺中方丈的训斥。土改复查时,有恶行的青云寺和尚纷纷逃离,没有恶行的和尚也大都返乡还俗,慧通无家可还,而且愤起揭发了青云寺盘剥周围群众的罪恶,并表示愿意投靠人民政府,干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时任慈河区区委书记的杨广圣正在大办教育,帮助农民从文化上翻身,为搜寻文化人求贤若渴呢。
于是乎,孙云得亦即慧通师傅便被留在区里当了教育辅导员,巡回各村帮办冬学和民校。今年春天又被送到县文教科举办的“速师培训班”学习了半年,结业后,便被派到卢家岔小学来了。
三
就在孙老师和高支书他们在屋里做着招生登记准备的当儿,祠堂,亦即学校的院子里前来报名上学的人们已经排好了长队。有父亲来送儿子的;有爷爷来送孙子的;有爹娘同来的;有全家出动的。
雁树贤家就是这样,不仅树贤两口子来了,他的丈母娘小白鞋也来了,而且是最积极的一个。那霎,她正在吃午饭,一听见村街上有人敲锣通知,未等碗底见干,她便撂下碗筷就要拉着根根到学校报名。树贤本打算吃过早饭到猪圈濠里除粪的,见丈母娘没有带苗苗一同去报名的意思,就对老婆豆花说:“把苗苗也送去吧,新社会了,不识字咋行?总不能像俺们一样当一辈子睁眼瞎。”
豆花一边收拾碗筷一边答应着,小白鞋却说:“女孩儿家,早晚得围着锅台转。”言下之意是上不上学无所谓。豆花迟疑了一下,没有作声,树贤便决定亲自陪儿子、女儿来报名。
树贤一家来到学校院子里的时候,已经有好多人家排队站在了前边。小白鞋不怠慢,她拉着根根挤到了最前边,树贤、豆花和苗苗也只得跟了过来。小白鞋把脸贴在木格子门上,顺着封门白纸残破处的窟窿往屋里一瞅,禁不住脖子后头呲牙,暗中偷喜。她回过头来,贴在豆花的耳朵上悄悄地说:“哟,娃娃殿里的那个小师傅来当了先生啦,该着俺根根有福。”
树贤没听明白她们娘俩喳喳了些啥,只见豆花搭眼一望,脸上一阵绯红,浑身似乎哆嗦了一下。随后,豆花转身对树贤说:“我身子不舒服,家里的猪也还没喂,你和咱娘在这里等等吧,我先回去啦。”说完,不顾小白鞋的招呼,管自走了。
待高支书开门往里放人,小白鞋拉着根根抢行先来到讲台前。她对着讲台上的孙云得老师喊:“慧通小师傅。”
孙老师听了一愣。一看是小白鞋,不免心里激灵,耳根发热。正不知怎样应答。就听高支书说:“不兴乱称呼,叫……”
小白鞋像突然明白了似的,赶忙改口说:“噢噢,你看我这老脑筋,是该叫先生吧。”
高支书又给纠正说:“也不兴叫先生,叫老师,孙,孙老师。”
孙老师笑笑,也找到了话题:“对,我姓孙,孙云得,您老人家直呼我的名号就是。您是送哪一位孩子,来上学吗?”
小白鞋见问,给孙云得一个飞眼,声音高高的说:“这是俺外甥。”她说着把根根往孙云得面前一推:“根根,快,快叫……叫孙老师。”
孙老师看一眼面前这个胖乎乎、粉嘟嘟、长得蛮漂亮的小男孩,很快低下了头。他掩饰住心跳,忙问:“贵姓?”
根根把两手张开作飞翔状说:“俺姓这个。”
小白鞋喜不自禁地说:“这孩子乖,会逗人。你直说姓雁不就得了。”
高支书也在一旁说:“他姓雁,大雁的雁。”又对着树贤说:“那就是他爹,雁树贤,外号狗剩。”顺便开了一句玩笑。
孙老师望一眼雁树贤,轻轻地摇摇头,心里一紧,又问:“有学名没有?”
没等树贤和根根回答,小白鞋抢着说:“他爹爹是个土包子,哪里还能起名呼号,就求老师您给起一个吧,俺外甥可是个有出息的孩子,‘抓周’那一天,一抬手就抓了顶‘官帽’,你说说,也没有人教他。老师傅您可得给俺起个志气点的名字!”
孙老师问清了根根的辈份,沉吟了半晌,才说:“那就叫达远怎么样?雁达远。远走高飞的‘远’。”
小白鞋一听连连叫好:“俺外甥有朝一日远走高飞,一定会做官为宦的。”
这时候,树贤又把苗苗从身后拽出来,推到孙老师面前说:“老师,也给俺闺女苗苗起个名字吧,从今天开始她也是您的学生啦。”
孙老师看看瘦瘦巴巴的小姑娘,口里喃喃着:“女孩,叫苗苗,雁,雁,雁达……”
树贤听老师在那里念道“雁,雁”,赶忙告诉孙教师说:“老师,她不姓雁,她姓芦,芦苇的芦。”
孙老师听说小姑娘不姓雁倒姓芦好生奇怪,问树贤说:“她不是你的女儿吗?怎么会不姓雁?”他说着又把询问的目光投向高支书。
高喜兴说:“她是姓芦,不姓雁,她是……”
小姑娘苗苗听了,急得哭起来,争竞说:“俺不姓芦,俺姓雁!”她说着抱着树贤的腿说:“爹,你不想要俺啦,俺死了也不回姓芦的家。”
树贤说:“孩子,你哪霎都是爹的闺女,你姓芦,也是爹的闺女;你是爹的闺女,也得姓芦。你是芦家生人嘛。”
平日里,小白鞋在树贤家指手划脚争着做主,大事小情总是和树贤相左。这次却坚决的支持树贤的意见。她拽拉了一下苗苗说:“你是芦家的种苗嘛,你不姓芦算哪一条子事!”
苗苗望望姥姥愠愠的脸,已不敢大声争竞,但还是低声哀告:“俺要姓雁,俺要姓雁,俺不姓芦……”
老师听高支书解释了事情的原委,反复推敲琢磨,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名字,“芦雁春”。并解释说:“雁家的女儿,倒姓芦;芦家的女儿,可又是雁家养大的,苗者,春之征也。”众人听了都说:“妥!妥!到底是人家老师有才分。”
四
吃过早饭,跛子树仁早早地就带着儿子“神留”来学校报名。他们本来是排在前边的,但是三拥两挤,前边不断地有人“加塞子”,挨到他们进屋报名的时候,报名的队伍已经“进军”半数。
树仁本来是个急性子,遇事争强好胜,不甘落后,但解放后,火性已经收敛了不少。他迟疑着,并不急着进屋报名。这有一个不便明言的原因,那就是如何给儿子报名?儿子到底应该姓什么?
那是一个炮火遍地的年月,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从远远近近的地方传来枪炮声。鬼子被打跑了,老蒋又发动了内战,这里还成了反动派重点进攻的地方。
正值战乱,又逢着农闲,家家户户少见炊烟,清晨的村街上更是冷冷清清,很少有人走动。雁树仁刚刚办完父亲“六老汉”的葬事不久,又不得不趁着村街上没有人的当儿,到村西乱葬岗的舍林里埋葬了自己的第三个孩子——他和媳妇春杏是姑家表兄妹做亲,完婚数年,几次怀孕,孩子不是小产就是夭亡。小产的孩子多是分不清男女的一堆肉团。这一次好容易和孩子见了面,而且是个带鸡巴的,两口子大喜过望,还为死去的老爹深为惋惜。因为他们知道,“六老汉”之死,并不完全是慑于“把棍子会”的威力,也不完全是因为二儿媳的不贞不操。而且是因为“子孙不继,家道无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愧对祖宗啊!”他甚至认为这是自己前世作孽招来的报应。“天作孽犹可悯,人作孽不可活”。树仁和春杏似乎都听到过“六老汉”这样的自言自语。只是他们没有想到老爹会猝然寻了短见。两口子高兴之余还愧叹:“如果这宝贝疙瘩早来些日子,爹爹也许不会死。”不承想,宝贝疙瘩还是没好养,昙花一现就随爷爷去了。
雁树仁在舍林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埋葬好尚未来得及起上名字的宝贝疙瘩,恋恋不舍地在原地站着,默立少顷,就擦干眼泪,回头匆匆地往家里赶来。他不想让人们看到他的狼狈相,他惦记着家里悲痛欲绝的媳妇。
不想见人的树仁还是被人盯上了。
他的后脚刚刚迈进门坎,未及回头关门,就有一个黑影闪了进来。吓了一跳的树仁静神一看,原来是莲花山下尼姑庵的老尼普修。她曾多次到他家化过缘。尼姑庵败落后,她还独身一人住在破庙里,讨饭为生。春杏生养那天,她还曾上门化斋为自己道过喜。如今自己死了儿子,你又像跟屁虫似的来干什么?
普修见树仁面有愠色,赶忙解释说:“施主息怒,老尼是来求施主行善修好,收养个孩子的。孩子的娘得产后风死了,孩子爹闯了东北,老尼又养活不起,还求施主收下孩子,养一个是养,养两个也是养,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普修说着,解开尼袍,从怀里托出一个略嫌瘦弱的小孩儿,挂在胸前的红兜兜映衬着一张红红的小脸蛋儿。两只大眼睛一扑闪一扑闪,打量着正把他抱在怀里的春杏,小鼻子一翘一翘,毫不眼生的笑了,两只小手也捧着春杏的丰乳,小嘴巴拱来拱去,想含住乳头吃奶。树仁和春杏四目相视,惊疑的眼神,分明在问:“这不就是我们刚才送走的儿子吗?那小身子,那鼻子,那眼,那两只白白嫩嫩的小手手,都和自己才死去的孩儿一模一样啊。”他们裂嘴、流泪,破涕为笑。
普修老尼说:“佛祖有眼,使积善人家不会断根,这就是您的亲儿子,您对什么人也别说是人家的孩子。您要是日后还有亲生亲养,您拉扯这个孩子也会有功有名。他爹如日后闯出了名堂,也不会抹了您的养育之恩。施主,乱世遭逢,大德大罪,全在一念之差,您务必养好这个孩子。”
树仁和春杏认定自己的儿子命不该绝,尽管两口子都偷偷地去看过埋葬自己儿子的土丘丘,但他们还是相信是儿子死而复活,是投胎重生,是老天有眼,是神人打救。他们给孩子起名“神留”。是神人给自己留住了孩子。
临了,老尼姑嘱咐说:“到时候,可能有人来认子,孩子脖子上挂的小钱就是证见。”说完,趁着村街上无人,飘然而去。树仁两口子掀开小孩红兜兜看时,果见胸前用棉线挂了一枚方孔铜钱……
此时的树仁,正为孩子姓甚作难。说姓雁吧,确实不是自己亲生亲养的孩子,说不姓雁吧,两口子又视同己出,从体型相貌到脾气秉性均同自己的孩子毫无二致。村上的老少爷们也都这么说,两口子也从没对任何人说起这孩子是拾来的。再说啦,要在村上亮出这孩子另有爹娘,不仅还要有失子之痛,也会在村人面前丢尽面子,更会因无子嗣愧对祖宗。
思忖再三,树仁拿定主意:“就姓雁,说下天来,这也是俺的孩子。”
孙老师打量着面前这个瘦瘦巴巴但眉眼里透着机灵的小孩,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神留并不正面作答,他回答说:“俺叫什么名字,你问俺爹。”
树仁见状,赶忙说:“哎,哎,他叫留孩,俺想给他起名叫达文,不知妥不妥,请先生定夺。”
孙老师欲待下笔记名时,又问:“姓?”树仁说:“姓雁呢,姓雁。”他把“雁”字故意说重了些。孙老师迟疑着,他不知道此小孩是不是同彼小儿一样,姓的都是大雁的雁。
此时的小神留似乎觉得有必要作些解释,就接着爹的话茬补充说:“俺姓雁。‘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台水接天’,‘夜闻啼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就是那个‘雁’呀。”他回答孙老师,又望一眼树仁,就像在问:“我说的对吧?”
孙老师见能背《千家诗》的小神留如此早慧又如此机灵,很是喜欢。就特别关注起来,有意问神留道:“你说你姓雁,是《百家姓》上的第几姓?”孙老师明知《百家姓》上没有“雁”姓,想故意难为一下小神留,以进而测试他的机灵劲儿,看他如何作答。在场的人也都看着小神留,替他着急。
小神留略作思忖,即回答道:“俺是《百家姓》上第439姓。前有单姓408,复姓30,再往后排就是俺了。”
众人吃惊,孙老师更是眼睛放光,欣然作喜。他又考小神留说:“读过《三字经》么?”
小神留并不正面作答,开口便背诵了起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读过《千字文》么?”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不等神留背毕,孙老师又问:“读过《幼学琼林》么?”
“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
“读过《声律启蒙》么?”
“云对雨,雷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读过《朱子家训》么?”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读过《增广贤文》么?”
“昔时贤文,诲汝谆谆。集韵增广,多见多闻。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知己知彼,将心比心。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
孙云得老师禁不住喜上眉梢。他转而向树仁说:“看来孩子是读过一些诗书了?”
雁树仁忙答:“老爹在世时,给俺正过几句古文古训,我也教留孩认过背过。他和我一样,也只是略知一二,认字,会念,写不来。”
孙老师连说:“好,好,好,达文,就依您的主意,叫达文就蛮好。你如果家里有活落就先回去忙着,让达文留下,帮我招呼下学生好么?”
树仁满心欢喜,满口答应:“好好好,中中中,谢老师栽培。”一颠一颠地去了。
五
大野驴卢全福领着他的四儿“把棍”姗姗来迟,他们成了前来报名上学的最后一拨。
不是卢全福不重视学文化。他见区上的干部都懂文墨,知道将来要做人上人,就得识字。老大“皇军”长得高腿愣怔,有了文化,当个官儿也许有派头,可是一家七口,自己肩膀上扛着六张嘴,镢抓耙搂也难挣出吃喝来。没有个帮手怎么行?得叫老大帮着自己下地干活,养家糊口。老二“飞机”前龟后罗,委委琐琐,长得不出俏,当个官也不见得“畏”人。三儿“解放”虽长得有模有样,但是个犟种,不听老子嚷嚷,上了学也不会给老子省心,也不必上学,叫他俩蹲田、种园,理整瓜菜得了。小丫缺个“心眼”,六岁了,五个指头数来数去还是“仨”。上学也白搭,再说一个女孩家……让她在家帮秋桃烧火洗碗。老四“把棍”长得要脸有脸,要架有架,又争强好胜,和自己一个脾性。让他入了学,识了字,将来定会有出息。
上学得有“大号”,叫“小名”怎么行。“皇军”、“飞机”、“解放”、“把棍”、“小丫”这像什么话?!秋桃点拨野驴如是说。
卢全福认为有理。就起了个大早赶着驴到叶家洼把他的叔丈老骆驼贾大明白贾世通请来了。
自从六老汉上吊自尽,秋桃改嫁,作为六老汉的同乡、同年兼拐弯亲家的贾大明白再也没有到过雁树仁家。此一时,彼一时,当年,自己的侄女秋桃嫁给雁家老二,自己还曾居中作伐,也算是尽了媒妁之言成人之美,到六老汉家,自有居功的成份。虽说秋桃后来弄出丑闻,与自己脸上无光,也还是厚着脸皮登过雁家之门。可秋桃改嫁野驴卢全福,自己却没有尺寸之功。再说解放了,讲究科学,人们再也不迷信那一套老皇历,找他掐“八字”、算命、看日子、治病的少了。自然不便到雁树仁家和卢全福家走动,主动找上门来请教的就更少了。
这次卢全福来请,使他喜出望外,顿感一肚子学问又有了用武之地。他知道全福家有五个子女,早在路上就给他们想好了名字。老大叫卢作金,老二叫卢作银,老三叫卢作铜,老四叫卢作铁,小丫叫卢作锡,并且从数理和阴阳五行上说明了缘由。卢全福对数理阴阳、五行之类不感兴趣,只觉金银铜铁锡都是稀罕之物,宝贝难得,自然没有意见。“皇军”、“飞机”、“解放”也都没有意见,小丫更不知好歹,叫啥都行。偏偏在老四“把棍”身上遇到了难题。
贾大明白光临全福家的时候,“把棍”还在村东苇荒里打蛙子钓鳖。别看“把棍”只有九岁,打小跟着大野驴杀鸡扒狗、打蛙子钓鳖、套兔子、摸鲇鱼、掏鸟蛋……如今已习练成一把好手。他正为收获不菲而在兴头上,“皇军”来找他回家起名,本来就有些不悦。听说他叫作铁,稍一愣怔就大叫大嚷:“我不作铁!我不作铁!我要作金!我要作金!我不是铁,我是金子。”态度斩钉截铁,贾大明白怎么解释也不中,大野驴吼叫着吓唬也不听,他只是捂着耳朵嚷着要叫卢作金。
“把棍”之所以一定要叫卢作金是有来由的,他曾听小伙伴神留说过“到太阳山上背金子”的故事,老大虽然“贪财贪大了,被太阳晒化了”,但说明金子确实是好东西。从那时起,他就立志要得到金子,铁有什么稀罕的,锄镰、锨镢、挠钩子哪样不是铁,再说还生锈。所以他铁了心要叫卢作金。
这使贾大明白犯了难。他沉吟良久,口中念念有词:“这小东西,真倔!你个小老生子还要叫‘金’,这算哪一说?没有这样排法的么。要不让老大叫作今?不妥,不妥,虽不同字但是同音,容易叫混,不妥,不妥……”
他翻着眼望着屋笆,琢磨了半天,没有咒念,又扫视着一排溜站在面前的五个孩子,想看看谁好说话,把名字同“把棍”换换。当他的目光落在黑干潮瘦的小丫身上时,突然来了灵感。口里又咕哝起来:“生女乃弄瓦之喜,生男乃弄璋之喜。璋者,玉也。着,着,叫作玉。”
为了要让“把棍”接受,他还特为讲了“玉”之珍重,不下于金子。谁知,“把棍”还是不答应。
贾大明白有点火:“你这小外甥,好不晓事。金银铜铁,就该大外甥叫作金,敢情你是老大?!”
“把棍”顺势接茬说:“我就要当老大!我就要当大王!”
贾大明白真的火了,没好气地说:“好好好,你是山大王,那你就叫卢作‘Shai’吧。”他接着念出了“Shai”的写法:“左幺右幺,里边夹个言大嫂;左长右长,里边夹个马大娘;心字底,月字旁,扛起枪打老王,老王坐在山尖上。”
“把棍”一听,竟欣然同意,高兴地叫唤:“噢,我有枪了,我当大王了!”
弄得贾大明白哭笑不得,大野驴也感到莫名其妙。
没办法的办法,才决定要老师来定夺。所以等他们来到学校的时候,大部分人家已经报名登记完毕。贾大明白也有意来显示一下自己的学识,他像骆驼似的,一哈一哈地跟在大野驴和“把棍”的后边,到学校来了。
在学校门口,他们碰上了正准备回家的树贤一家。小白鞋眼尖,远远地看见了熟人老骆驼。“俺的老哥哥唻”,她老远就打招呼:“怎么又馋酒啦,来俺老侄子家过过瘾么?”
贾大明白这几年虽然没来卢家岔,但没断了和小白鞋见面,他们两个都替人保媒,一个能说会道,死人能说活了。一个会查日子、推八字,两个人一唱一合,活跃在慈河乡间,做成了不少媒事。都是道上走的人,但并不相互妒忌,倒是配合默契,两人也就越混越熟,见了面当然不眼生。贾大明白看清楚小白鞋正领了个小男孩从小学校里走出来,知道也是来报名上学的,就问:“大妹子,这是你常说起的那个小外甥吧?”
小白鞋嘻嘻地连声说:“就是,就是”,一边把根根推到老骆驼面前,教导说:“快,叫,叫姥爷!”根根不情愿地叫了声“姥爷”,就撇下小白鞋,跑着去追树贤和苗苗。
苗苗刚才看到那边来了卢全福,不愿与他碰面搭话,就拉着树贤的手,拐弯从另一边先回家去了。
贾大明白问:“小外甥起了个什么台号?”
小白鞋喜滋滋地说:“叫达远,雁达远,远走高飞的远。”贾大明白望着远去的根根的背影,拊须片刻,连声叫好:“起得好,起得好。大雁要是远走高飞,一定会飞黄腾达的,前途无量啊!”
小白鞋听了自然欢喜。她不无推崇地对卢全福说:“俺外甥他爹是个老粗,啥也不懂,你有这么个好丈人,还用得着找先生给孩子起名么?”
卢全福一脸的无奈,说:“俺这不是找叔来起名嘛,可这小兔崽子就是不受头,非要和皇军争名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贾大明白接上话茬说:“名字倒起了几个,也蛮好的,可他就是不应口。只好来找师傅看看中不中。”
卢全福刚踏进教室门口。高支书就说:“野驴,你怎么才来,不想叫孩子上学啦?!”
全福说:“这不,小兔崽子混帐嘛,耽误了时间。”
孙老师开始提笔登记,他问高支书:“还有姓叶的?单姓独户吧。”
高支书说:“你看我这张嘴,说哪去了。他不姓野,姓芦,也是芦苇的芦。”
神留在一边听了,忙纠正说:“不是芦苇的芦,是芦字去了头。‘虞万支柯,昝管卢莫’的‘卢’。”
孙老师“噢噢”两声,恍然明白似的问:“是不是前边的几家姓芦的都是没草头的卢?”他问过神留又转向高支书说:“芦卢同音不同字呢。”
高支书说:“芦字有头没有头,我也唬不清。都以为是芦苇的芦。”
孙老师听了贾大明白介绍的情况,盯着把棍想点子。少顷,他对把棍说:“叫作Shai是不成的。这个字连康熙字典上都没有,写起来也费事,将来你升学、做工、结婚登记都是麻烦……”
贾大明白听老师说自己给把棍起的名字连康熙字典里都没有,洋洋自得地望望全福,心里话:“看看,连老师也承认老夫的学问高深吧。”口里却说:“先生高见,先生高见。”
孙老师又和颜悦色的和把棍商量:“你看这样中不中,你不是喜欢当大王又喜欢枪吗,叫作铅怎么样?枪子都是铅做的,厉害得很呢。”
想不到把棍听说,竟高兴的拍手打掌,大声叫着:“我叫卢作铅了!我叫卢作铅了!”
六
尽管卢全福家五个孩子只有一个报名上学,卢家岔小学开办的第一年,报名上学的孩子还是人满为患。因为教室太小,桌凳太少,坐不下多少人。孙老师和高支书商量再三,划算来划算去,决定采取划分年龄段的办法解决问题。
第一批学生只收八至十六岁的孩子。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刚好坐满教室。将原有的冬学改为民校,不仅冬闲学文化,一年四季的晚上都可利用小学校的教室,利用学习好的小学生当小先生,教十六岁以上的青壮年学文化,同样可以扫盲。八岁以下的小孩子来年再上。分级分批,学校实行多级复式,将来办成初小和高小都设班的完全小学。
为了满足学生和家长们求知如渴的强烈愿望,还决定当天下午就开学。一时没有课本。孙老师就先在黑板上给学生正了一课《百家姓》。教了几遍读音之后,就让达文领着同学们一遍一遍朗读: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禇卫,蒋沈韩杨,朱秦有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魏陶姜……”
稚气童声伴和着松涛鸟鸣。
古老的祠堂里又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
来源 | 乐乡游
版权属原作者,如侵权请联系删除
未经允许谢绝二次转载

作者简介
徐敏宗,山东五莲人。1986年加入中国作协山东分会,高(2)级作家。学生时代即涉猎文学创作。参加工作后,不管是务农、教学、从事新闻报道,担任领导职务,还是离岗、退休之后,均坚持文学创作笔耕不辍。现已发表各类文艺作品计260万字,并多有作品在市以上获奖。
其代表作为"精神病院”系列作品长篇小说《本根》。十年前面世时曾广受好评,至今还有许多人记得其中的故事情节。最近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好人巷》是其"精神病院”系列作品的第二部。出版后,除被国家图书馆收藏外,分别在淘宝网、当当网和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发行销售。各地读者均有好评。
其长篇小说《本根》和《好人巷》均获“日照市文艺奖。其新闻作品及部分文艺作品在市以上乃至全国多有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