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曾经发生过两次巫蛊事件,一件是失宠皇后陈阿娇涉嫌诅咒武帝,另一件是卫太子刘据涉嫌诅咒父皇。后一件的后果极为严重,引发了太子刘据与武帝的军事冲突,太子兵败自杀,卫皇后自尽,汉廷中枢政治剧变。
要厘清卫太子巫蛊之祸的整个事件,就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巫蛊”。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其名著《金枝》中曾对原始文化中的巫术做过描述,他认为在很多原始巫术中,通过攻击偶像惩治仇敌属于交感巫术中的模拟巫术,它所依据的巫术原理是“相似律”——两个相似的事物之间存在交感关系。
基于这种相似律的存在,施行巫术的人可以通过对不同的偶像,诸如画像木偶、土偶、草儿纸人、蜡人等,施以不同的惩罚方式,譬如箭肚针刺、劈裂、束练焚烧埋葬等等,这些统称为“偶像祝诅术”,而最终的噩运将要降临到那个被惩罚的人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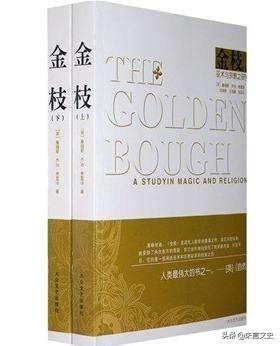
《金枝》
如果按照这个解释模式,秦汉时代的“巫蛊”就很符合这种原始巫术的特征。所谓的“巫”,在中国传统典籍中的解释很多,其主流诠释就是上古先民社会的神职人员,与政治权力复杂纠缠。从文化地理来看,上古三代至于先秦,“巫”文化在楚地最为盛行,据《国语·楚语下》记载观射父对答楚昭王:
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
按照这种解释,“巫”拥有非常人所及的知识与智慧,他们是天地之间的媒介,垄断着对宇宙现象与神秘力量的解释权。汉朝与楚国有着密切关系,文化上受楚文化影响也是可以理解。
那么何又谓之“蛊”呢?“蛊”的原义,是以毒虫让人食用,使人陷于病害。《说文·虫部》云:“蛊,腹中虫。《春秋传》曰:皿虫为蛊,晦淫之所生也。”

巫蛊之祸
“巫”与“蛊”的结合就意味着拥有超自然能力的“巫”使用“蛊”这种手段来加害于人。在汉代流行的“巫蛊”形式,是将桐木削制成仇人的形象,然后在桐木人上插刺铁针,埋人地下,用恶语诅咒,企图使对方催祸。根据邓启耀的《中国巫蛊考察》一书的定义,中国的巫蛊之术指的是:
用纸人、草人、木偶、泥俑、铜像乃至玉人作被施术者的替身,刻写其姓名或生辰八字,或取得被施术者身上的一点毛发、指甲乃至衣物,做法为诅咒后或埋人土中,或以针钉相刺。据说,被施术者就会产生同样的反应,刺偶像的哪个部位,真人的哪个部位就会受到感应性伤害。为了折磨仇家,施术者往往在偶像上遍钉铁钉并合厌以魔鬼偶像,最后才以巨钉钉心,弄死对方。
虽然“巫蛊之术”是神秘主义文化,甚至相较于儒学,可谓一种邪术。但是,“楚俗信巫鬼,重淫祀”的文化传统影响下,汉廷统治者最初并不禁止“巫蛊”。刘邦在吴中地区时曾“悉召故秦祝官”,命令各县设置官府管理的祠社,并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初定天下后,又根据修筑社祠,以长安为中心,根据地域名称设置巫祝,命其按照时令祭祀不同神祇。可以说,楚国的“巫”文化是汉代国家神学建构的一部分,也是在儒学“君权神授”理论建立之前的国家神权理论来源。

刘邦
汉文帝二年三月,朝廷特别颁布以一道涉及到“巫蛊”问题的诏令:
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族,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从文帝的这个诏书看,当时的汉廷对于“巫蛊”之事还是比较宽容的,基本将其视为“细民之愚”。但是,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改变了帝国对于“巫”文化的态度。发生于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的“巫蛊之祸”,涉及多方因素,与汉廷权力斗争、治国政策等复杂纠缠。
《汉书·戾太子传》对“巫蛊之祸”有着比较详尽的记载,其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武帝末,卫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会巫蛊事起,充因此为奸。”这句话将“巫蛊之祸”的原因归结为武帝晚年,皇后卫子夫失去宠爱,奸臣江充上位,在他的构陷之下,才发生武帝父子对抗的“巫蛊之祸”。

汉武帝
事实上,将整件事情归结于江充,实在是过于夸大这个人的作用,也是将复杂的政治斗争简单化了。“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这首流行于武帝时代的民歌,很好地说明了出身平阳公主府“讴者”的卫子夫见幸于武帝之后,卫氏外戚集团兴盛的历史。《汉书·外戚传》记载:
先是卫长君死,乃以青为将军,击匈奴有功,封长平侯。青三子襁褓中,皆为列侯。及皇后姊子霍去病亦以军功为冠军侯,至大司马骠骑将军。青为大司马大将军。卫氏支属侯者五人。青还,尚平阳主。

卫子夫
另外,卫子夫的姐夫公孙贺也因卫氏势力而扶摇直上,据《汉书·公孙贺传》记载:
贺少为骑士,从军数有功。自武帝为太子时,贺为舍人,及武帝即位,迁至太仆。贺夫人君孺,卫皇后姊也,贺由是有宠。元光中为轻车将军,军马邑。后四岁,出云中。后五岁,以车骑将军从大将军青出,有功,封南窌侯。后再以左将军出定襄,无功,坐酎金,失侯。复以浮沮将军出五原二千余里,无功。后八岁,遂代石庆为丞相,封葛绎侯。······贺子敬声,代贺为太仆,父子并居公卿位。
卫氏集团的崛起,离不开武帝的刻意扶持,用意在于制约外朝集团和旧外戚势力。当卫氏集团过分强大的时候,新的势力就会在皇权的支持下勃兴,起到制衡的作用。当卫氏集团形成气候之后,新兴的李氏外戚集团便成为武帝手中的权力平衡工具。

卫青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乐师李延年献出自己的妹子李夫人,换来的是李氏家族的荣耀和富贵。李夫人所生一子昌邑哀王刘髆。与卫氏集团类似,李氏外戚也是一个军功家族。因为李夫人得宠,其兄李广利也成为统率大军出征西域和匈奴的名将。
李氏集团当然不仅只有李夫人和李广利,还有刘屈氂、莽通、商丘成、莽何罗等人。在这些人中,刘屈氂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刘胜之子,行政职务是涿郡太守。征和二年, 公孙贺因罪下狱,他取代公孙贺为丞相,封澎侯。
刘屈氂虽然是皇室身份,但地位权势并不如李广利这样的外戚新贵,所以二人结成了儿女亲家,李广利的女儿嫁给了刘屈氂的儿子。刘屈氂能上位当上丞相,与李广利的推荐不无关系。

李夫人
随着卫青、平阳公主的死去,卫氏集团的地位在征和年间已经岌岌可危。据《汉书·卫青传》记载:“自卫氏兴,大将军(卫)青首封,其后支属五人为侯,凡二十四岁而五侯皆夺国。”卫氏侯国皆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公孙贺之子、太仆公孙敬声挪用北军军费一事,则揭开了卫氏集团覆灭的序幕。据《汉书·公孙贺传》记载:
敬声以皇后姊子,骄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军钱千九百万,发觉,下狱。是时,诏捕阳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贺自请逐捕安世以赎敬声罪。上许之。后果得安世。
公孙贺为了给自己儿子脱罪,主动承担缉捕朱安世的任务。这个朱安世号称阳陵大侠,是与郭解、朱家同一类型的人物。朱安世被捕之后,反而大笑:“丞相祸及宗矣。南山之行不足受我辞,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朱安世在狱中上书,“告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诅上,且上甘泉当驰道埋偶人,祝诅有恶言。”

公孙贺
朱安世,这样一个江湖豪侠,竟然开启了大汉朝一场惨烈的政治斗争大幕,“巫蛊之祸”由是而起。如果揆诸文帝二年所颁布的《除诽谤妖言诏》,武帝时代的这种“祝诅”之事应当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武帝不同于乃祖,从对陈皇后的巫蛊事件处理就可以看出,汉武帝有心摆脱楚地巫风对政治的影响,何况这种“祝诅”指向了皇帝本人。
朱安世的告发,促使了汉武帝对宫中“巫蛊”的调查,另外一位重要人物——江充介入进来。很多史料和大多数的研究者都认为江充是将事态激化,并引向卫太子的关键人物。根据《汉书·江充传》记载:“充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因是为奸,奏言上疾祟在巫蛊。”
江充其人,本名江齐,赵国邯郸人,其妹曾嫁与赵国太子刘丹。但是,赵王家族乱伦胡搞,太子丹与同母姐姐私通,此事为江充告发。几经周折,江充进入长安权力场,成为皇帝的直指绣衣使者,有点像盖世太保的意思。

江充
出于对于权力控制的紧张,汉武帝除了启用寒微外戚制约勋旧贵族之外,还任用大量酷吏监控新旧贵胄,江充就是其中之一。江充与卫太子刘据之间有矛盾,但是从问题本质上讲,江充在矛盾中并没有多少越轨的地方,他所履行的都是武帝赋予的执法职能。《汉书·江充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后充从上甘泉 ,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充以属吏。太子闻之,使人谢充曰:“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闻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宽之!”充不听,遂白奏。上曰:“人臣当如是矣。”大见信用,威震京师。
后世一些历史研究者将江充及其家人早年与赵王家族之间的旧怨与“巫蛊之祸”联系在一起,江充被描绘成一名向汉室复仇的复仇者,“巫蛊之祸”被诠释为构陷卫太子和离间武帝父子关系的政治陷害。

卫太子
事实上,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江充都没有构陷太子的胆量和能力,甚至也没有动机。正因为朱安世的告发,武帝开始了一次在长安禁绝巫蛊的整治行动,江充所扮演的仅仅是执行武帝旨意的角色。武帝虽然命江充主持查办“巫蛊”,但是也并未将权力全部交给江充一人,“ 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
这里的三个人中,韩说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汉初异姓王韩王信的曾孙,汉武帝早年宠童韩嫣的弟弟。顺便说一句,武帝的性取向是非常复杂的,韩嫣可能是他早年第一个男朋友,韩说本人与其兄的作用也可能一样。
上述三人的介入,说明武帝并不完全信任江充,他们起到了监视和制约江充的作用。在这样的安排之下,江充是不可能有机会提前进入太子宫,将桐木人埋下的。于是,“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的事情应当是实锤!

晚年汉武帝
太子在宫中埋下桐木人,自然是诅咒武帝,原因不难理解,皇位而已。已然东窗事发,太子遂问计于少傅石德。石德担心株连自己,于是献计铤而走险:
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
石德的意思就是干脆用矫诏拿下江充,然后弄死。至于皇帝,尚在甘泉宫,消息不通,太子不如先下手为强,免得重蹈当年秦朝扶苏覆辙。所谓的“奸臣如此”,石德的所指应该是李氏集团,因为将卫太子比作扶苏,那么言下之意,昌邑王就是胡亥。事实上,查办“巫蛊”是武帝自己的旨意,石德未必不知,所谓“奸臣”,可能只是消除太子发动政变的心理恐惧。

巫蛊之祸
于是乎,太子刘据发动政变,“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曰江充反。乃斩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太子起兵,但很快事败,“长安中扰乱,言太子反,以故众不附。太子兵败,亡,不得。”从起兵到出逃,不过十天时间。在此期间,汉武帝赐丞相玺书曰:“捕斩反者,自有赏罚。······紧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
不仅如此,武帝甚至走出甘泉宫,亲自指挥与太子的军事对抗,“幸城西建章宫 ,诏发三辅近县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将。”
武帝父子兵戎相见,最终太子刘据兵败自杀。在太子兵败逃往的同一天,武帝即派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敢奉策收回皇后卫子夫的玺绶,卫皇后因此自杀。卫皇后是无辜的吗?如果没有她的玺绶,太子起兵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太子行“巫蛊”和起兵的背后是卫氏外戚集团对武帝皇权的挑战,其核心人物就是太子和卫皇后。

卫子夫
卫氏外戚遭此重创,几乎覆灭,而李氏集团则成为这场政治变乱的客观受益者。李氏集团的莽通、商丘成都因在平定太子兵变过程中的功劳而被封侯。第二年,李广利再次获得兵权,出征匈奴,李氏集团犹如当年的卫氏集团,外有李广利手握重兵,内有丞相刘屈氂执掌朝政,权利煊赫一时。
李氏集团崛起,对未来帝位也有野心,就在李广利出征匈奴之前,丞相刘屈氂送别至渭桥。李广利直接就说:“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昌邑王刘髆就是李广利的妹妹李夫人之子,李广利与刘屈氂又是儿女亲家,所以“屈氂许诺”,“故共欲立焉”。
但是,李氏集团的好景不长,其覆灭的路数竟然与卫氏惊人相似。据《汉书·刘屈氂传》记载:
是时,治巫蛊狱急,内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数有谴,使巫祠社,祝诅主上,有恶言,及与贰师共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有司奏请案验,罪至大逆不道。有诏载屈氂厨车以徇,要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贰师将军妻子亦收。贰师闻之,降匈奴,宗族遂灭。

老年汉武帝
“巫蛊之祸”灭掉了两个外戚集团——卫氏和李氏,两名皇子在皇位争夺战中出局,太子刘据兵败自杀,昌邑王刘髆在丞相刘屈氂被杀之后的第二年就死了,很明显,弄死的他的是武帝。可以说,汉武帝自己搞死了两个儿子——太子刘据和昌邑王刘髆。为什么呢?因为他所属意的接班人是幼子刘弗陵,也就是日后的汉昭帝。《汉书·外戚列传》记载:
拳夫人进为婕妤,居钩弋宫,大有宠。元始三年,生昭帝,号钩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钩弋夫人和尧母门的故事,不过这里有个很大的疑问,怀胎十四个月,这是绝无可能的怪事,上古的帝尧十四月而生只是神话传说,钩弋夫人怀孕十四个月,只可能说明一个问题:汉昭帝刘弗陵并非武帝亲生子。

钩弋夫人
武帝可能知道吗?当然可能,但是为了皇权的稳定,刘弗陵究竟是谁的儿子已经不重要了。关于昭帝身世,朱言后文还会详细论述。相较于身后有着强大外戚势力的刘据和刘髆,刘弗陵登上帝位,对于帝国权力的稳定更为安全一些。所以,整个“巫蛊之祸”,只是汉武帝借题发挥和引蛇出洞的权谋而已,目的是打掉卫氏和李氏两个权力集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