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根皮筋勒住老范的左脚,梅女提一下,老范勉强挪半步。梅女个子矮,必须把皮筋举过头顶才能挪动老范的脚,力量稍微不到位,老范拄着拐杖的身体就侧斜着。老范的身体一斜,拐杖也跟着斜,梅女扶不住,两个人就一起摔倒在地上。梅女跪着,蹲着,甚至想借助椅子,使尽了吃奶的力气,也无法将老范扶起来。老范的左手与左脚都是不听使唤的,仿佛不属于他的身体,无奈之下,他只有啊呀呼嗯地嚎,声音含混,短促,嘴唇哆嗦着,喉咙里像堵了一口痰,究竟说了什么,梅女也不清楚。梅女无助地坐在地上,看着木然的老范,欲哭无泪。
这样的日子,梅女不晓得熬到哪天是个头。
老范的名字是范真,与那个画国画的范曾同音不同名。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他是在娘肚子里从新安江移民到婺源许村的。那年,与他父母一起移民的,差不多有三十万人。在许村,父母还生了个小儿子,不幸的是,后来得了脑膜炎,死了。如果让老范用两个成语概括父母的后半生,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勤俭持家与积劳成疾。老范搬到县城,父母死活也不肯离开许村。在父母生前,老范还特意陪父母去千岛湖走了一趟。只是,他们的老家在水底,根本看不到了。
老范的名字很少有人叫,人们都欢喜叫他绰号——饭桶。比老范年纪大的一见面,就饭桶饭桶地叫,他也爱哎地应。据说,这是老范早年下乡收古董时,为一只梅瓶与人赌吃,吃了一斤八两的米饭才赢得的名头。老话说,一不赌力,二不赌吃,老范倔强,觉得赢了就妥了。在婺源做古董行当,做得好的开了民俗博物馆,一般的只有开个古董店糊日子,混得差的,只有拉皮条,赚个手续费。老范不算做得好,只有一间古董店,小日子倒过得安稳。做古董生意讲捡漏,所谓的要嘛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这样的生意有没有,肯定有,只是少之又少了。
梅女刚到老范家做保姆,对饭桶这绰号觉得别扭。好在,她叫老范他也应得欢。说起来,老范是婺源生婺源长,却说不来婺源话,按当地民间的说法,就是绕佬一个。老范没有得脑血栓前,梅女已经在他家做了四年的保姆。平日里,老范对人不薄,就是脾气有些暴躁。偏偏,梅女是个慢性子,属于文火慢炖的类型,你急她不急,倒也好相处。四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问题是,老范离异,梅女丧偶,一个没有续弦,一个没有再嫁,两个人一个门里进出,日子长了,街坊邻里就有了闲言闲语。有时,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首先感到讶异的是老范的两个儿子。
一天晚饭后,老范对儿子说,别人的嘴长在别人身上,我堵不住,也不想堵。今天没外人,有件重要的事必须说一说,我如果能够娶到梅女,是前世修来的福气。老范的话一出口,他的大儿子进生愣住了,半天没缓过神来,他疑惑地望了望父亲,摸出一支烟去门口抽烟了,小儿子连生根本没当一回事,眼睛没有离开屏幕,盯着朋友圈中抢红包。梅女觉得,这一刻空气都凝固了,她警惕地扫了老范一眼,又看了看玩手机的连生,说老范你是不是喝多了,周末一起吃餐饭,这样的玩笑可不好开。
老范茶杯盖都掀开了,茶也顾不上喝,问,我像在开玩笑吗?
梅女拿抹布擦着手,红着脸说,我是来你家当保姆的,你也不想想,这说的是什么话。何况,我比你还小一岁呢。
梅女以为,老范的话随说随丢,就过去了。谁知,老范是个死心眼,没过几天,又当着儿子的面把话题提了起来,话语里连商量的语气都没有。老范盯着梅女说,这些年,人家介绍过好几个,不是没相中,就是嫌拖老带小屁事多。我呢,算是枯木逢春吧,好不容易有个想法,你是什么意思,好歹给我个态度。你是不是经历过一次丧偶之痛,就连找配偶的勇气都没有了?
没,没有!我这样的人,还能有什么意思呢。梅女扪心自问,这个问题自己连想都没有想过。她无奈地摇摇头,犹豫地说,本来……本来想等女儿高中毕业就回乡下,看来得提前回去了。这样吧,这个学期一结束,我就辞工。
梅女心里清楚,在离开范家之前,必须找到活干,不然,经济来源就断了,女儿上学的费用也就无从着落。
那天之后,梅女感到老范的大儿子进生怪怪的,话语更少了。尤其,老范魂不守舍的样子,经常欲言又止,文公北路的古董店也关张了,瓶瓶罐罐的,还有许多杂件,都搬到了家里,经常一个人神神秘秘地躲在房间里倒腾古董。既然,梅女都把话对老范说到这个份上了,自己也就轻松了。梅女每天还是踩着原来的节奏,买菜、做饭、洗衣、打扫卫生。而老范呢,生怕梅女跑了似的,进进出出跟随左右。梅女不免烦了,说,老范呀,你让左邻右舍怎么看,这又是何苦呢?
嘿嘿!老范一笑,依然我行我素。
老范在客厅郑重其事地对梅女说,不可否认,那些年下乡是收到过好东西,字画、砚台、瓷器、玉器,可都从手上溜走了,就连一方有朱熹题款的抄手砚都没留住。为什么?图利!有时候,错过了,就失去了。人呢,更是如此。说着,变戏法似的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袖珍锦盒,用手掌抚了抚盒面,递给了梅女。
你这葫芦里卖什么药?梅女尴尬地问。
你,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老范盯着梅女说。
看到老范欲言又止的样子,梅女已经猜出了锦盒中的内容。梅女的冤家也送过她戒指,只是为了还债,她不得不卖了。这个时候,她忐忑而犯难了,心里泛起莫名其妙的情愫,又说不清道不明的。
实话实说吧,里面是一枚戒指,我曾经找马未都先生掌过眼,老货,黑翡的,水头不错,希望你能够收下。老范说着,似乎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
梅女听不懂长過眼是什么意思,但马未都在电视里见过。那个白头发老头,在电视里讲起古董来一套套的,应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听老范这么一说,梅女心中更没底了。
这,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
梅女慌乱,眼也没敢抬,就想把锦盒塞回到老范手上。没想到的是,老范顺势就把她抱住了。梅女的力气哪里是老范的对手,她被老范搂住不能动弹。
你……你疯了?这……这是欺负人!梅女慌慌张张地说。
老范不管不顾,躬身贴着梅女的耳朵,轻轻地说了句——我要你。
老范的话虽然轻,却足以击穿梅女的耳骨。随即,老范嘴唇贴了上来,舌头探到了梅女的舌尖。梅女的身体一颤,瞬间软了。老范的手像长了眼睛似的,在梅女的乳峰穿梭游走,把她的心湖都荡开了。仿佛是一场迟到而又久违的邂逅,老范与梅女互相看着,自己都感到惊愕。客厅双人布艺沙发上的丝巾,像麻花拧成了一团,靠背也掉在了地上。老范顾不得整理,索性抱起梅女进了卧室。
二
梅女信命。能够与老范结缘在一起,她更加坚信无疑了。
丈夫出车祸去世那年,梅女只有三十出头,女儿刚刚小学毕业。丈夫留给梅女的,除了官司,还有一屁股的债务。在丈夫生前,梅女对他的称呼是以爱代替的,丈夫去世后,梅女就称他是冤家了。无助的时候,梅女常常含着眼泪自言自语,说冤家呀冤家,你什么都好,就是命短了。似乎,说几句,叹息一下,梅女的心里就轻松一些。好多次,梅女在做同样的梦,不是掉入一个无底的深渊,就是被人按在火边烤,烤得身体都要干了。最后,都是在灼痛中惊醒。
好些日子,梅女不敢相信丈夫离去的事实。可在婆婆一次次的咒骂声中,她确认丈夫是真的死了。
梅女认识老范,算得上是机缘。那天,老范在梅女所在的樟村收古董,梅女手头正紧,想把娘家陪嫁的一对银镯卖了。虽然,银镯是祖传的,工艺也不错,毕竟值不了几个钱。再说,婺源民间银饰品多,老范很少收银器。老范拿着镯子在手上掂了掂,皱着眉头说,祖传的饰品,还是拿回去留个念想吧。梅女接过镯子,用手绢包了起来,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按理说,梅女的家庭困难与老范是不相干的事,可听到梅女家的遭遇后,他重新找到梅女把银镯收了下来。面对梅女的疑惑,老范亮了亮镯子说,收古董的也是人,看走眼是常有的事。
在樟村,老范不止一次听到了梅女的遭遇与困顿,还有一根筋的婆婆对她的咒骂。村庄里有些家庭的事,是很难理解的。比如,梅女丈夫的车祸,婆婆怎么能归结到她的头上呢。老范是经常走村串户收古董的,他在村庄也算是走得多了,但像梅女的婆婆这样不讲理的,他还是头一次见到,其实,梅女的婆婆也是早年就守寡了,她从媳妇熬成婆,把子女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也确实不容易。俗话说,舌头无骨,随人转。话,传多了,转多了,梅女就成了丧门星。
老范再次遇见梅女,是在樟村村口的马路上。当时,老范在樟村收了一只蒜头瓶,准备开车返回县城,而梅女正在路边候班车,说是在家待下去,迟早要憋死,逃出去打工了,图个两耳清净。
路边田野的油菜花正开,闻到的都是油菜花的花香。老范看到梅女捋着头发单薄的样子,当时自己也不知是基于收到蒜头瓶如获至宝的心情,还是出于对她的怜悯,说家里正缺一个保姆,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走。说着,老范的目光越过了梅女的肩膀。梅女犹疑了一会儿,喃喃地吐了两个字——好吧,就把帆布包背在了身上。
老范的双手摸着方向盘,专心开车,眼睛斜都不斜一下。车窗外,行道树、田野、山峦、村庄都在后退,梅女却不知道自己的前方在哪里。一路上,老范与梅女都像哑巴似的,没说一句话。梅女晕晕乎乎地坐着老范的车到了县城,还没下车,就吐得一塌糊涂。老范递纸巾给梅女,她竟然不知道接。老范摇摇头,苦笑了一下,说,我哪里是请保姆,还是当保姆得了。
县城的街上,车来车往。面对车流灯影,梅女感到眩晕,她恹恹地跟着老范,走到他家门口了,还躬在地上嗷了几口,感到肚子里吐空了,连苦水都吐了出来,脑中更是一片空白。
那一夜,梅女昏昏欲睡。早上醒来,梅女发现老范家空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大概是八点钟左右,老范提着塑料袋回家了,里面是豆浆、菜包,还有油条。梅女见到老范,拘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没等梅女开口,老范挥着手说,肚子不饿是吧,还不去拿筷子?说完,他径直走出了大门。
吃早餐的时候,梅女才发现老范家的房子是别墅,两层半,有个小院子。梅女不是那种不识数的人,她嘴上不说,却把对老范的歉疚表达在了做家务上,一天三餐,炒菜、蒸菜、糊菜,变着花样做。梅女哪知,老范是无肉不欢的,三天没肉见面,脸就拉了下来,说这样吃下去,脸都会吃成菜色的。老范说这话的时候,不是因为梅女生分,也不是失态,而是他的生活习惯使然。梅女没说话,她摇摇头,又点了点头,分明自己听懂了老范的话。
好在,梅女做乡下土菜的手艺还行,每餐开始荤素搭配,什么粉蒸肉、红烧肉、虫菜肉、酱爆肉,什么小炒肉、水煮肉、回锅肉,什么卤肉、扣肉、烤肉、腊肉,变着法子轮流做,再炒两盘蔬菜,外加一碟豆腐乳抑或酸辣椒,让老范吃得大呼过瘾。梅女心细,买菜讲究,食材专挑菜农手上买,买肉也要买烧猪食的猪肉,只要吃饲料的猪肉,她从肉色上就能分辨出来。梅女买菜挑剔的程度,几乎让菜市场的菜农与屠夫都领教过。
许是食材新鲜,味道也合胃口,老范的两个儿子饭量也增了。只是,他们吃完,碗筷一搁,就不见了人影。老范觉得,家里有梅女操持,就够了。
三
一个没有女人的家庭,无疑是有缺憾的。
香烟、打火机、剃须刀、拖鞋,甚至内衣,很少有序的时候,梅女整理好,等老范和他儿子一回家,又是乱糟糟的。问题是,梅女一一整理归位,衣服叠好后,老范和他儿子还觉得不顺手,急起来找不到,就埋怨梅女。开始几天,梅女觉得无所适从,慢慢也就适应了。许多时候,老范和他儿子在家,抑或有客人来了,等他们落座,梅女泡好茶,端上,就轉身去了厨房或是房间里,很少露面。尤其,梅女在一个月中例假的那几天,像做贼似的,卫生巾都掖着藏着。
梅女是那种想事的人,想到事,就放在肚里。日子一天天围着客厅、厨房、菜市场打转,她最放心不下的是在村里读书的女儿。女儿一天天长大,好在个子继承了自己的冤家,不然,像自己的个子,矮墩墩的,将来走出去就没个样子了。自己一辈子已经是熬成的酱了,可女儿不是。
一想到自己的冤家,梅女就忍不住流泪。隔一段时间,梅女也想尝试着忘掉过去,但八年的夫妻生活,哪能想忘就忘掉呢。奇怪的是,有的晚上,梅女迷迷糊糊的好睡得很,过了几天,晚上又睡不着觉了。有时,睡梦中,仿佛有人压在身上,压得喘不过气来,想喊也喊不出声音。惊醒过来,只有一身冷汗。梅女害怕黑暗,她把电灯开着,又无法入眠。有时,梅女是躺在床铺上眼睁睁地盼着天亮,隔壁房间老范的鼾声,还有客厅里电子钟的走动声,都听得真切。尤其是,夜猫的叫声,一阵阵,凄凄的,嗡得慌。
梅女的丈夫已经走了好几年了,有好心人也为她牵过线,都被她谢绝了。有时,梅女看到同龄人出双入对的,心里也有过想法,甚至,萌动过女人的欲望,毕竟,自己才步入中年的门槛。但,一想到女儿,心里一切都消退了。只有女儿,才是自己唯一的希望。梅女心里清楚,女儿能够转入婺源中学读书,是老范帮了忙的。女儿的分数刚好上线,婺源中学是省级重点中学,招生名额却有限,竞争激烈,而自己在县城两眼一抹黑,抬头不认识半个人,是老范忙前忙后跑了好几天,才把事情办妥。
请客的事,老范半句都没提。具体费用花了多少,梅女也不清楚。梅女了解老范的脾气,他不想说的事,你问了也等于零。
中秋的前一天,梅女正在院子里晒衣服,婆婆不知从哪冒了出来,不声不响的,吓了她一跳。梅女想,樟村到县城有五六十里地,县城又有这么大的地盘,她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妪不知是怎么摸上门的。
嗬,贩钱家的有出息了,家里的田地在抛荒,居然躲在城里过上小日子了。瞒得过么?躲在被窝窿里吃鸡子的事都有人晓得,何况送上门的货呢。婆婆瘪着嘴说,一脸不依不饶的样子。
梅女在围裙上搓着手,不客气地放下脸说,出门讨生活,总比在家里让人憋死强。
真不要脸!想当初,我那不争气的儿子怎么看上这样的货色。一脸克夫相,克了我儿子还嫌不够?
这不是你家,别像疯狗一样乱吠。梅女火了。
呸!怎么样,你还敢打我不成?
老范在屋里听到吵闹声,端着茶杯就走了出来,见是梅女的婆婆,笑着说,大老远的跑来,有事屋里说。
跟你有什么好说的,一对狗男女。梅女的婆婆跨上前一步,她不仅腿脚灵便,骂人也顺溜。
你说什么?老范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对狗男女!难道我说错了吗?梅女的婆婆重复了一遍。
你一把年纪,满脑头发都花白了,积点口德好不好?老范如鲠在喉,脸都被她气青了。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有本事你嚷呀,我还怕你嚷。哪有什么好佬,有本事来打我一下就算好佬了。你贩古董都贩得,贩人也应该没问题。
老范气不打一处来,吼道,滚出去!
没人稀罕哩,看一对狗男女的眼热。不是找孙女,凭你?哼,请都请不来。如果是我,脸皮都不知往哪搁。不过,畜生当街都可以……梅女的婆婆咬牙切齿,把铁皮门一拍,骂骂咧咧地走了。
看老范半天没吭声,梅女心里不免愧疚,好像无理取闹的不是自己的婆婆,而是自己。
梅女得知老范离异的原因,是一年后了。那天中午,老范喝了酒,话语特别多,不管你听不听,他像倒豆子似的,吧嗒吧嗒地一股脑倒出。
嗯,怎么说呢,我一辈子就喜欢古董,喜欢喜欢就把喜欢的老婆赶走了。这,也不能全怪我,能怪我吗?是她有洁癖,说什么出土的东西阴气太重,受不了。依我看,什么都没有。不可否认,早年和我一起贩古董的盗过墓,我也一起去过,却没动过手。这一点,我可以对天发誓,让人戳脊梁骨的事不会做。老范嘘了一口气,竖起食指摆了摆,继续说,没错,我是能够抱着古董睡觉,她看不惯,想走,完全是找的借口嘛。收古董是我要糊的生活,我怎么妥协?妥协得了吗?
作为男人,老范能够不隐瞒,不避讳,对自己说这些,梅女真的很惊讶。然而,她隐约感觉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在向自己压来,内心感到惶恐,她茫然地听着,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仿佛老范的话不是对自己说的。
更糟糕的是,她整天疑神疑鬼,逼我把古董店里的女店员辞了。文公北路有六家古董店,哪一家店没有女店员?从这一点上,我不得不佩服女人的想象力。也不想想,人家都可以做我女儿了,这可能吗?
如果换作往常,不是老范喝了酒,梅女说不定会补上一句——很难说。但看到老范话唠的样子,她忍住了。
老范接着说,还有更可气的,她凭什么把我辛辛苦苦弄来的瓷片当垃圾丢了,太没有眼力了,也不看看是什么朝代的。我不心痛两个钱,是心痛瓷片。老范怔了怔,似乎还没说过瘾,有一句俗话怎么说来着,最毒妇人心呐,她要了我一对桃瓶跟镇巴佬走,恶绝得很,老公儿子都可以撇下。她那嘴巴,生来就是数落别人的,我不像她,好聚好散,再说她就没意思了。我要记恨她,记恨得完吗?
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这人就是块木头。是木头,知道不?一点意思都没有,没劲。没劲,知道不?老范剜了梅女一眼,转身盯着博古架上的梅瓶,拿在手上,又放了回去,他摇摇头,欲言又止。
梅女大气都不出一声,冷冷地看了老范一眼,转身出门了。
四
谁也不会想到,正当老范筹备与梅女婚事的时候,他一摔不省人事了。
梅女急了,就去掐老范的人中,也不见效果,心里咯噔咯噔的,急得眼泪都涌了出来。120电话,是进生拨的。很快,救护车就到了玉宇小区。随着呜呜的警报声,小区跳广场舞的,推婴儿车的,散步的,还有保安都围了过来,救护车前挤满了人。
出了什么事?
人不要紧吧?
唉,怎么会这样呢?
手忙脚乱的梅女,嗓子干涩,眼圈红红的,连双脚都是虚软的,面对大家的问询,只是一个劲地摇头。她不知道怎么回答,脑袋是蒙的。
梅女没见连生哭过,那天在医院急救室门口,连生流泪了。
按年纪,进生完全可以成家立业了,连生也步入了青年,一遇到事,二人都没了主见。问题来了,老范不仅没有办理居民大病医疗保险,而且钱都存在银行卡上,他的密码连儿子都不知道。无奈之下,用老范的生日、电话号码试过几张卡的密码,都不是。虽然,进生有工资,却是月光族。进生、连生,还有梅女,几个人一起凑拢的钱,包括微信红包都转了出来,在医院不到一个星期就花光了。没钱怎么看病?
看到两兄弟愁眉苦脸的样子,梅女能撒手不管吗?她在医院走廊上转来转去,急得直跺脚。跺脚也没用,如果跺脚能够跺出钱来,就好了。情急之下,梅女找到每年一起去齐云山上香的桂香姨。听桂香姨不止一次说过,早年她和老范是邻居,交往不错,向她开口借钱救急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看到桂香姨愣住半天没有反应,一脸为难的样子,梅女说,我也没有什么值钱的,要不,就把黑翡戒指抵押在你这里?
你傻呀,什么抵押不抵押的,多难听。桂香瞄了一眼梅女手上的黑翡戒指,迟疑了一下,不好意思地说,不是我不肯借你,实在是手头拿不出来,家里的积蓄全让信贷公司的给套进去了。我也是头脑发热,利息没赚着,还欠着亲戚的一屁股债。
桂香上前搂着梅女,慢吞吞地继续说,唉,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我也是火烧乌龟肚子痛,有讲不出的苦。你不想想,我原来没事,每天一场麻将,雷打不动,现在呢,连麻将都戒了。这样吧,改天我去看望老范。
这一说,弄得梅女进退不是,更加不安,她含着泪告别了桂香姨。梅女拖着沉重的双腿赶到人民医院,看见进生正叼着香烟坐在长条椅上,一口一口地吐着烟圈。
也不知道家里的古董哪一样值钱,不然,拿出去卖了就有钱了。分明,进生的话是对连生说的。
哪知道,即使知道,拿去卖给谁呢?你忘了,我们小时候偷老爸几枚袁大头换钱,都被他打得半死,如果拿他古董去卖,那不等于要他的命呀。连生埋着头,小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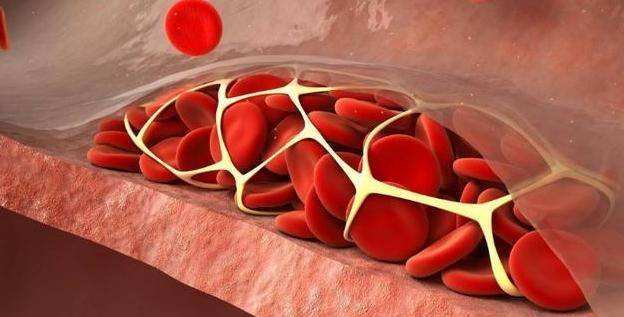
这倒也是个问题。可这哪跟哪,这是拿去卖钱救他的命。进生应了一句,继续吐着烟圈。
人嘛,钱嘛,到底是人重要还是钱重要?没有了人,钱有个卵用。梅女脑袋里一直绕着这样的字眼打转。无奈之中,她急咻咻地说,要不,给你妈妈打个电话,让她救个急?
进生扫了梅女一眼,又看了看连生,没有立即接话。他不屑地说,要打让他打,我是抱养的,跟她早就闹僵了,打了电话她也不会接。
进生竟然是抱养的?他怎么会是抱养的呢?梅女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话到喉咙口了,还吞了回去。
连生犹豫了一会儿,说,我给老妈发过微信,告诉她老爸病了,没说这么严重。说完,独自拿着手机去走廊拐角打电话了。
老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老范都病成这样了,她不会不管的。再说,没有过不去的坎。梅女像在对进生说,又像在自言自语。
老范的前妻秋玉从景德镇赶到婺源县人民医院,老范还没脱险。
妈!连生悄声叫了一句。
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会弄成这样呢?秋玉声音压得很低,还是很尖。
嗯,我们也料不到,老爸会病成这样。连生把目光从母亲身上移到了连接父亲的氧气瓶。
病房里很静,仿佛能够听到各自呼吸的声音。梅女是第一次见到秋玉,听说她与老范离婚后,没多久就嫁给了景德镇一个画瓷的师傅。梅女小心翼翼地说,那天,老范在家里摔了一跤,就摔成这样了。
你是谁?有你什么事?秋玉盯着梅女,样子咄咄逼人,眼睛里除了质疑、警惕,还有更多的内容。
梅女想,好在那天进生连生都在家,不然,自己有一万张嘴也说不清。有一次打扫老范的房间,梅女在相框里见过老范和秋玉的结婚照,梅女还想象过秋玉的样子,见到人,与照片上还是有距离的,下巴尖,颧骨高。看到秋玉的样子像母老虎似的,梅女惹不起躲得起。这个时候,梅女有委屈,也只能憋在心里。她低下头,弱弱地吐了两个字——保姆。
真的是保姆?秋玉冷冷地问。
是。梅女挤出是字时,心里像被针刺了一下,她害怕秋玉缠着再问下去。
好在,秋玉在一直问连生古董店的事,主要问店里的古董都搬哪去了,怎么一点鼻孔风都不透一下,她根本忽略了梅女的存在。她们母子说她们的,梅女默默地坐在墙角边,也不作声。
秋玉来去匆匆,前前后后加在一起,她在医院待的时间不到半天。梅女发现,秋玉转来转去,连在老范病床前一次近距离的俯身都没有。进生与秋玉在病房碰面了,他只是点了下头,并没有叫她。梅女想回避一下,省得夹在中间尴尬,偏偏,秋玉站的位置刚好挡住了她的去路。秋玉悄悄扯了连生一把,两个一前一后去了病房門口,她告诉连生说,如果没改,你老爸建行卡号的密码应是你的生日。
其实,秋玉的话,梅女与进生都隐约听到了。连生返回病房,直愣愣地站着,一句话也没说,进生就皱着眉头出去了。

老范住在医院重症病房,脑电图、脑血管照影、脑超声波、CT扫描,一一进行,抢救了十天,命是保住了,后遗症是半身不遂,话语都讲不清楚,只知道嗷嗷地叫,喉咙里像被痰堵住似的。庆幸的是,老范捡到了一条命,而同一个病房的老余,比老范还后入院,脑溢血,就直接没有从手术台上下来。老范从住院那天开始,先是进生连生轮流和梅女一起看护,出院了说是要分开看护的,最后还是落到了梅女一个人身上。
起先,梅女为老范准备了电动的轮椅,可老范坐上去往一边倒,弄不好轮椅就侧翻了。梅女只好请人做了一个学步车似的木桶,即可让老范不至于摔跤,也可以时不时地推着老范转转。连生看到梅女一天到晚累得够呛,提出夜里要看护父亲,都让梅女挡了回去。梅女努力睁着眼皮淡淡地说,有我呢,你去睡吧。
五
看到老范双眼空茫,流着口涎的样子,梅女不由想到他以前每天头发梳得一边倒,还有下巴刮得光洁的清爽劲。树怕藤来绕,人怕病来磨。人呀,一病倒,就没个人样了。一个好端端的人,怎么会得这样的怪病呢?梅女对脑梗脑血栓这样的病症也不了解,听医生说说,也是知晓了一个大概。但,她记住了医生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患者一旦脱离了危险期,不是没有康复的可能。
尽管,梅女每天主要是服侍老范,四个人的饭,以及卫生还是要包揽的。累了,梅女也想发脾气,可她又能对谁发呢?长此以往,梅女觉得自己非被拖垮不可。人心都是肉长的,即使有一万个理由,梅女见老范病成这样,她能够丢下他不管吗?
没有去民政部门办理登记,梅女还是一个保姆,要照顾这样的病人,有太多的不便。夜里,梅女一个人无数次哭过,她哽咽着,没敢哭出声来。
可是,有的事,梅女自己不好说,别人呢,又不会帮忙说。自己把这里当家是一回事,别人眼里怎么看又是另外一回事。
也有好心人不止一次劝梅女,你是好戏不断,年纪轻轻的,何苦!
或许,这就是我的命。梅女淡淡地答。
一天又一天,梅女一直守在老范身邊。今后,究竟怎么过日子,她心里也没谱。更让梅女心里没底的是,丈夫去世后的那几个月,月经周期有过紊乱,可最近就完全消失了。莫非……哪有那么多莫非。梅女连那个词想都不敢想。
梅女思前想后,觉得自己卑微,却从老范心目中获得了温暖与尊严。梅女一不做二不休,她决定豁出去了,要和老范登记结婚。梅女在老范病得不轻的时候提出结婚,首先感到惊讶的,应是进生和连生吧。尽管,梅女轻描淡写,话语说得很慢,有着少有的平静,但进生和连生始终没有作声,脸上也未流露出任何表情。
梅女头天晚上与进生说得好了,让他第二天陪同去民政局,可左等右等,十点多钟还没看见他的身影。梅女电话打过去,也联系不上,语音提示说,你拨打的号码不在服务区。发短信微信,也像石沉大海。梅女只好硬着头皮给女儿打电话,想她来帮把手,谁知女儿沉默了一分多钟,支支吾吾地说,前些天,前些天奶奶来学校了,凶巴巴的,可骂得厉害。再说,学校也不让请假。
孩子,你不能懵懂呀!俗话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如果没有老范,你还不知道在哪上学呢。梅女嘀咕着,就把电话挂了。
无奈,梅女推着老范去社区与派出所,把证明一一开好,已经是下午了。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告诉梅女,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是头一次遇到,范真还是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能不能够办理,要请示上级再说。
梅女忧心忡忡,她把老范送给自己的黑翡戒指拿给工作人员看,说老范求婚的时候是清醒的呀,怎么就不能登记呢。你们不是说要婚姻自由吗,怎么轮到我就不自由了,没有了婚姻的权利呢?
工作人员摇摇头,说,戒指是黑翡的,我们也不识货,即便是宝贝,也不能作数。问题来了,这一登记,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就会牵涉到家庭财产等等问题。行使婚姻自由权,必须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进行的,《婚姻法》里结婚的条件与程序都有规定。放心吧,你留个电话,有了消息,我们就会立即通知你。
梅女本来心里就不痛快,一听,火了,嚷嚷道,他现在是一个废人,一个需要把屎把尿的废人,急需要人照顾,你让我怎么放心,放心个屁。我这是披蓑衣救火——引火烧身。你们也不想想,我能拿终身大事开玩笑吗?
任凭梅女怎么说,工作人员记下手机号码,眼睛只盯着电脑屏幕,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了。
好不容易,梅女把老范推到街上,天空已经布满了乌云,有了雨前的征兆。梅女想抄近路回去,偏偏有建筑工地的工程车堵住了路口。
雨,说落就落了。梅女想把老范推到屋檐下躲一躲,可到处都是楼房,却找不到一个能够躲雨的屋檐。
这是造的什么孽啊?梅女叹息道。她全然不顾自己,撩起衣襟就去擦老范脸上的雨水。可是,那么大的雨,雨水怎么能够擦得完呢。
好不容易将老范推到家,看见进生在家里招呼家庭安防公司的师傅装监控,她鼻子一酸,突然想哭,却只偷偷抹了眼泪,忍着没有哭出来。进生呢,瞥了他们一眼,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进生在这个节骨眼上装监控是什么意思,是与连生共同商量的吗?怎么没有听他提起过?梅女一分神,老范的木桶推车被门槛卡住了,他的嘴巴在哆嗦,似乎半边身体都在颤抖。
六
老范坐在学步车似的木桶里,咧着嘴笑。他的右手紧紧地拽住木桶沿,左手垂勾着悬在桶外。老范皮肤比生病前白净多了,手上的青筋暴突明显。从洗头方便考虑,梅女将老范的一边倒头发剃成了光头。老范嘟嘟囔囔,那咧着嘴笑的神情,几乎与小孩无异。
为了老范肌肉不出现萎缩,身体不生褥疮,梅女是想尽了办法,又揉又捏,又抬又拉,又搓又洗,累得够呛。麻烦的是,老范吃饭容易呛着,有时,梅女喂老范吃粥都呛着,咳个不停。甚至,有时大小便还拉在裤裆里。梅女感到匪夷所思的是,老范烦躁不安的时候,看到电视里播出《华豫之门》《华山论鉴》等鉴宝节目就慢慢安静了下来。这一细小的发现,让梅女涌出了泪花,说明老范的脑袋里还是有残存记忆的,或者说,老范的病情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没有时间,梅女买菜、做饭,甚至一日三餐只好应付着过,剩饭剩菜也舍不得倒掉,微波炉热一热照样吃。去一次菜市场,她恨不得搬一大堆回家塞在冰箱里。有时,去菜市场都抽不开身,直接让邻居帮忙捎点菜回来。连生还好,能够踩着时间回家,帮衬打个下手。进生却很难说,三天两头不回家吃饭。梅女问进生,他只有一个字:忙。到底忙什么?是谈女朋友了,还是工作或者其他原因?梅女又不好问。日子久了,梅女嘴上不说,心里对进生还是挺揪心的。确切地讲,她觉得与进生之间有隔阂。隔阂在哪?她也弄不清楚。
在梅女心目中,进生仿佛成了埋在她和老范之间的一枚暗雷,说不定哪天就炸开。出乎意料的是,进生的暗雷没有炸响,秋玉却找上门来了。
秋玉到来时,梅女刚刚把老范哄着,转移到桶外,她正用皮筋勒住他的脚在艰难地挪动。梅女满身都是汗,有些恶心与眩晕,人都快要虚脱了。
哟,我以为谁呢,有的人也不掂掂自己几斤几两,死皮赖脸地就要钻这个门。看来,我真的是小看你了。我不得不佩服你的眼力,苍蝇盯蛋,一盯就是一条缝。秋玉一只脚站在门里,一只脚还站在门外,面无表情地说。
听话听音。很显然,秋玉今天不是来做客的,她的话里带着一种刻薄的酸味,还有挑衅的意味。梅女累得要命,没有力气去接秋玉的腔。来者都是客。梅女安顿好老范,腾出手还是为秋玉泡了杯茶,也没吱声。梅女注意到,秋玉染过的头发正在褪色,发根部分是白的,发梢是黄而枯的,脸部神情黯然,下巴尖瘦,气色比上次差多了。梅女有种预感,秋玉的家庭出现了状况。先前,连生说母亲嫁的那画瓷器的镇巴佬好赌,三天两头不回家,梅女还不敢相信。
坏了,坏了,这博古架上的梅瓶呢?秋玉的声音近乎是惊叫。
尽管不想搭理秋玉,但,博古架上的梅瓶不见了是事实。梅女依稀记得梅瓶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不见了。记得当时,老范曾经拿着梅瓶想告诉自己什么,是自己把老范的话挡了回去。是失窃了,还是……梅女越想越乱,脑中一团糟。
败家子,当时我想拿走梅瓶死都不给,结果呢?哼!那么贵重的东西,要么让母狗吞了,要么等着带到棺材里去。秋玉的话,不是刻薄,是十分过分,一点口德都没有。
梅女的心像被东西堵着绞着,在隐隐作痛,她根本没有心思与秋玉较嘴劲。
秋玉看到梅女像傻子一样站着,瞄了一眼她中指上的黑翡戒指,悻悻地说,你这枚戒指,水头不错哩,是我退给老范的。说不定呀,他还送过古董店里那个狐狸精呢。轮到你,已经不知是第几手了。
梅女算是领教了,以前老范说秋玉的嘴巴不饶人,她还半信半疑,接触几次,果然。心里暗想,像她这样的妇女,当初老范离婚是对的。薄情的人有,能够这样薄情的,恐怕只有她秋玉算一个了。怎么说,老范也是她前夫,都病成这样了,不但漠不关心,还有心思嚼烂舌头。
哟!奇了怪了,一细看,怎么还不是那么回事,水头不对呀,这黑翡戒指不会掉了包,是赝品吧?
秋玉哟地一声尖叫,让梅女吓了一大跳,下意识地用右手把戴戒指的左手捂住了。不过,她脸上疑惑的神情,瞬间就消失了。
赝品怎么啦?即便是赝品,我也喜歡。何况,比有的人吃不到后悔药强。梅女的话,仿佛把秋玉噎住了。
好不容易,秋玉咬牙切齿地吐出两个字:出去!
在梅女的耳中,秋玉的声音比窗外的蝉鸣还无聊,直刺耳鼓,她白了秋玉一眼,不耐烦地说,贱不贱的,也不是你说了算。嗯,有事就直说吧。
秋玉走到老范面前,老范的神情没有任何变化,他的眼中是空茫的。秋玉干咳了两声,说,嗬嗬,八字还没一撇呢,就把自己当回事了。也不睁眼看看,我是谁。再说了,连生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这个家还是我说了算。还有一点,想必你死都不会想到,进生也是地地道道姓范的,他是老范的儿子,只不过不是老范和我生的。明白不,老范不是省油的灯。
你是谁?我管不着。重要的是,我知道自己是谁。梅女忽然觉得,秋玉有些可怜,别看她表面貌似有一层坚硬的壳,其实内心是脆弱的。甚至,她的想法完全超乎常理。一个正常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但有一点是梅女想不明白的,既然进生是抱养的,他和老范又有怎样的故事呢?重要的是,老范连鼻孔风都没对自己透一点。
岂有此理!这话轮不到你说。在这个家,你算老几?你以为,母狗摇下尾,公狗上了身,就成了。屁!秋玉朝地上吐了一口痰,气冲冲地说。
梅女受不了这样的侮辱,气不打一处来,回敬道,千只草鞋,想必还是头只的好吧。我问心无愧,不像有的人,拣七拣八,拣得瘦皮眼瞎。
秋玉啧啧两下,一脸的怒气,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难道,你敢说不是心有所图?老范人废了,可他的钱没废,他的古董没废。
听,你还好意思提老范,你配吗?梅女厉声问。
凭什么?我不配,你……你配?秋玉的声音虚虚的,低了几度。
没工夫和你闲扯,蜂窝炉上还煎着药哩。说完,梅女轻蔑地看了秋玉一眼,特意转了转中指上的黑翡戒指,然后用木桶推着老范去了厨房,把她一个人撂在了客厅,似乎把所有的疲惫与憋屈都甩在了身后。
突然,秋玉颤颤地笑了起来。梅女没有转身,听声音,她觉得秋玉一定笑得很痛苦。这时,梅女的手机振铃“咚咚锵咚咚锵”地响了,来电显示是民政局的固定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