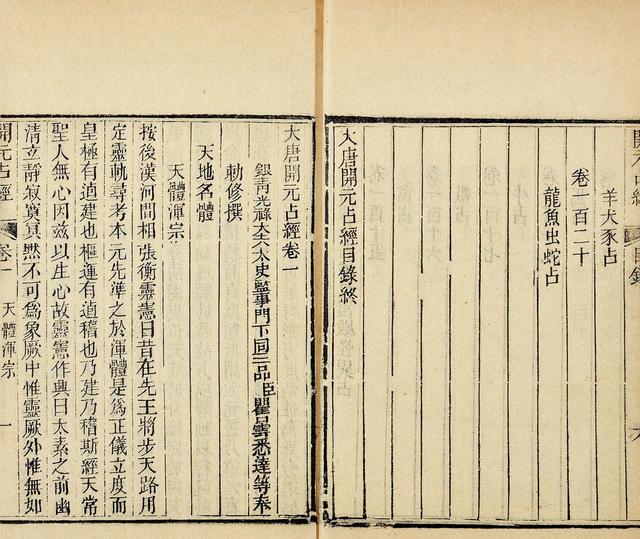星命之学在唐已较风行,不少士大夫都信之不疑。例如韩愈,从他为李虚中所做的墓志铭中,已可看出他对推命之学的赞赏和崇信,此外在他的文集《昌黎集》中,又找到一首自叙其星命的诗,曰《三星行》。
现在讲文学史的人,是不会提到韩愈对星命学的兴趣和他的这首诗的,因为他们觉得这是迷信的货色,对一个大文学家,讲他的迷信,似乎不大光彩,所以人们就为他忌讳这些东西了。这当然是现代人的思考方式,用自己的心去度古人的心,当然就会产生隔阂和偏差,于是今人心目中的古人形象便残缺不全,面目全非了。
从星象学的观点看问题,会帮助人们丰富对古人的了解。韩愈的《三星行》是这样写的:
我生之辰,月宿南斗。
牛奋其角,箕张其口。
牛不见服箱,斗不挹酒浆,
箕独有神灵,无时停簸扬。
无善名已闻,无恶声已讙,
名声相乘除,得少失有余。
三星各在天,什伍东西陈,
嗟汝牛与斗,汝独不能神。
前人说这首诗是韩愈自悯其生多遭人毁而作。诗的大意是,我诞生之时,月在斗宿。斗宿之前为牛宿,之后为箕宿。奋角张口,都是对其形状的形容。三星即指斗、牛、箕三宿。三星之中,牛、斗并未对我的命运产生什么影响,所以说牛不能驮箱,斗不能舀酒浆(指二星徒有牛、箕之名,而无其实,比喻二星对自己命运不起作用),而只有箕宿对自己的命运产生影响和作用,所以说“箕独有神灵”。
箕的影响和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无时停簸扬”,指自己的名声一直象簸箕簸扬一样,一直在赞誉和皆毁之中波荡。而这种簸扬却并不符合事实,所以说:“无善名已闻,无恶声已讙,”即我本无什么善处优点,但名声却已为人闻知,我本无什么恶处缺点,但名声也已宣扬在外。但善名与恶声相比之下,是得少而失多,所以说“名声相乘除,得少失有余”。这就是指訾毁多于赞誉。
最后他感叹道,斗、牛、箕三星分别处在天上不同位置,其形状伸展的方向也是参错不齐(什伍东西陈),其中只有箕起了作用,而牛与斗,却很可叹,“不能神”,即不象箕有神灵那样发生作用。
韩愈的《三星行》所反映的星命观,当然不像那些以星命为业的专家那么复杂,但也确有其独特之处。按星命学看,生时月所躔之星宿及度数,即其人之身宫及身度,由此可知,韩愈确也受了当时星命学的影响,所以他才联系自己的身官之星,来概叹自己的命运。
但他又没有完全按照星命学那一套来理解星宿与自己命运的联系,而是按照自己的独特理解来解释其中的关系,所以才有了这篇《三星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位文学大师对于自己生活及命运的内心思考,并为后人理解其人留下了一份绝好资料
无独有偶,唐代大诗人杜牧也有一份自谈星命的资料留给后人,这就是他的自撰墓铭。此铭载于《樊川文集》卷六中,在叙述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后,杜牧又按星命学对自己的经历遭际做了总结,他说:
我生在角星(命宫所在),昴、毕对于角而言就是第八官,叫做病厄官,也叫做八杀宫,土星在此宫。此时火星继木星之后为王。杨晞说:“木星在张宿,对于角而言,是第十一宫,叫做福德官。木为福德,大君子救于其旁,无虞也,我自作湖州太守不到一年,迁为中书舍人,这是木还福于角,足矣。其后土火还死于角,宜哉!又自视其相貌,目流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斯寿矣,某月某日死于安仁里。
从这篇文字中可以看出,当时星命学已比较成熟,而杜牧对此学亦较精通,故能应用自如。此外他还懂相面术,与星命学配合运用,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