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柏桦,译者丨袁剑、刘玺鸿
历史常常被认为是过去事件的事实上的连续,但其也是过去事件的当下叙述。这第二种或者说叙述性的层面,则基于文人墨客的书面记载。诸如纸钱习俗这样的案例中,想要在这些书面记载中抓住活生生的现实是有困难的。这一问题也困扰着人类学家。
另一方面,牢记不要顺从我所在领域当前的学术潮流——也就是对于那些所谓有“精英主义”意味的东西置之不理
(例如,文学作品)
,并将农民习俗视为对“独裁”政权的“反抗”形式,以及大众不管怎样都被帝国秩序所奴役
(虽然无可否认并不总是处于自主状况)
——是十分重要的。许多像纸钱和缠足这样的习俗都被指向这种奴役。
在这样的警醒下,我接近纸钱习俗历史的方式就包括了五个意在解释其缘起抑或流行的假设。
(1)这一习俗来源于儒家传统,尤其是当其在有关仪式的经典文献中被明确表达的时候;
(2)这一习俗的流行伴随着印刷术的出现,而印刷术的出现则受到佛教文本和附身符的刺激;
(3)这一习俗的发展是信托文件和远距离商贸发展的意识形态上的对应物;
(4)这一习俗变得流行,成为民众将其祭品加以经济化的方法;
(5)这一习俗变得流行,使民众可以在参与宇宙和帝国秩序中的过程中,同时嘲讽帝国为了维持自身所颁布的限制消费的规定。
最后一个假设正是为了使这一系列的解释更有说服力。所以,虽然我认识到每一个假设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并没有任何一个可以代替其他四个,但是我很赞成最后一个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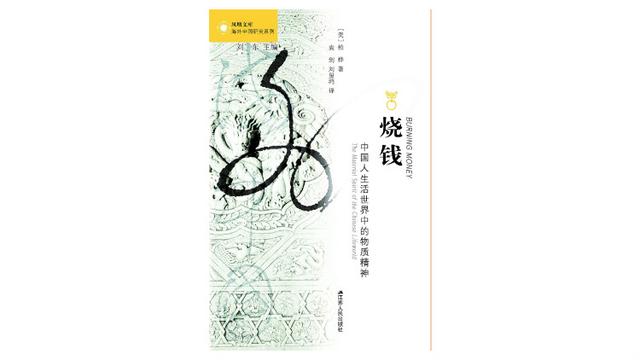
《烧钱: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质精神》, [美]柏桦著,袁剑 / 刘玺鸿译,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丨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版
我研究纸钱历史的起点和许多中国历史学家一样,即儒家经典《礼记》中的记载。正是在这里,有着对纸钱的“终极神圣性假定”,虽然《礼记》对于这一习俗的记载,时间上要比官方“纸的发明”早几百年。其首要的主张,就是“死者”是非实体化的魂
(souls)
和灵
(spirits)
,而且它是有感知能力的。这一点,在《礼记》的文本中,甚至是英文译本中,都是相当吸引人和意味深长的:“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
《礼记》清晰地表明,非实体存在处于一个与活人不一样的感知秩序中,因此他们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每一种感知模式
(活着的肉体,已埋葬的死者的魂魄,分离出的或非实体的灵)
都有其自身的感知需求,因此也就需要不一样的供奉方式。死者身边的财宝、明器或者说对灵的供奉,是与奉养活人的器物和方式不一样的。
《礼记》似乎认可两种类型的陪葬品。一种是那些最初由活人使用,现在则被废弃的器:“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琴瑟张而不平”。另一种则是不能用于活人的东西的复制品:“涂车、刍灵”。《礼记》除了没有提及纸制的器物之外
(虽然提到了稻草,但除了由稻草而来的草纸制作的纸钱外——还有纸制的奴婢、二奶和影星——都可以做)
,其还一直坚持依据感知方式的不同将器物分类,这成为了纸钱习俗的自明公理,并且在据说是孔子撰写的《礼记》成书后的几百年才成型,在今天依旧保持其合法性。
《礼记》作为当今世界的一个清晰而又戏剧化的表达,可以在河北蔚县的冬祭中找到。在这片黄土高原的农田中,大型的汉代墓地附近不时会出现逝去的家族成员和先祖的墓地。当我在2007年11月的一个早上参加我的房东及其亲属在墓地的冬祭之时,我感受到了这种古老性的存在。冬祭的核心环节是向新坟或老坟供奉冬季衣物。女人缝制出洋娃娃大小的黑色棉衣或丝衣,还要为“新坟”——三年以内的死者——做外套、裤子和鞋。三年之后,这些坟墓就会成为“老坟”,这时候所做的衣服尺码和颜色并未变化,但是改用纸来做。

当这些旧坟在时间和记忆中逐步消退的时候,这些无论是供奉给尸骸还是鬼魂的冬季衣物,都由一团棉花和一张藏青色的纸制成。当然,读者要明白,蔚县的农民并没有说他们是按照《礼记》去做的;相反,对他们而言,这只是经验原则,实际中的行为会根据情境不断进行调整。
与儒家的箴言相平行的是历史的另一个维度,也就是制纸技术的持续改进。纸张首次用于死者相关仪式是在东汉时期,纸被放在坟墓前,用于替代金属货币。这发生在汉和帝时期,纸也被认为在同一时期发明。接下来则是在随后500年中,纸如何出现在墓地中代替金属货币和织物
(丝)
货币的零散片段。虽然已有证据表明,就连这些金属硬币都是专门制作出来的陪葬品,而且也与儒家的主张和礼仪相一致,但是不清楚的是,是这些纸本身就有货币价值,还是说仅仅是价值高昂的金属和丝织品的便宜仿制品。
在汉唐之间的这一时期,纸张的技术性和实用性都得到了发展。其它两个型塑纸钱习俗的关键因素开始发挥作用:佛教的兴起和印刷技术。佛教的兴起已经得到很多学者的重视,与之相关,木版印刷的出现也受到关注,被认为可以追溯到隋朝。印刷术使佛教可以以经文和符咒的形式在民众中传播,这是纸钱出现的主要动力。
最早记载“纸钱”的文献之一是公元7世纪的佛教文本——《法苑珠林》。里面有一个鬼故事,说的是一个有着丰富神灵知识的人解释说“对鬼魂有用的东西和对活人有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黄金和丝绸是唯一可以在两者之间共用的东西,但如果是仿制品则有特殊的用途。因此我们必须用黄色的锡箔纸来制作黄金,用纸来制作丝绸,这样的东西会比其他东西更值钱”。
对于纸钱的首次描述,与我们今天所见是完全相容的。这一广为流传的故事有着其他版本,最主要的一个记载于《冥报记》中。13公元9世纪的时候,纸钱就有了它最通用的形式,也就是钻孔的草纸,而且这与现在制作和销售的纸钱样式很相似。
文学家段成式提到,在他搜集和出版的鬼故事中,就有钻孔的纸:在唐宪宗时期,长安城西北部有一个叫李和子的人得到阴间通知,要其为自己吃掉的460只猫和狗偿命
(想必是违反了佛教的理念)
,但是他想通过买“衣服和凿楮”烧给鬼吏的方式来延长自己的阳寿。甚至如果佛教与纸钱在这里存在着强有力关联的话,纸钱习俗相较于佛教也是独立发展的,并且与本土仪式中的奥妙和礼仪有着紧密的关联。正如当下所展现的一样。
排除与宗教和神秘之间的关联,纸钱习俗的最初动力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一些发现表明,纸钱的流行与纸币
(或者说真的钱)
的出现处于同一时期。这是唐宋商业革命的一部分,这一变革起始于公元621年唐高宗对缗钱价值评定建立的新标准,他将传统基于钱的净重进行估价变为基于每一串钱的加权平均重量进行估价。这种标准下的新货币上面,刻有“乾封泉宝”字样。这种货币外圆内方缀连成串的制式,可以追溯到西汉的金属货币,并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
但是这一标准促进了随后几百年的商业变革,并进而促成了用纸来传递货币财富这一方式的出现。到了公元9世纪,由于钻孔草纸被用于仿制的金属货币送往阴间,纸被用作交易的信用凭证,以及一系列黄铜供应带来的现实问题以及携带大量金属货币或其他一般等价物
(银、丝绸、其他纺织品、盐等等)
进行交易带来的不便,刺激了新的货币标准的出现。商人开始使用从当地柜坊获得的印纸作为交易收据。
在公元995年,四川成都的商人开始使用“交子”作为私人交易的媒介。到了公元1024年,宜州官府发行了第一种官方纸币,分别代表从一到十贯钱不等。这引起了中央政府的关注,他们在意的是商业秩序和纸币的印制,规定纸币造假是经济犯罪。
到了12世纪,纸币每年的发行量相当于两千六百万贯钱。在元代,总量进一步提高:“在整个元朝,货币体系基本上都是纸币”。侯锦郎注意到,也是在这一时期,“仿冒的纸币”开始出现,这种纸钱直到20世纪变为法定货币的仿制品之前,我们对其都知之甚少。当宋元时期,纸币在现实世界的商业使用中的一系列问题得以解决的同时,也经常面对一些现实问题,例如纸币倾向通胀,伪造、磨损以及相互抵触的货币管辖权问题。
等到了明朝,尤其是清朝的时候,纸币不再获得朝廷的偏爱,虽然私商依旧使其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流通。当用作真钱的纸币在明清时期不再受官方欢迎的时候,用于灵界的纸钱反而在全国流行起来,并且从宋朝一直延续到今天——毕竟它是一种想象性经济。
第四种也是被学者广泛接受的一种理论认为,纸钱的流行是普罗大众对他们丧葬花销的一种节省行为。这一解释利用了这样的典范观念,献给死者的财宝(比如随葬品)应该被降低级别或者用常见的原料,或者是用泥土、稻草等其他更便宜的原材料制作比例缩小的复制品,另外就是得对活人没什么用。
正如高延指出的,这些实践遵守了儒家教义,提倡葬礼的适中和节省,以避免过分占用生者有限的资源。
(这一教义与禁止奢侈的规定也是一致的,用来限制不同阶层的行为)
。除了在禁奢令基础上实践这样主张之外,儒家的经济节省直接表现为允许穷人家庭在经典规定上减少祭品的尺寸和花销。当宋朝政府运用诸如朱熹的《家礼》这样的礼仪指导书籍在民间复兴和传播儒家教义的时候,《家礼》也不断告诫道,仪式的形式要根据家庭的物质财富状况加以调整。比如:
玄六纁四,各长丈八尺,主人奉置柩旁,再拜稽颡。在位者皆哭尽哀。家贫或不能具此数,则玄纁各一可也。其余金玉宝玩并不得入圹,以为亡者之累。
除了明确允许在仪式花销上加以节省,纸钱在朱熹的《家礼》中并没有被提及,即使普罗大众采用纸钱也已经有四百年历史了。朱熹和他的那些文人前辈、同辈和后来者,对于纸钱都表达了一种喜忧参半的态度。当大多数人认为烧纸钱是粗俗的和错误的“礼”的表达的时候,少部分人则认为,作为一种对祖先的圣礼是可以接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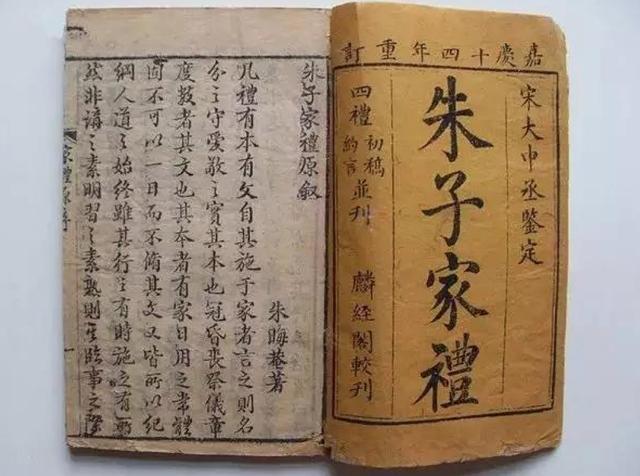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朱熹之前一个世纪的哲人邵雍在春季和秋季祭祀祖先的仪式中都会烧楮钱。同时代的程颐,对此感到特别惊奇,并问比其年长的邵雍为什么这样做。邵雍回答道,“脱有意,非孝子顺孙之心呼?”。南宋孝宗皇帝在位时期,受到朱熹的影响,据说也烧纸钱给他的先祖。当文人雅士对此发出抗议,认为这是一种俗仪,不适合他的天子身份,但是皇帝认为在一个世纪前已有了邵雍这样的先例。正是邵雍的哲学帮助确立了正统儒家士大夫朱熹的官方地位。
此外,据说皇帝宣称邵雍在制作其先祖的祭品时,没有用过真的钱。但是,邵雍对纸钱习俗的捍卫在文人雅客和官员那里没能获得认可。更为典型的是另一位著名士大夫司马光,他与邵雍是同时代人。司马光指出,纸钱的流行,是因为要寄送一些表达哀悼的礼物给服丧中的亲属和朋友,于是每个人都寄送纸钱去烧;但是他又说道,这样的行为对于服丧的家庭来说是毫无作用的,而且如果能收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反而更好。
在《家礼》中,朱熹对司马光这样的说法产生了共鸣。他评论道,要供奉(给那些服丧的人)就应该用(真)钱或丝绸。他进一步说道:“执友亲厚之人,至此入哭可也”。19世纪晚期,也就是七百多年以后的厦门葬礼上,朋友和亲属带来了代表哀悼的东西,就是锡纸,用来当做“棺材纸”烧掉。通常的礼物开支列表被认真保留。朱熹的告诫的确被注意到了,但是“钱”一直被视为“纸。”
其它两个对纸钱习俗的假设,可能更看重儒家认知规则的强化:所谓与佛教的联系和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的浪费。这关联到国家收入来源的问题,也就是要确保劳动力被集中到农业以及劳动产出能于国家有用。许多基于国家利益的儒家学说推动者都将纸钱和佛教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和财富,而这些人与物在国家手中可以更好地运用。
此外,纸钱推动阴间活动走向繁盛,而这些活动很容易被那些具有对抗性的神秘势力,诸如萨满、道士、风水师和僧侣所操纵。他们本身在时间和空间上与日常生活嗜好、民众关心的事务以及那些厌恶儒家秩序的人靠得更近。这些相同的神秘感知往往都是一些关于奇迹显圣的民间故事,但还是被诸如洪迈《夷坚志》这样的文学作品搜集和记录了下来,其中包括的许多关于纸钱的记录都无伤大雅。文学作品对纸钱习俗的使用一直持续到后续朝代以及艺术门类——元杂剧、诸如《金瓶梅》和《红楼梦》这样的明清小说、民国食代的故事与诗歌,甚至《苏丝黄的世界》这样的好莱坞作品中。
在文学作品对纸钱的使用之外,纸钱也成为不论王朝史还是地方志都关注的话题之一。我们发现,从北宋开始,开封就有制作纸钱的作坊,还有专门出售纸钱的店铺,而民众也在拜祭仪式中使用纸钱。当纸钱的生产成为地方和区域一项引人注目的产业的时候,官方表示出了对其将劳动力浪费在纸钱生产上的担忧。我并不认为这一担忧可以被过分强调。正是那些上流社会的人士,尤其是有为官背景的人,从他们的视角看来,所谓的纸钱习俗“经济”是最脆弱的。
例如,1139年,士大夫廖刚向宋高宗呈递了一封劄子,表达了对东南地区的农民放弃农业而去制造和焚烧纸钱这一现象的警惕。这一地区对于宋高宗所在的杭州政权来说,是农业和赋税的基础,该地区承担了极大的赋税,用来支持杭州政权和女真人之间的争斗。结果就是反抗与镇压的蔓延,因此造成了大量生命、劳动力和耕地的丧失。廖刚写到:
臣闻天下事有人情所未厌不可以强去者,去之未见有益,存而不问未见其害,则存之可也。其有世俗积习之弊,所从来久远者,存之而民不知其非,去之而民实受其赐者,又乌可以不去之哉!此则在于圣智开天下之昏愦,以与之一新其耳目尔。臣尝怪:世俗凿纸为缮钱,焚之以微福于鬼神者,不知何所据依?依非无荒唐不经之说,要皆愚民下俚之所传耳!使鬼神而有知,谓之慢神欺鬼可也。兹固不足论,惟积习久远、送终追远者以此致其孝,祷祀祈祝者以此致其诚。是使南亩之民转而为纸工者十且四五,东南之俗为尤甚焉。盖厚利所在,惰农不劝而趋,以积日累月之功,连车充屋之积付之瞬息之火,人力几何?其不殆哉!窃痛今天下之农夫,死于兵寇者过半矣。而东南不耕之田在在有之,可谓民力不足之时。而迩来造纸为钱者益众,愚民终不悟其不足以救祸,然则此弊将果何时已耶!臣谓末作之妨农,其它犹或有用。若穷力以输鬼工,倾资以给野火,尤无谓也,臣愿陛下断然下焚纸之禁,斥其有害于农无补于教,使愚民顿悟百千年习俗之非,不亦善乎!此臣所谓去之而民实受其赐,则不可不去之者也。若曰:凡民之于鬼神,孝子之于其先,必欲有以致意焉。则如释氏经幡之类,量许焚化,以贵贱为之限制,亦足以徇其情矣。此殆所谓民所未厌而存之未见其害者。大抵弥文之弊近世为甚,簿书案牍之繁百倍于古。姑置不论,且如尺书通文,古人不过一纸。今则不然,必务多以相恱。倘亦为之禁约,则敲冰屑玉无所于售,将亦易业而为农夫矣。是率天下以为敦本务实之事也,岂小补哉!幸圣明裁之。
劄子的最后,透露出一种对大为流行的纸钱习俗勉为顺从的意味。除了禁止这一习俗,廖刚希望纸钱的使用可以真实的佛教行为来进行。有一些例外是,在士人阶层有极少的赞同声音,宣称纸钱习俗是供奉鬼神的一种经济的方式。除了一些高官,以及在之前的案例中提到的一位宋朝的皇帝用了纸钱之外,这一习俗通常被暗示与佛教的传播有关,或者是神秘学,或者是无伤大雅的其他旁门左道。此外,这一习俗大行其道,并成为了我将在下一章谈到的供奉仪式的一部分。
虽然,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来看,节约化的假设与以下两个重要的事实并不一致:中国民众经常在葬礼和纪念日献上真实的财宝,并宣称会因为这些花销而获得名声,也愿意承担这些债务来埋葬和纪念死者。尤其是在社会流动性和商业化水平提高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行为就更为常见。在这种情况下,禁奢令会放松对生活世界的束缚。第二,更为重要的是,用纸来对俗世的财宝和金钱进行仿制,并不能避免那些奢侈的行为。
当我们将第二点和那些流行的指导传统仪式的手册中依旧保持对消费区隔的敏感这一事实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获得了对纸钱习俗之所以流行的第五种解释:纸钱推动了一种奢侈精神,允许发起一场无限制的仪式,他们可以在供奉过程中通过焚烧来彰显自己。

换言之,纸钱允许民众去愚弄采用了禁奢令的仪式实践。从古至今,禁奢令通过规定人们被允许的展示和行为
(穿着、住行、葬礼、随葬品和纪念物品等等)
来区隔个人的社会阶层和官方阶序,这
尤其体现在礼仪和仪式场景中,更为突出是在葬礼和建筑规制上。包括朱熹作品在内的关于仪式的书籍,对这些区分都很敏感。《礼仪》就记载道:“淫祀无福”。“淫祀”通常指在供奉上是“过量的、放肆的、低俗的、淫荡的”,并且在这本书中,也提到先给一个鬼神的牺牲并不能给他庇佑,对这一行为的“惩罚”简单来说就是,供奉是无效的。
更不吉利的是,每个朝代制定消费区隔法令的统治者能够使这些法令在事实上被强制推行,但与之相伴的,则是诸如科举系统这样的“社会阶梯”不断膨胀所造成的灵活性的增加,以及商业阶层的地位上升,这都对法令构成了巨大挑战。关键之处在于,限制消费的敏感性已经扎根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不可能通过纸钱习俗将之解除。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习俗在那些地位和阶序上都享有禁奢令特权的人看来是“俗”的,但在那些没有什么地位却为阶序的神秘性或者获得社会地位而着迷的人,以及那些对如何控制他们生命可能有话可说的人那里却大受欢迎。
在某种意义上,纸钱习俗是对禁奢令的双重嘲讽。对于一般民众来说,以纸钱来供奉将“祭品”中所具备的挥霍精神展现甚至凸显了出来。此外,这一精神的体现将会引发现实世界中相当程度的真实花销。用纸钱进行供奉所产生的现实世界中的花销构成了持续反对烧钱习俗的理由之一——纸是一种商品,用纸来当钱进行焚烧这一行为,无论你打算如何看待它,终究是在“烧钱”。
纸钱成为一种对统治阶层禁奢令的无情嘲讽这一理论,在考虑到唐宋转型时新儒家思想大众化过程中与商业的关联越发紧密,并使禁奢令的社会影响下降这一事实,则更具说服力。纸钱可以说就是一般民众跟那些将各个统治阶层与一般民众区分的帝国秩序进行博弈时所下的越发重要的赌注。
大概到11和12世纪的时候,烧钱已经是一个十分普遍的习俗了:士人阶层因为这一习俗出现在劳工阶层而对其源头动力进行批评,而劳工阶层对此习俗早就适应了。到这一时期,这一习俗已经固化到中国人生活世界的仪式网络当中,并已经成为无数诗歌、戏剧和小说的文学修辞来源:北宋诗人苏轼在被流放到海南岛的时候发现,在清明节之际,这些边远之地的人们都用纸钱来进行祭祀,便说道:“老鸦衔肉纸灰飞,万里家山安在哉。”
本文摘自《烧钱: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质精神》( [美]柏桦著,袁剑 / 刘玺鸿译,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丨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版),由译者和出版社授权刊发。
整合丨吴鑫
编辑丨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