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书信,曾是我们的先辈传递信息、交流感情的便捷工具,是礼仪与文化的重要部分。阅读一行行文字,心头便涌起几分庄重与愉悦。特别是写给亲人和朋友的信,不带功利,没有掩饰,只有沉甸甸的真情。
可以想象,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家书抵万金”的年代,突然收到亲人的信件,该是何等激动与兴奋。手捧信纸, 字里行间仿佛跳动的都是亲人的气息和一笔一画的惦记。
记得当年我进城读书离开家乡时,爷爷和父母反复叮嘱:“别忘了经常写信回家呀!”每个月读信、写信也成为我最快乐的一件事情。那句平常的“见字如面”, 排解了我多少想家的苦闷和对亲人的牵挂。
如今,电脑、电话普及,手机在握,信息化手段早已代替了传统的书信。无论你是在城乡什么地方,甚至出境出国,只需按下几个简单的阿拉伯数字,家乡消息、亲人惦记、人间苦乐忧喜,都会伴着铃声瞬间抵达。在电话里倾听着熟悉的声音,思绪立刻长出翅膀,飞向朝思暮盼的故乡和亲人……
有一次,我生病住院,却以出国为由,一个多月没与父母通电话。后来父母得知真相,从此每次通电话,母亲总会像过堂一样,要求每人必须讲上几句话,哪怕是句简短的问候也行。我知道,其实母亲只是要听听熟悉的声音,亲自获取平安的信号,图个心里踏实罢了。通话次数多了,双方身体和情绪的微妙变化都能感受得到。身体状况不佳,往往一张口就听出来了。父母刚从地里干活回来,那喘气声会粗重,感冒了会咳嗽,即使痊愈了,一时也会留些声调的异样……
父母年龄越来越大,沂蒙老家来电话,我总是既很期盼,又有几分担心。盼着随时随地更多听到来自家乡、来自亲人的消息,担心的是来自家乡和亲戚邻居的坏消息。
这些年,生活条件好了,我和妻子也形成了每周必与父母通电话的习惯。不过父母一般不会在电话里诉说家里和家乡的坏消息,说的最多的,是些菜园庄稼、家长里短的琐碎事。亲切的声音时常激活我关于故乡的美好记忆:绿油油的麦浪,火把红的高粱,儿童脸蛋般的红苹果,撑开雪白小伞的蘑菇,踩在脚下或黑或黄的泥土,嗖嗖爬上大树察看鸟蛋的少年,山村的鸡鸣狗叫,山清水秀的景色, 乡村的声音、颜色和味道……
“天气预报说有雨呀,可要少出门哦”,“最近气温下降,多穿厚衣服呀”,“我又做了油饼、水饺,可惜你吃不上噢”……母亲多少次像对待我小时候一样,嘱咐这惦记那,甚至用好吃的东西来馋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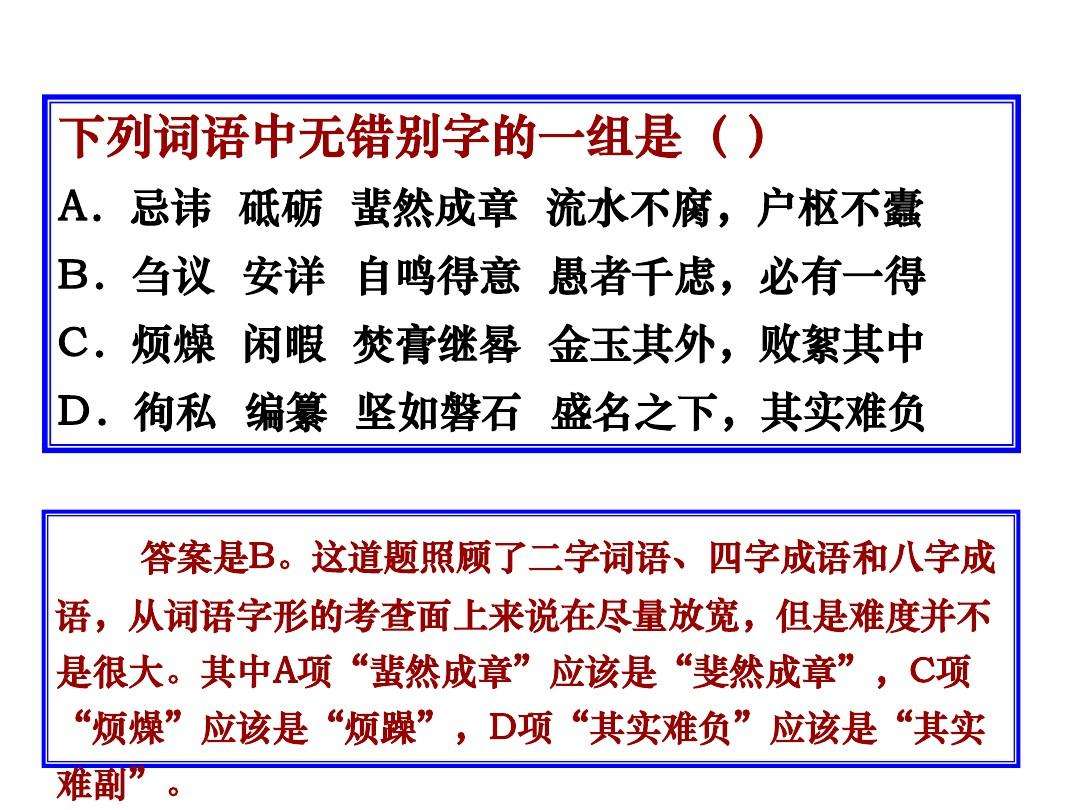
2012年10月底,我妻子跟随学校的团队去美国考察,当时正巧“桑迪”飓风横扫美国东部。年迈的父母是普通的农民,对美国和世界版图是没有概念的。但那个清晨,父亲急匆匆打来电话,用极少见的命令的口气说:“美国刮大风啦,快打电话让孩子他妈回国吧,抓紧哦!”当我把这份牵挂传递到美国,妻子在异国他乡被这热心暖肺的惦记和嘱咐感动得落泪。
通讯发达了,电话一部,耳听八方,网络信箱,情系万里,再不用“请明月代传情,寄我片纸儿慰离情”。亲人之间的联系,更多是手机短信、微信。年长者由于视力和习惯的原因,依然喜欢打电话、接电话,这样方便,心里踏实。耳背了, 孩子们声音就大点。闲暇时,则拿笔给亲人写封家信,心底会涌动昏黄煤油灯下的那份温情记忆,闪动爹娘满头白发堆积的乡愁。
从叮嘱“别忘了写信”到嘱咐“别忘了打电话”,是礼仪之邦的中国人情感交流方式的重要变化。但情感的内核,那条柔韧的精神之线并不为此变化。通讯方式的变化,缩短了时空距离,依旧拴系的,是牵肠挂肚的万里真情与相知相守的快乐时光。
原文载《人民日报》2015年2月7日第12版(大地副刊)
李家淳:伯父自记事起,“爸爸”一词就不曾从我嘴里出现过。面对一个身材瘦削、个子中等的种田男人,我平素总是呼他为“伯”——一个单音节的名词。并且这样的呼唤次数不多,往往要到迫不得已的时候,譬如要钱缴学费、买文具,或者去田里喊他回家吃饭的时候,我便会简短地、嗓音低沉地叫一声“伯”。
少年时,我实在弄不明白姆妈为何要让我们兄弟几个唤父亲做“伯”,而且即连“伯父”都不是。每次听到隔壁的美子甜甜地喊她父亲为“爸爸”,那种亲热、贴切、顺理成章的感觉,真让我很是羡慕。我们唤父亲为“伯”,别扭、生硬,听起来老大不情愿。恐怕他也一样,总是不太喜欢这个称呼吧。看他一脸严肃的表情,估计八成也是不乐意的。不管父子双方做何感想,我们家只有“伯”,没有“爸爸”、“爹”之类的呼唤。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渐渐地熟悉了这样的叫法,接受了“伯”就是“父亲”的事实。
我是二十四岁那年定亲的。双方父母,即我家的“伯”、姆妈和她家的“家”、“奶”(呵呵,比我家的叫法更别扭)要求合合八字(老家的风俗:男女订婚必须八字相合),我才认真地了解了一下对父母称呼上的禁忌问题。据八字先生讲,小孩子出生后,如果出生年月与父母的生辰时间相克,孩子就得改口,用另外的称呼叫自己的父母,越是隔开辈分,叫得疏一些,就越是平安无事。难怪,我得叫父亲为“伯”,而妻子竟然把父母叫做“家”、“奶”,也许她的童年比我还郁闷吧。
“伯”的称谓横亘在我与父亲中间,两个男人,一老一少,长达三十余年,我们之间便注定了会是一种感情隐忍的关系。对于父亲的远年旧事,我陌生得恍如隔世。那是另一个世界,遥远、模糊、虚妄,听来的故事带着明显的不真切。
姆妈说,父亲十九岁被抓壮丁,与同村的十一个男人一起被绑着去了战场。做裁缝的爷爷伤心过度,咳血而亡。小脚奶奶求神拜佛,无济于事。作为童养媳的姆妈刚满十六岁,下面的小叔又患病落了残疾。没奈何,奶奶和姆妈只好关了裁缝铺,开起了一家门面窄小的店,卖酒水、豆腐聊以度日。这样一熬就是三年。三年后,从抗日战场死里逃生一路乞讨的父亲回来了——同村的人只剩他一个幸存者。我们的家族得以绵延下来的因缘,就是父亲面对着爷爷已去,一家破败的境况而跪伏在老屋门口开始的。
我所感兴趣的,并非是我们兄弟何时出生,倒是父亲为何去参加了抗日战争竟又回来?他在外面为何没有混出个名堂?该不会是逃兵吧?这些疑问压在我的心里,憋了好久,始终没有听到过父亲说起,而姆妈又往往语焉不详,前后矛盾,直到现在还是个悬案。对于那段经历,父亲只有几句话:“四十八天打衡阳,小日本的飞机天天在头上像鬼叫,我们把死尸拖在一起做掩体……”就把他在外三年的当兵生活高度概括掉了。迄今为止,我未曾去查过历史资料,未曾印证一下父亲的经历。反正,我们家后来被划成贫农,我们的身世就得以固定在了乡村钱戳湾的几间破屋内。
作为种田的父亲,除了大哥、大姐有机会与他共处一陇田干过活,像我,比唤他“伯”还要陌生。十五岁以前,我去放牛、割草、砍柴、浇菜,这些活计都是姆妈安排。大哥、大姐年龄大,在生产队挣工分,算是全劳力。父亲和他们说话时,声音温和、柔顺;二姐从十二岁起患心脏病,干不得重体力活,基本上在家养病,顺便也帮姆妈做些针线活、煮饭,她也备受关爱。三姐、我、小弟就不同了。我们三个年龄小,不仅读书要花钱,照父亲的说法,我们“纯粹是个消费者”。因此,那些年月,父亲几乎没有和颜悦色的时候。尤其是我,天生一副反骨,在他疾言厉色之下,我的逆反心理特重,往往在家里大唱反调,在外也惹事生非。结果,我没有少挨棍棒的“教育”。每次,当我被这个国民党的老兵吊起来,一下一下被打得鬼哭狼嚎之际,姆妈便眼泪汪汪地替我求情,一家人围在我面前,拼命叫我向父亲讨饶。谁知道我这个“逆子”除了哭,就是不低头。父亲气得半死,一边打我,一边对姆妈呵斥:“慈母多败儿,都是你宠坏了他!”因此,很多年里,父亲实在是懒得多看我两眼。记得有一次,因为和三姐争一把算盘去上课,我们在家打了起来。父亲不问青红皂白,又把我打了一通。而三姐,却躲在旁边幸灾乐祸。我觉得父亲总是偏袒女孩,一赌气跑出了村外,躲到菜地藏了起来。夜色悄悄地降临,我听见了父母亲焦急的呼唤声。事后,我听姆妈说,其实父亲还是很疼我的,每次打完我,他就后悔。这些子女中,只有我的学习成绩最好,父亲是希望我长大后能够光宗耀祖,别像大哥他们一样趴在泥土里忙活一辈子。那时候,我哪里会相信呢?我们之间,日日在屋檐下相见,可话语却少得可怜。
一九八零年,五十岁的父亲突发脑中风,二姐病逝。我们家算是跌进了深渊。患病后的父亲整日躺在床上,半边手脚瘫痪,情绪郁郁寡欢。他变得喜怒无常,动不动又哭又笑。天气好的时候,他会搬一把椅子,坐在院子里晒太阳。阳光淡淡地照射下来,他脸色阴沉,嘴角歪斜,长久地盯着地面出神。偶尔,听见他自言自语地说:“打衡阳那阵,我哪里会想到今日?现在我冇个卵用,叫狗都不应声了。”说这话时,几滴浊泪从他眼角滴下来。我能觉察出一个强悍的男人陷入孤独、无助、悲哀的情绪中无法自拔的心境。我们只当那是一种病症,日子长了,总会感到不耐烦,就都由着他。除了姆妈陪着他,给他安慰,并且不厌其烦地听他说些陈年旧事,大家都不再过多地留意他的情绪起落。
我在外教书、娶妻、生子,父亲是用一个病者的姿态旁观着,他失去了帮助我的能力,而隐匿的爱却悄然漫溢。有一年夏天,我独自去插秧,父亲一瘸一拐走了五里路,为我送来喷药用的农具和当天的中饭。太阳很毒,马路上尘土飞扬。他站在路边,发音不是很全,声音已然苍老地唤着我。我看见他病残的身体歪斜着。噴雾器压在肩上,好像一根大树干压着他的半个身子。烈日下,他被汗水和泥尘涂抹的脸颊变得黄白青绿。目送他归去的背影,我的夹杂了复杂情感的泪水,滴落在饭菜里。
一九九四年初夏,父亲走完了他的七十一年人生。临终时,他对姆妈说:“我供老二读书最多,苦了一世,病了半世,刚刚想过几天好日子,享他一点福,没想到就等不上了……”。
他去世后,我慢慢咀嚼着过往岁月。关爱、哀痛、刚直、守望……这些词汇一一涌上心头。父亲,——“伯”,似乎就在另一个世界看着我们。
轻轻呼唤着“伯”时,我觉得如此地亲切和歉疚。
李家淳,笔名存朴,江西石城县人,广东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天涯》、《散文》、《文学报》、《百花洲》、《浙江作家》、《青春》、《黄河文学》、《青年作家》、《作品》、《散文选刊•下半月》、《文学与人生》、《岁月》、《手稿》、《华夏散文》等报刊,部分文字入选《散文2010年精选集》、《江西现当代散文选》、《行走天涯》等选本;已出版散文集《私人手稿》(珠海出版社2009年8月版)。
公众号“深纹路”
陈德兰:偷吃的老人在这个舶来的节日里,我带着一套新衣,回家哄老爸开心。老爸一定不知道,这个世上还有一个节日叫父亲节。
邻家二嫂来串门,和我娘唠叨起她那八十几岁的老公公: “唉,现在学会偷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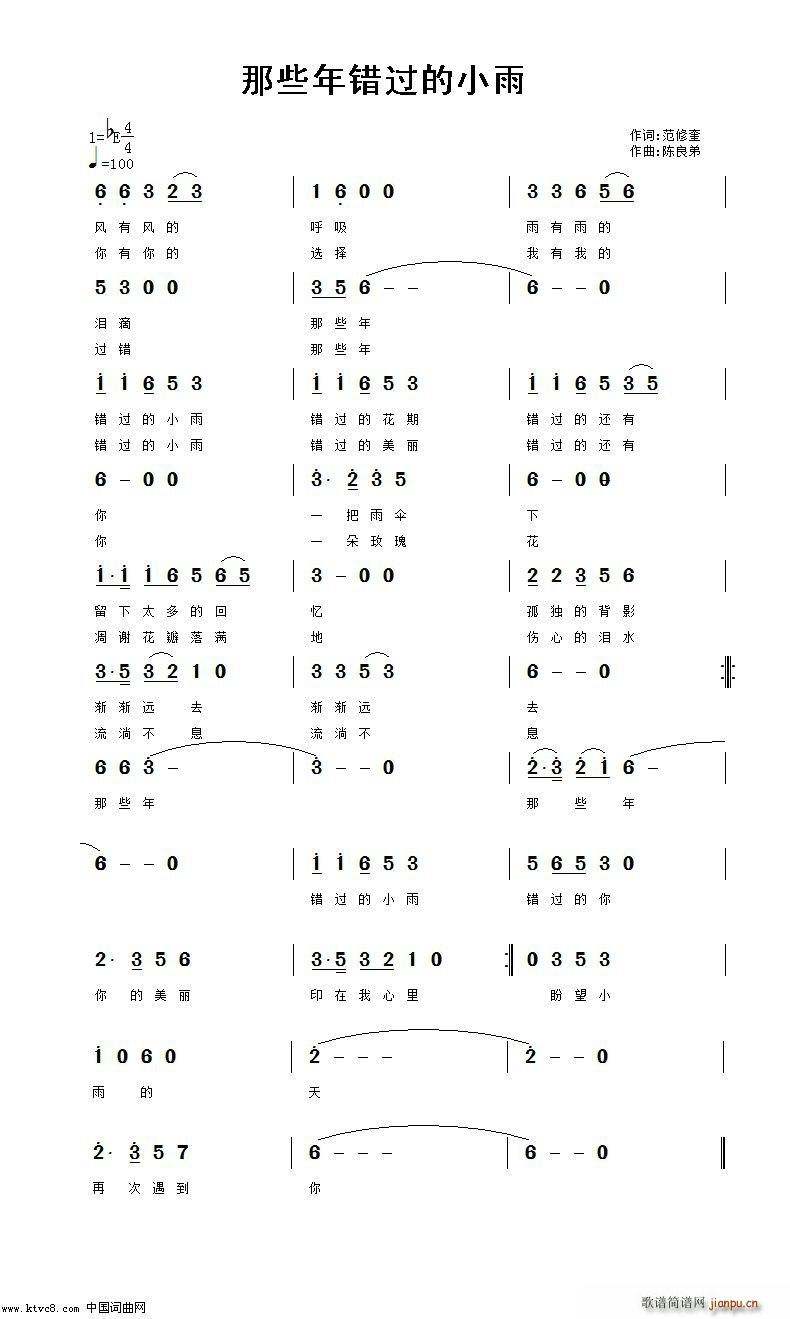
偷吃?现在虽不是家家富得流油,但是吃饱喝好还是没问题的,怎么会偷吃呢?可再听二嫂细说,那情形还真是偷吃。
二嫂说,菜烧好放在锅里,还没盛到碗里时,老头就会趁家人不注意时从锅里捞上一筷子,狼吞虎咽地吞下去,也不怕烫。菜端到桌上,假如老头一人在桌上吃饭,那样子就跟抢吃一样。但如果一家人一起吃饭,老头就不动筷子了,你不给他搛菜,他就不伸筷子。那样子就像过去的小媳妇,团在桌边,可怜兮兮的。
二嫂说这些时,很无奈也很不解。她说,外人看见,好像我们小辈不准他吃饭,可我们谁都没说过什么,更不会限制一个老人吃饭啊。他以前不这样呀,为啥年纪大了会变成这样呢?
二嫂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了奶奶。
那时,父母在田里干活,奶奶一人在家守门,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可随着年岁增长,奶奶什么也干不动了,却好像越老越馋,而且总是一人偷偷地弄了吃。显然,父母对奶奶虽说不上有多细心体贴,可家常过日子,总是事事顺着奶奶,并没有对老人家有任何苛刻之处。但我常听父母说,奶奶在家偷吃,起初我不相信,出嫁后把奶奶接过来住了一个月,发现奶奶还真有偷吃的习惯。
吃饭时,你做再多菜,奶奶也不怎么伸筷子,总要你夹了给她,才吃一点点,还一个劲地谦让。可你前脚刚走,她后脚就偷吃,知道奶奶有这癖好后,我回家时总是轻手轻脚的,有时在家门口见奶奶猫着腰趴在碗柜那儿,我就转会儿再回来。
这是跟我娘学的,当年说到奶奶偷吃时,娘说,不能吓着奶奶,更怕奶奶塞了一嘴东西噎着,当然,主要还是怕奶奶被人撞见不好意思。
后来,我搬到城里住,问过城里的同事或邻居,她们说,家里的老人没有这毛病。我有些怀疑,认为城里人虚荣,不说这些家长里短的事。
二嫂重提这个话题,娘的一番话让我茅塞顿开。娘说,老人觉得自己老了,不能干活又不能赚钱,还要跟着晚辈白吃白喝,心里过意不去;也怕晚辈看他吃得多会心疼,所以才会偷吃。
顺着娘的思路,我终于知道为何城里的老人不偷吃了。因为他们一般都有退休金,底气比较足,所以吃得很坦然。但农民一旦老到不能干活,会觉得自己拖累了儿女,怕日子久了儿女们嫌弃,于是才会有偷吃的习惯。
给父亲试衣时,看他眉开眼笑的样子,很像一个孩子。我不禁想,父母还没老得不能干活,估计现在还不会有偷吃的毛病,等到他们老得不能动时,会不会也……我的眼睛,突然间就涌出了泪水,心也跟着尖锐地疼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