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生过胡子疮吗?你知道什么是胡子疮吗?
如果不知道,你就接着往下看,让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的一九六三年,那也是新中国最困难的年代,我在鹤壁集的六完小读三年级。
我的母亲因为弟弟的夭拆,终日以泪洗面,伤心过度,患了偏头疼的青光眼,最后失明了。为此,我的父亲也辞去了公职。
那年冬天上了大冻,寒冷得很,冻得我浓黄的鼻涕挂在两个鼻孔下,嗤溜几次吸不回去,擤也擤不掉,快要掉进嘴里的时候,我就举起胳膊,用棉袄袖子往鼻子处一抹拉,擦在了棉祆袖子上。时间长了,膈巴在棉袄袖子上,明晃晃硬巴巴的一层。鼻子也被擦得红丢丢的,皲裂着小蚂蚱口子,冷风一吹薅的生疼。
像这种情况,那个时代的小学生也不止我一人。只不过是别人家的父母健全,隔三差五的给孩子清洗了,所以不像我的棉祆袖子,明晃晃的膈巴的那么明显。
失明的母亲,有时候也会搂着我,摸着那硬巴巴的棉祆袖子,暗自落泪。终于快过年的时候,有一天睡觉前,她让我脱了衣服拱进被窝,把我的棉祆拿在手里,用湿布摸索着擦拭我的棉祆袖子,然后让父亲拿着在煤火炉上烘烤,不致耽误我第二天上学的时候穿用。
记得开春后,我的嘴唇上面,长出了一个疙瘩,红红的,后来疙瘩上生成一个水泡,有点痒,总忍不住想用手指去挠挠。后来把那个小水泡挠破了,流出了一点儿有点粘粘的黄水儿。第二天,黄水儿流过的地儿也起了一个红疙瘩,痒痒的。而先前挠破红疙瘩的地方,则结了薄薄的一层黄痂。
就这样来回反复,越长片越大。黄水流到哪儿,就沾染到哪儿长疙瘩,再结痂。我的上嘴片子被那黄色的结痂长满了,下巴上也开始被沾上了。以至于我在吃饭的时候不敢张大嘴,大笑的时候也受限,显得有点很不自然。
我的父亲也很着急,街里卫生所的医生也没啥好办法,只能涂上点紫药水巴干,弄得嘴唇周边的结痂都是蓝蓝的,上学时的同学们也都躲着我。
后来,胡同那头住的王奶奶告诉母亲,“要不叫孩儿他爹领孬儿(我的小名),去西下坡找药铺的老曹瞧瞧吧,人家几辈祖传专门瞧疮。”
母亲就催促父亲带我去找曹大夫。
趁了个星期天,我厮跟在父亲后面,去了西下坡的那个药铺。

药铺已经开了门,一个虎背熊腰的年轻人,正在一块一块的把卸下来的门板,摞到门后靠墙的地方。
一个佝缕着腰的瘦弱老头儿,正在给一位腿上有疮的汉子换药,用一把木镊子从疮口里拽出来虎口长的药捻子,粘满了淡黄色的脓汁。
——恶心死了!我吓得躲在了父亲身后。
那瘦老头儿他戴着一顶黑灰油亮的瓜皮帽,脖子上滴溜着瘸了一条腿的老花镜,瘦削的脸上眼小鼻子大,一撇八字胡还老长。总之,长的不景人。
我躲在父亲身后,从父亲胳痨肢的缝隙里偷偷的看他。
瘦老头给那汉子换上新药包扎好后,问我们啥事?
父亲说明了来意,把我从后边拽出来,推到曹大夫面前。那个瘦老头把滴溜在脖子上的瘸腿眼镜架到鼻子上,略微瞅了两眼,咳嗽了一下,像公鸭一样的干瘪声音,从他那黄牙缝里篦出来,“早干啥了,叫孩子遭恁大罪?!”
父亲则唯唯嚅嚅,陪着笑脸,“好治么?”
“除了搭背疮不好治,其它的都没啥。”瘦老头一边说,一边伸出他青筋暴露的干枯的手,用手指甲扣了扣我嘴唇上的结痂,“疼吗?”
我躲闪着点了点头,嗯了一声。
“这是黄水疮,长在嘴上也叫胡子疮,是平时不注意卫生被病毒感染上的。治是能治,就是时间得有点长,孩子脸上不好看。”
父亲要求曹大夫,“该咋治就咋治,只要能治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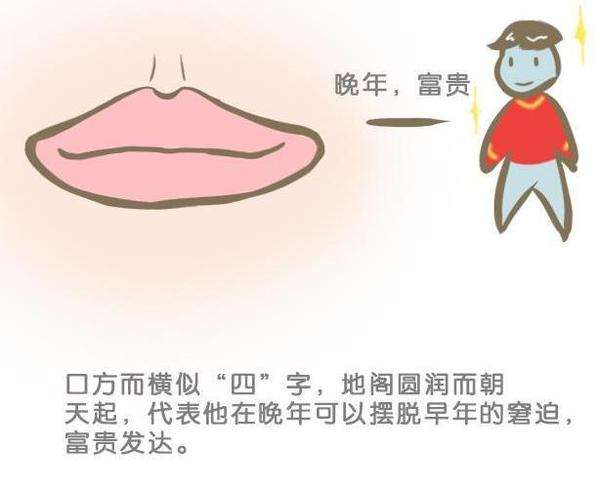
“恁先回去,我今儿上午给恁把药配好炒好碾好,后饷恁来拿药,回去用香油调成糊涂抹上,不到十天保好!”
父亲千恩万谢,然后领我回去了。
下午我就涂上那黑黑的药糊糊了。
由于是香油调制的,又抹在鼻孔下方,一股香油味夹杂点焦糊的中药味,直窜鼻子!
我就这样闻了十来天的香油味,嘴上明晃晃的,黑糊糊的。从第六天起,就逐渐有结痂脱落,进入第九天,基本上就掉完了,露出了粉红的新皮肤光光滑滑的。父亲怕没有好彻底,又坚持让我多抹了两天,直到把那点药用完。
母亲用手摸着我光溜溜的嘴唇,长长的吁了一口气,一个多月来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放下了……
也不知是不是小时候的胡子疮太严重,破坏了毛馕。等我长大后,胡子长出的很不整齐,至今都有点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