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用“女作家”来强调作家的性别时,就已经暴露出作家一般被默认为男性的事实,这一点和社会上许多方面是相似的。也正因如此,“女性书写”在当今的文学中成为相当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它展现了一种新的视角,有别于占据社会主流的男性视角。
3月30日,在上海建投书局与世纪文景联合举办的“女性书写,一种撬动世界的力量”主题展中,开启了一场以“漫游者与艺术、城市的发现”为题的瓦莱里娅·路易塞利
(Valeria Luiselli)
作品座谈会,瓦莱里娅代表作《我牙齿的故事》的译者郑楠与《上海文学》编辑部主任来颖燕参加了座谈。
瓦莱里娅·路易塞利1983年生于墨西哥,2014年获《洛杉矶时报》评选的“阿特·塞登鲍姆新人首作奖”,2017年入选波哥大39位拉美青年作家名录,以及柏林文学奖短名单。她出版首部作品《假证件》时年仅27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新星,被誉为博尔赫斯和科塔萨尔的继承者,是拉丁美洲文学界极具潜力的青年作家。

瓦莱里娅•路易塞利。
真正优秀的作品是雌雄同体的
“女性主义”的思想,最早由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中提出,它偏向激进的女权主义,渴望打破父权制约。西苏所创造的美杜莎形象和女性主义的主题相契合,因为美杜莎的头颅被割下,表示的是男性强制要求女性沉默。西苏最开始是想反对拉康所谓象征男权的男性中心主义,因为“女性一直被写作粗暴地驱逐”。由此,也催生了很多思考性别问题的女性,如波伏娃、伍尔夫。
在这样的思想启发下,女性书写的目的主要在于展现女性作为主体而非男性附庸所进行的文本创作,它有两个目标:摧毁和预见不可预见之事。郑楠表示,上世纪70年代美洲的女性创造了很多作品,正是为了抵抗自上而下的男性强权,进行自下而上的抗争,她们的写作和女性主义是紧密相连的。拉丁美洲从未缺少为女性权利而写作的女作家,瓦莱里娅可以说是对这种传统的继承,而非凭空产生的。
然而,瓦莱里娅本身并不乐意被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她认为,女权主义的成功应当以女权主义的不再呈现为目标。因为,只有大家不再需要强调女权主义,才意味着女权主义的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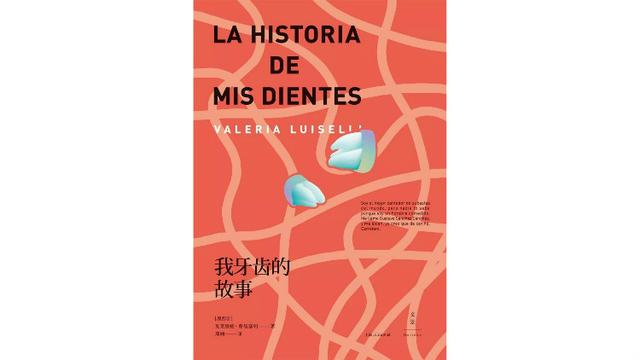
《我牙齿的故事》作者:(墨西哥)瓦莱里娅·路易塞利,译者: 郑楠,版本: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
郑楠说,“我也反对两分法,即两性是对立的,或男性和女性分别是压迫与受压迫的”。她认为,女性文学研究希望建立的是两性共同、平等的写作。对此,来颖燕也表示赞同,她提出,由于性别的客观存在,基于自身性别的写作视角是难免的。但是,女性写作不等于要陷入女性立场。为自身女性的客观身份所限制,会使得视角变得偏狭,很多人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才意识到自身女性身份的问题。
在来颖燕看来,性别意识是一种局限,也是一种基调,但不能任由其成为我们写作的束缚。优秀的写作是关乎人类整体命运的,女性写作所展现的也应当是关乎整个人类命运的。正如伍尔夫所说,真正优秀的作品是雌雄同体的,是超乎性别意识之上的。
在现场,来颖燕还提到一位男性调查者的报告。报告中,当女性作家被问及是否进行女性主义写作时,她们纷纷表示惊讶与不悦。她们并不是专为女性文学而写作,只是在写作中渗透着自身的性别认识,她们反对自己被贴上“女性主义”这样的标签。
恢复小说在现代世界里的“无门槛”
瓦莱里娅的《我牙齿的故事》是一个虚构与非虚构交织的文本。在写作《我牙齿的故事》时,瓦莱里娅将稿件定时寄送给胡麦克斯
(Jumex,国内称“果美乐”)
果汁厂的工人们,由工人们朗读、讨论,并将录音反馈给她,她再据此进行修改。
在这本小说中,有很多文字直接来源于工人们的真实经历,或者录音里的记录,里面有真实的作家,甚至还有真实的照片,而另一部分则属于虚构——这使得她的作品变成虚虚实实的存在。其思考生活和艺术之间、写作和工厂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抑或是缺失某种联系。瓦莱里娅在书的后记中说:“我应当如何在他们之间搭建桥梁呢?与其说是我在写工厂和工人的生活,不如说我是为他们而写的。”
瓦莱里娅的写作灵感部分来源于19世纪的古巴哈瓦那雪茄厂。那时候的老板为了给工人们解闷,会请知识分子来为工人们朗读文学作品或报刊,并发展为一种运动。这种运动不仅减轻了工人的疲劳,还提升了工人的文化水平,后来传出了古巴之外,在很多地方的雪茄厂,如美国,出现了这样的朗读者。朗读者作为一种工厂内的有机成分,为广大工人所接受。美国有些工厂不愿意工人们受到这样的知识启发,便撤销了朗读者,工人们还为此展开各种抗议和斗争。
郑楠认为,本来就有座桥梁存在于工厂和博物馆、工人和写作者之间,只是有时我们自己不去关注它,有意忽视它。很多人,尤其知识分子,对工人的文学是存在偏见的,认为它很粗糙。来颖燕也表达了类似看法,她说,有时工人创造出来的作品更加感人,古巴的朗读者更像是文学对大众的一种切近。
小说是一种叙述的艺术,叙述艺术一直是存在的。在没有小说之前,像传奇等叙述艺术就已经出现。来颖燕认为,小说有更低的门槛,方便我们进入;但艺术不一样,艺术更侧重欣赏性。像进入博物馆,就进入了一个艺术氛围当中,你必须沉入这个氛围来思考、冥想。而小说属于所有普罗大众,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开放的。
在郑楠看来,小说的预设前提是虚构性的,但《我牙齿的故事》里有很多真实的东西。《我牙齿的故事》不仅仅是表达一种女性书写,而是为了文学上被垄断了话语权的人,去进行打通虚构和现实的实验,让现实里实际的、不可忽视的群体重新进入被垄断的虚构世界。这个群体可以是女性,也可以是工人,总而言之,是要恢复小说在现代世界里的无门槛,让小说重新成为大众的东西。

活动现场,来颖燕(左)与郑楠。
当个人记忆和国家记录不相符
瓦莱里娅本人对后现代的“拼贴”标签不以为然,但其确实使用了很多这样的技巧。她的拼贴是有意义的,其反对的是无意义的拼贴。拼贴的过程本身就是作品的一部分。整个文学作品的表现过程都属于这个作品。整个作品形成的过程都融入作品本身当中,呈现给接受者的不是单纯的成品。
对于这种写法,瓦莱里娅有自己的看法。“我希望它是我的调查结果所反映的影响,如果我们要给它贴一个标签,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调查文学。”如果看她的其他作品,也能从中发觉档案研究般的痕迹,甚至从有的文字里,还能见到现实生活中瓦莱里娅的影子。虚拟与真实边界的模糊特质,在其今年新写的《LOST CHILDREN ARCHIVE》
(《失踪儿童档案》)
里体现得更加明显。其中穿插了很多无证难民,尤其无证儿童移民所经历的磨难,而其本来是写一对夫妇带着孩子在亚利桑那州的旅行。
据郑楠介绍,前几年西语美洲比较流行一种小说写法叫autofiction,来自智利和阿根廷。当个人记忆和国家记录不相符时,我们只能通过文学记录下来。真实和虚构的打破,是保全我们记忆多样化的方式。通过虚拟想象来弥补档案记录的空白。瓦莱里娅的《失踪儿童档案》中可以见出这种写法的痕迹。

《假证件》作者: (墨西哥)瓦莱里娅·路易塞利,译者: 张伟劼,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
来颖燕强调,实验性和传统是摇摆的,他们没有一种明确的定义。在任何时代中,原创的书写与传统的书写都是并存的,正是不断有这样原创的书写,才使得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殊作品。瓦莱里娅虽说是实验性的,但其实有些复古的意味,某种程度上回复到“讲故事的人”的时代。根据本雅明的《讲故事的人》,我们现在的经验在不断贬值,人们渐渐丧失了表达自身独特体验的能力,我们不再有“讲故事的人”。
尽管我们试图超离我们的性别局限,我们很可能最终无法超离,但对于这种超离的渴求是应当的,文学创作需要突破这样的局限。瓦莱里娅的文学中也充满了游戏性,其中的一个游戏是给每一种语言的翻译者提供不同的《我牙齿的故事》的文本,她认为这很有意思,但德语译者对其颇有微词,认为这会让读者误以为是翻译错了。这样的游戏性存在于她作品的很多方面,或许这也是其对现实中各种问题的一种揶揄和反讽。
记者:吴鑫 实习记者:陈奎州
编辑:徐伟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