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要过年了,上海写字楼里Linda、Mary、Michael、Justin将挤上火车回家乡,名字又变成了桂芳、翠花、二饼、狗剩。”近年来,类似的春节返乡段子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吐槽亲戚的帖子也屡屡在社交网络上引起共鸣。
青年学者罗雅琳将它们统称为“乡怨”式返乡写作,这已成为几乎每年春节必备的流行文化。在仔细分析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春节自救指南》、papi酱吐槽奇葩亲戚的小视频等“防亲戚”指南的文本之后,她发现,正在春节从大城市返乡的年轻人身上蔓延的“乡怨”情绪,指向的是某种以“城乡价值观对立”的形式显现的代际差异:对大都市原子化生活方式产生深刻体认的返乡年轻人,如今已经难以忍受温情脉脉的“乡土中国”内绵密的人际关系和缺乏界线感的关怀。
被亲戚追问工资多少、职位高低、买房了没有、什么时候结婚生子……类似的经历几乎每一个返乡年轻人都有,这是春节吐槽亲戚的各种段子总能引发热议的大背景。但罗雅琳注意到,当下的乡怨叙事与传统中国寒门贵子一朝发达就六亲不认的故事模板有着很大的不同:如今的年轻人吐槽的不是“穷亲戚”,而是强势的”小城中产”亲戚,他们往往有更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更稳固的社会地位,他们若隐若现的优越感往往让在大城市里尚未站稳脚跟的年轻人抬不起头来。比如在《春节自救指南》中,“二叔”可以拍着胸脯向“我”保证:“一个月工资有多少,到我单位工作要不要?”

因此,“这些关于‘过年回家’的集体吐槽,是‘小城中产的孩子们’在受过高等教育、皈依大都市生活之后返身与父辈之间的斗争。”罗雅琳指出,在大城市生活工作的年轻人的真正身份是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都市新穷人”,于是“现代”价值观便是他们反击父辈的唯一武器。两代人家庭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本是无高下之分的两种选择,却在年轻人占主场的舆论场中被贴上了“现代”与“传统”、“世界化”与“地方性”、“先进”与“落后”的标签,反映出的是乡土中国失去了“现代性”的问题。
罗雅琳提醒我们注意,“乡怨”式返乡写作与学院知识分子的“乡愁”式返乡写作,实际上衍生自同一种文化心理——前者抱怨小城比大都市闭塞保守,后者感叹农村美好人伦关系在城市化进程中被金钱社会所玷污。她指出,这两种返乡写作都以乡村的他者化为大前提,但我们需要自问的是,在当下中国,除了“城市”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正面生活价值的存在,让“乡土中国”不再是现代性追求中的异类?
《“乡愁”与“乡怨”:两种“返乡”写作》撰文 | 罗雅琳
2010年,学者梁鸿出版了“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这本书的写作动机源自她对自己学院内“虚构的生活”产生怀疑,于是她带着一种寻找“真正的生活”、“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和“最广阔的现实”的愿望返回自己在河南穰县梁庄的故乡,希望以一种整体性的眼光探问乡村现状和它在当代社会变迁中的位置。2013年,她又出版了一部讲述梁庄“进城农民”的作品《出梁庄记》。这本书与另外两部纪实作品——美籍华人记者张彤禾的《打工女孩》、新疆女诗人丁燕“卧底”东莞工厂写出的《工厂女孩》,同在2013年出版,让“进城农民”成为当年的热门话题。梁鸿回到自己的农村家乡,以她的家人和乡亲的故事为主线,写作有关当代农民命运的“返乡日记”,这一行为迅速得到呼应。2015年春节期间,当时就读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博士生王磊光写作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成为微信朋友圈和微博等社交媒体的热门文章。2016年春节前夕,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师黄灯写作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再次引发了人们的热烈讨论。这样的写作,或许与中国人文学科正在经历着的“社会史视野”转型息息相关。这些学院内的作者尝试在传统的散文写作中加入社会学的视角,从他们身边亲友的故事中讨论中国农村在现代化和城市化中的命运,既有真情实感,又有学理分析,因而都成为一时流行的文本。
《出梁庄记》描绘了一幅乡土秩序与离乡者共同凋敝的图景。梁鸿以一种现实主义态度勾画出打工者的生存状态,虽然她写了西安、南阳、内蒙古、北京、郑州、深圳、青岛等不同城市的进城农民生活,但这些人的命运似乎是一致的:一方面他们居住在生活条件恶劣的城中村,遭遇欺骗、工伤、排外、羞辱,始终无法融入城市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也对致富怀有不切实际的渴望,参与打架、造假和传销,并积极加入城乡对立的话语生产之中——“城里人好骗”。作者从农村走出,却已适应城市生活,这使她陷入一种身份的两难:同为梁庄的进城者,她与这些农民工有着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亲密性,但城中村、电镀厂等环境,以及农民工为在这些环境中生存所采取的生活习惯和情感态度,也让已经习惯于当“城里人”的作者产生种种不适感。
梁鸿使用“乡愁”来统摄和克服这些矛盾的情感。她在《出梁庄记》的后记中引用帕慕克的“呼愁”,将自己对梁庄的情绪定义为现代化过程中人人都有的忧伤。对中国人而言,乡土是必须背负的命运,它的别无选择性让《出梁庄记》显得格外动人。事实上,这也是当下类似作品在处理城乡问题时所共同借助的手段。张彤禾在《打工女孩》中将“背井离乡”作为自己与打工妹们的认同基点。在徐则臣的“北漂小说”系列中,他也是通过在异乡的无家可归感,把卖假证者、卖盗版碟者、大学生、诗人等北京的“异乡人”联系在一起。“乡愁”具有沟通不同人群的“公约数”性质,当作者将走出梁庄的打工者生活以一种“现代性乡愁”的形态呈现出来,不同身份的读者就都能在《出梁庄记》中找到哀伤而感人的力量。

然而,这又是一种稍显简单的态度,它把城乡在空间上发展不均衡的事实变成了时间上对古老乡村的怀念。《出梁庄记》中的农民工有缺点,但他们代表着故乡,他们的缺点更展现出作为美好理想的乡土风景、人伦秩序已经消逝,从而在使“乡愁”更为浓郁的同时,也造成了对农民工现状的潜在批判。乡愁反过来确认了怀乡者处于现代进步时间之中,而农民工则成为闯入现代空间的他者。书中屡屡可见作者对梁庄人的“国民性”批判:她认为梁庄人对自己亲人在外的状况漠不关心、逆来顺受,认为城市把那些和善、羞涩、质朴的乡亲改变成不讲规矩的打架者,等等。她把梁庄“算命仙儿”贤义姊妹们的麻木归结为“这一切或许与农民身份无关,而与人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的狭窄有关”,反而在贤义那儿发现了与“遥远的过去和历史的信息”相连的安静、超脱的性质和“开放性、光明性”。此时的她已经快要陷入“东方主义”的危险边缘:认为乡村必须是宁静、神秘的世外桃源,乡村人必须淳朴、多情,否则就是自甘堕落,不值得人们对其有所关注或同情。在《出梁庄记》的后记中,面对正在开展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梁鸿担忧梁庄的人将离开泥土和原野,被困在高楼,进入“陌生人社会”,因而感到“疼痛慢慢淹没我的整个身心”。这同样不免让人感到一种“东方主义”:引发伤感的既是农村的现实,也是身为“城市人”的作者那碎裂的田园故土梦。
在《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梁鸿对当代农村在市场经济刺激下的道德衰败和情感离析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同样,在王磊光的返乡笔记中,他也感叹当前农村亲情关系的淡漠和人与人之间的“原子化”状态。在黄灯笔下的乡村图景中,“乡风乡俗的凋零”也是她所批判的对象。然而,对于这一问题,另一位学者刘大先在对顾玉玲的《回家》所写的书评中给出的答案或许更近人情。同为“非虚构”作品的《回家》,写的不是中国农民工,而是从台湾地区返乡的越南移民劳工,但一样涉及劳工流动中伦理格局和情感模式发生变迁的问题。刘大先对此写道:
情感在移动中发生变革,倒未必是被金权异化,而是对于这些人来说,情感过于奢侈——它原本在艰难人生中也不过是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更因为生活的重压而空间被压缩到最小。
那一幅民风淳朴、道德醇厚的乡村图景原本就出自我们的想象。无论是沈从文的湘西,还是汪曾祺的江南,都是作家对城市中的诸种“现代”病症有所不满,从而有意构想出的一个理想国度。人们时常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与当下中国乡村社会进行对照,以此说明传统的社会结构被毁坏。然而,费孝通自己也曾声明,“乡土中国”只是他的一个ideal type(理想类型),一个从“具体事物”中提炼出来、还需要回到“具体事物”中不断核实的“观念中的类型”。乡村的道德状况并非时至今日才遭堕落,真实的乡村生活中从古至今都存在虐待双亲、卖儿鬻女、抛妻弃子等情况,这些情况也并不唯独发生在乡村。若说道德堕落,难道今日中国都市的道德状况会比农村好?“传统的消逝”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普遍状况,只不过人们将乡村视为“传统”的化身,才会对其中“传统的消逝”更为敏感,甚至产生苛责。
只有抛弃这种“乡愁”的视角,才能将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不是看成“伤逝”,而是看成可能的机遇。梁鸿、王磊光和黄灯在谈到农村风俗堕落时,最为忧心的问题之一是农村老人的赡养问题。所谓的“留守老人”,也是当下新闻报道中最容易引发批判的话题。这样的忧心是人道主义的,然而,在有着多年农村实地调研经验的社会学者贺雪峰看来,“留守老人”反而反映了一种新型的“老人农业”模式的兴起。贺雪峰提出了一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即在由年轻农民进城务工获得务工收入之外,由年老父母在家种田,保持原有的农业收入。中老年农村人口很难在城市找到工作,但是,当前农机、农技、农艺的发展使他们完全具备在土地上耕作的能力。这样的“老人农业”是半生产半休闲性质的,不仅具有经济效益,而且有利于农村老年人保持人生趣味,参与人情往来。这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悲惨,反而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农村出现的新型伦理形态实际上是与农村生产方式的变迁相配套的。人文学者因农村风俗的变迁而感叹农村的衰败,却选择性忽视了农村在现代生活之“变”中诞生的诸种活力。他们的“乡愁”是真实感人的,却受缚于一种关于农村的道德化视野,因而削弱了对于农村真实情况的把握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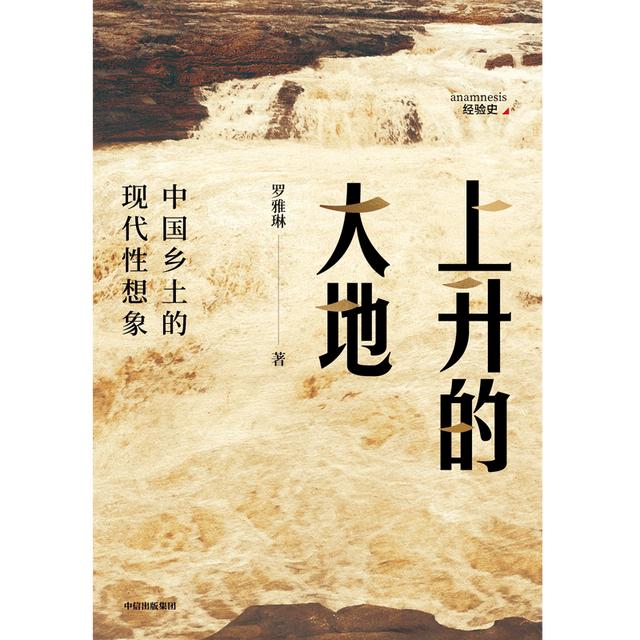
在“乡愁”之外,另一种流行于都市的乡村叙述是“乡怨”。“乡怨”的出现同样与“返乡”这一行为有关,其写作者同样是那些从外地进入大城市并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当他们在春节这样的日子“返乡”之时,一种或可名为“乡怨”的情绪便会集中爆发。
在曾经的流行文化里,“过年回家”是充满喜庆的。20世纪80年代有朱明瑛在1984年春晚上唱红的《回娘家》:“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个胖娃娃。”90年代后期起最火的是陈红唱的《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在这些耳熟能详的文本中,回家充满辛苦,家中不乏唠叨,但它们始终是甜蜜的负担。而如今的春节,“吐槽亲戚”几乎成为年年必备的流行文化。在2017年春节前夕,先是有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春节自救指南》刷爆朋友圈。这首歌涉及父母逼婚、亲戚“围堵”、攀比与唠叨等内容,引发年轻人的广泛共鸣。紧接着,以吐槽成名的网红papi酱也发布了小视频“致某些令人讨厌的亲戚”。继2016年春节前夕的“希望法律禁止所有讨人厌的亲戚过春节”之后,这是她第二次在春节前夕推出吐槽奇葩亲戚的小视频。种种“防亲戚”指南,一出必成爆款。与“亲戚”联系着的,是那个被视为充满人伦之美的“乡土中国”,但当代年轻人似乎更愿意成为“都市”中的原子化个体。从这些文化新现象可以看出,某种或可被命名为“乡怨”的情绪正在春节从大城市返乡的年轻人身上蔓延。
平心而论,家乡亲戚的无尽追问确实是令人厌倦的。工资多少、职务高低、结婚与否、房子大小……这些功利性的问题和露骨的攀比破坏了关于“家”的温馨想象: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不分彼此的互相扶持、无条件的接纳与包容。但这些问题并非仅仅存在于“家乡亲戚”的世界,生活于大都市的年轻人每天同样在进行着类似的自我拷问。只需随便逛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校园论坛,就会发现每日热门话题中也充斥着类似的问题:从要不要出国,到去工资高、没户口的私企还是工资低、有户口的国企,从要不要和家境好但是自己不爱的人结婚,到如何通过房产证上名字的增减维护个人利益……为什么这些问题一从“家乡亲戚”口中说出,就显得如此势利、短浅、面目可憎?
“乡怨”的普遍流行,并不是寒门贵子一朝发达就嫌贫爱富的故事。《春节自救指南》中代表着负面形象的“隔壁老王”是一名有13辆路虎、刚进行过A轮融资的成功人士,papi酱也从未将穷亲戚列为自己讨厌的人群。被强烈吐槽的亲戚大都事业小成、家境殷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乘着东风兴起的所谓“小城新富”“小城中产”。他们凭借在家乡累积的金钱和人脉基础,再加上作为长辈的权威身份,足以在从大都市返乡的年轻人面前指点江山。被教训的年轻人经济实力尚薄弱,又作为晚辈,无法理直气壮地当面反击,只好将自己的情绪在种种吐槽视频、吐槽文章中发泄出来。
年轻人掌握的网络技术,以及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接受的“现代”价值观,是他们反击父辈的武器。因此,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上发布短视频就成了年轻人发泄“乡怨”的主要方式,这是父辈力所莫及而年轻人可以大展身手的地方。这些吐槽作品的立场,也是绝对“现代”、绝对符合当下政治正确的:性别平等、自由恋爱、尊重个人空间。与此相对应,家乡则被呈现为过分“传统”的:性别偏见、“逼婚”、肆无忌惮打听隐私的“熟人社会”。在papi酱的“致某些令人讨厌的亲戚”中,听“喊麦”和唱《好汉歌》成为“讨厌亲戚”的身份符号。在都市流行文化的阶梯上,这是某种“低级”趣味的象征。家乡的情况是否真的如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观看视频、进行吐槽狂欢之后,在经济实力上落败的年轻人终于在精神上、在文化品位上彻底战胜了“庸俗”的“小城中产”。
小城镇曾被视为中国经济的特色和活力所在,在费孝通等人的设想中,中国小城镇的发展能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激发民间活力,促进城乡一体化,避免以往城市化道路中对于农村的抽空。理想中的小城镇既具有与大城市类似的生活设施和福利保障,又保留了乡土社会较为悠闲的生活节奏和温馨的人际关系,是最宜居的地方。如果说,中国传统的故事模式是寒门贵子一朝发达就嫌贫爱富、六亲不认,那么,在当前流行的亲戚大吐槽中,我们看到的却是进入都市的年轻人在强势的亲戚面前抬不起头。这不是20世纪80年代的代表性作品——路遥的《人生》中的故事:回到故乡的高加林虽能从德顺老汉那里得到某种感人肺腑的道德教诲,但除了耕种贫瘠的土地之外别无选择。而《春节自救指南》中的二叔满可以对回乡年轻人拍拍胸脯:“一个月工资有多少,到我单位工作要不要?”“小城中产”拥有这样的底气,正是中国小城近年来发展状况良好的一个缩影。这群人本可以成为那些进入大都市打拼的年轻人的后方支援,却以“烦人亲戚”这样的负面形象出现在大众文化的视野中。“小城中产”恰好是“德顺老汉”的反面:他们可以为下一代提供雄厚的经济支持,却再也无法带来任何精神上的滋养。联想到近年来支撑着节节攀升的北、上、广房价的购房模式是普遍流行的“4+2”(一对夫妻加上双方在小城的父母一起供房),甚至是“六个钱包”(指夫妻双方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们会看到小城市、小城镇之于北、上、广的彻底落败——前者不仅在经济资本上为后者输血,在文化等级上也是远远不及后者的。
这些关于“过年回家”的集体吐槽,是“小城中产的孩子们”在受过高等教育、皈依大都市生活之后返身与父辈之间的斗争。一方面,这是两代人之间家庭观念的差异。在传统的大家族观念中,姑姨叔舅过问年青一代的学习和生活状况是理所应当的。而年青一代持有的家庭观念是由夫、妻、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模式,“七大姑八大姨”是根本沾不上边的无关人等。那些只有在过年才回家的年轻人无法与这些长时期见不着面的亲戚产生同处一个“家”的认同,也就找不到与他们团聚的意义,更无法把他们的嘘寒问暖和打听近况视为真正的“关心”。这本是两代人之间虽无奈但属自然的“代沟”。另一方面,这也是年轻人用已经习惯的都市生活方式对故乡的生活方式所进行的否定。在新一代的价值体系中存在着一种理想生活样板:进新兴企业工作而非考公务员,喝外国牛奶、吃进口维生素片而非家乡的传统饮食,做“丁克”而非生“二胎”,年底出国旅游而非回家过年……这本是并无高下之分的两种选择,却被贴上“现代”与“传统”、“世界化”与“地方性”的标签,进而转化为一种“先进”与“落后”的价值等级。对年青一代而言,“过年回家”就是从无限与世界接轨的大都市回到落后于现代世界的地方小城。亲戚的不断追问自然有讨厌之处,却也提供了大都市生活方式之外的另一种对照视角,或许其中不无道理。然而,在年轻人全盘接受了这一套“现代”价值体系之后,他们回家时遭遇的所有不适就再也无法导向自我反省,而是被轻易地归纳进“先进”与“落后”的理解框架。当两代人的“代沟”被转化为价值上的高下,代与代之间的理解就变得更为不可能。说到底,这依然是传统的中国“大地”失去了现代性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重视出身,即使通过科举进入京城或在他处做官,也始终保有地方的文化传统。而如今进入大都市的年轻人,无论来自何方,几乎都接受着同一种以现代化和都市化为导向的文化教育。一旦谈及传统、家族,就有被视为小地方习气脱落未尽的危险。我们无法再指望从小城走向大都市的人们能为自己出身的社群代言,“小城”也就无法在流行文化中获得正面的形象。这样看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对于“七大姑八大姨”的吐槽和学院知识分子的返乡笔记,其实是同一种文化心理的衍生品。前者是抱怨小城比大都市闭塞保守的“乡怨”,后者是感叹农村美好人伦关系被金钱社会玷污的“乡愁”。它们都无法在当下中国找到除“城市”之外的另一种正面生活价值的存在。
充满“乡怨”的知识青年凭借着在大都市学来的中产阶层价值观反击父辈,但他们自己尚未成为真正的中产阶层,否则就不会在亲戚的提问前无地自容。他们的真正身份,是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都市新穷人”。这群年轻人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活跃于新兴媒体,操纵着当下的文化话语。他们大多怀抱着上升的梦想,却陷落于消费社会创造出的过多欲望,臣服于虚拟经济和金融资本支配下水涨船高的中国房市。借用汪晖的话说:“他们是不满的源泉,却未能展开新的政治想象;他们在消费不足中幻灭,却不断地再生产着与消费社会相互匹配的行动逻辑。”同为都市知识青年的文化产品,“乡怨”和“乡愁”构成了同一种社会进程的一体二面。“乡怨”折射出他们的不满,而“乡愁”则映照出对新价值寻而不得的虚空。
“乡愁”也好,“乡怨”也好,都诞生于“返乡”这一行为之中。正如梁鸿在《中国在梁庄》的前言中所表述的,“返乡”这个动作诞生自她对于学院内“虚构的生活”产生怀疑,进而希望在乡村寻找一种“真正的生活”。这是一种卢梭式的动机。卢梭基于对现代人生活的不满,热情歌颂前现代的野蛮人,其目的正在于批判现代生活的败坏。然而,这种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野蛮人并非真实存在的,而是卢梭有意制造的与现代社会相对立的虚构物。梁鸿希望在梁庄找到的“真正的生活”,也未尝不是一种虚构。所谓“真正的生活”,不过是作者不满于学院内和都市中的生活所虚构出来的对立面——一个理想世界。这种理想中的、虚构出来的“真正的生活”终于在现实的梁庄中落空,“乡愁”于是诞生,虚构也就成了“非虚构”。同样,年轻人在春节返乡前爆发的“乡怨”,也因他们将乡土生活放置在城市生活的对立面,并对后者所代表的现代价值观深信不疑。对于“乡愁”和“乡怨”的书写者而言,乡村始终在与城市的对照中显现,因而无法避免地沦为城市及其所象征着的“现代”的异类。这样的乡村就只能呈现为一片沉沦的大地。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上升的大地:中国乡土的现代性想象》第四章,内容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