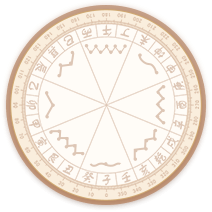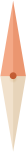原题
马克思帮助我离开黑龙江
作者:庄稼婴
插队呼玛
1969年的秋天,我们中学成了“集体插队”的试点,69届十个班的学生一锅端,统统去黑龙江呼玛县插队。呼玛县曾经是中国最北的县,直到1981年,漠河县从呼玛县里划了出来,呼玛才丢了最北县的称号。
我们被分配到呼玛县金山公社的四个生产大队,即四个较大的村子,往每个村扔进去两三个班,我们的命运就此被决定了。
那年11月,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嘻嘻哈哈,哭哭啼啼,木知木觉,从上海登上了北去的列车,经过五天四夜,来到了白雪皑皑的黑龙江边。

我们出发那天的情形
金山沧桑
我去的村子叫金山,在黑龙江边,对岸有个苏军兵营,名副其实的“反修”第一线,不过金山从未成为过战场。
淘金辉煌时期,也就是知青到来前的半个世纪,这里曾被称为金山镇。“镇”留下的遗容是一条大路,从村口直通江边,据说在鼎盛时期,路边有酒馆、杂货铺、青楼、铁匠铺等。等我们到了村里,路边除了农舍,只剩下破旧的铁匠铺,叮叮当当,修理农具马具。当然,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有新气象,村口有了个供销社。
淘金浪潮过去后,淘到金子的人跑了,剩下的是没淘到金子的失意冒险家、人老珠黄的妓女、一贫如洗的苦力、还有从俄国流亡来的“老毛子”。亏得又从关内陆续来了些闯关东的汉子,这繁华过一时的小镇成了个80多户人家的村落,男女老少加在一起,300来号人。
1969-1970年间,从上海来了三批知青,共200多人。第一批是老三届的高中初中生,后两批加在一起有150人左右,均为69届初中生。他们上中学的时候,除了小红书,什么都没学,实质上是小学毕业生,我也是其中一员。
自从来了知青,金山就失去了前几十年的宁静和秩序,知青食堂建在大路旁,整天有活蹦乱跳的少男少女来来往往。村里的猪狗鸡散养,满村乱窜,初时,女孩见到猪啊狗啊迎面跑来,吓得左右躲闪,哇哇大叫,男孩则乐得紧追不舍,有个上海来的小民兵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追猪,这才发现猪跑得比民兵快。大路上就这么吵吵闹闹的,搞得周边人家鸡飞狗跳。
安心务农
因为是集体插队,我的插队,跟一般人的插队不同,整日扎在知青堆里,跟当地农民的接触非常有限。
我住的女知青宿舍,一座木格楞房子,进门的小门厅里放农具,两边两扇门通往两个宽敞的房间,房间内各有三条炕和一堵火墙,四五个人睡一铺炕。
到金山的第一天晚上,进了宿舍,火墙火炕烧得热乎乎的,屋子里点着明亮的电灯,地上是宽宽的木板地,令我等喜出望外。
火墙头上有两个灶眼,两个大水壶成天咕嘟咕嘟冒着水蒸气,热水供应充足。女知青爱干净,大水缸里永远灌满了清水,收工回来你洗脸我洗衣,到了晚上用热水泡脚。上海人非常惧怕的东北“老白虱”,跟我们无缘。
知青多,不单独做饭,一日三餐去知青食堂吃。饭菜千篇一律,早饭大碴子粥加馒头,给一根萝卜条,萝卜条非常咸,带点臭味;午饭晚饭大白菜土豆汤,汤很薄,一碗盐水,零星几片土豆和白菜,馒头放了碱,黄黄的,有时放多了,微微有点涩。毕竟是面粉,不是杂粮,而且绝对够吃,男生曾经比赛饭量,冠军是“大胖”,一顿吃了三斤四两馒头。对我来说,不用自己挑水打柴,生火做饭,已心满意足。
插队的头一两年,什么都新鲜,日子过得挺有滋味。我们学会了去井里打水,学会了跟着扁担颤动的节奏,挑起沉重的担子行走如飞,学会了抡起大斧子,把粗大的树墩劈成四爿,学会了生火烧炕,学会了去江里钓鱼,上山采木耳和野生蓝莓,最重要的是学会了播种、铲地、割黄豆、捆麦和其他的农活。在农民的指导下,农活越干越顺手了。
那时候,大家都以为要在金山生活一辈子,既然如此,该干活干活,该吃饭吃饭,该找乐找乐。早上跟同学一起出工、收工后聊天、串门、唱歌、去外边溜达,偶尔还装装样子,大家一起学毛选。

为家人拍摄的照片:美丽的黑龙江和幸福的知青
对多数人来说,安心务农不是出于扎根农村的革命激情,而是随遇而安。上海人相当实惠,如果有选择,能留在上海,谁脑子有病要来农村?不过既然来了,就好好过吧。
由于我们中学地处原来的法租界,周围小洋房老公寓多,69届就近入学,学生的家庭背景不那么无产阶级化。宿舍里不少同学出身于知识分子、高级职员、资本家,他们大多中规中矩,温和内敛。当然还有不少黑帮子女,被整得头疼,逃到农村来避难,对革命也不那么热心。因此,在我的周围还真找不出一个热血沸腾非闹着要下乡的。虽然有人相对积极一些,有人消极一些,但同学间相当包容,同是天涯沦落人嘛。
村里自己发电,晚上十点电机房关机,全村熄灯睡觉。刚下乡的时候,十五六岁的少女,有说不完的废话,并排躺在炕上说说笑笑。睡得太晚了,早上根本醒不来,民兵女排长,一个当地青年,被委以“闹钟”的重任,每天一大早来我们宿舍打门,大声呼叫:起床啦,干活啦。一两个月后,成天干活把我们累得贼死,熬夜聊天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跟老农民一样,也早睡早起了。
就这样,我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金山确实是块宝地,自然资源丰富。勤快的农民下河捞鱼,上山采榛子木耳黄花菜,套个野兔狍子,养猪养鸡,种点自留地,再去供销社打几两白干,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知青是一人饱全家不饿,队里粮食柴火富足,不愁没饭吃没柴烧。哪怕我这样一天只挣八个工分的,到了年终分配,扣除口粮柴火,还能分到100多元现金,回上海探亲的来回车票50元左右,完全负担得起。
偶遇马克思
平静的心态并没有维持太久,不知从哪天开始,周围的一些同伴陆续离开了。大家如梦初醒,原来我们不必在这里呆一辈子。
金山公社约有1000名知青,偶尔县办厂来招几名工人,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想通过官方渠道上调,几乎是白日做梦。知青家长这会儿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神通广大的走得最早,往往是去参军;后来有的转到南方农村,那里知青少,上调机会多;有的直接进外地工矿;有的嫁给有城镇户口的;有的病退回了上海。同伴的一个个离去,给我们的内心带来一次次冲击。
表面上似乎一切如旧,大家一起上工收工,心却散了,每个人有了自己的秘密,开始考虑个人的前途。离开农村的道路曲曲折折,布满荆棘,不少人四处碰壁,遍体鳞伤,却依旧在原地踏步。我们是越想内心越沉闷,连脚步都沉重了起来,大路边的狗,也不怕我们了,自在地躺在家门口,懒得抬头看我们一眼。
我一向喜欢看书,一天在同伴的炕沿上发现一本书,《马克思和燕妮的故事》,情不自禁翻开。书中提到,家里闹财政危机的时候,马克思常闷头做数学题,以此逃避烦恼。这本书里别的说了什么,全忘了,只记得这段。
那几年,我家境遇不太好,要离开农村,谈何容易?首先是无亲可投,因为亲戚都集中在北京上海,投也白投,户口进不了那两个城市。其次是靠友无门,父母一辈子在上海工作,社会关系基本都在这个城市。在母亲的动员下,众亲戚开始积极“结识”外地人,而且特别是南方乡镇的,希冀为我找条出路。
我的情绪起起伏伏,在期望和失望之间游走,马克思的故事,醍醐灌顶,给我指明了一条路。 每天晚上,同伴在身边聊天唱歌打毛线玩牌,我趴在炕沿上做数学题。数学非常奇妙,钻进去乐趣无穷。晚上十点熄灯了,我在煤油灯下继续解题。就这样,不知不觉学完了初一的代数,还让我的“勤学”在村里广为人知。
饥渴岁月的知识飨宴
我的勤学被远在北京搞科研的舅舅知道了,正巧他听说1973年大学招生要考试,催我冬闲季节去北京温课备考。
1972年的冬天,我到了北京的小姨家。小姨夫妇五十年代末大学毕业后,双双留校任教。两个书呆子,出身不好,不闻政治,幸亏是年轻教师,够不上学术权威,顺理成章成了逍遥派。小姨那会儿在校办厂做无用功,姨夫则被派去为工农兵学员编写教材。他俩供职的北师大院系在原辅仁大学的校舍,教工宿舍在附近的胡同里。
小姨家很小,里屋只放得下一张大床,外屋硬塞进两张小床,收了两名“寄宿备考生”——插队的远房表姐和我。表姐是北师大女附中的,23岁了,全家上下为她即将成为大龄女而担忧,听说大学招生要考试,她决定回京温课。
我和表姐朝夕相处了五个多月,共享一张小方桌看书写字。我们的房间也是小姨家的厨房、饭厅和杂物间,煤炉、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清扫工具、过季衣物,满满当当,到处都是。原来睡在外屋的表弟,被我俩鹊巢鸠占,不得已每天借宿邻居家。
我俩从早到晚埋头温课,学习进展迅速,不久我学完了初中数学,课本里的习题都被我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小姨和舅舅还塞给我一些习题册,专供我练习。表姐是重点中学的高中生,我的作业常由她检查,一箭双雕,她借此复习了初中数学。
有一天,小姨拎着沉重的蓝布包回家来,难掩兴奋,她遇到了交情很深的老图书管理员,从图书馆弄出来一包“毒草”。更可喜的是,看完了还可以去换。
我和表姐迷上了《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巴黎圣母院》《基督山恩仇记》《红与黑》《罪与罚》《契柯夫短篇小说集》等名作,一放下数学书,就抱起小说,废寝忘食,看得昏天黑地。
真希望如此美好的日子能继续下去,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1973年初夏,我带着一脑子的数学公式和古老动人的外国故事,回到了乡下。黑龙江上的冰雪融化了,清澈的河水徐徐流淌,冻得坚硬的大地解冻了,一地泥泞,每迈一步都很费力,鞋上裤腿上沾满了厚重的湿泥。日照越来越长,树枝抽出了新芽,呼玛100天的无霜期到了,我们又该出发去“地营子”了。
有幸陪考
金山风水好,一面临江,背靠山岭,满山密密的小树林,周围耕地不多。在粮食为纲的时代,只能到离村子较远的地方去开垦农田。呼玛县人少地多,在平坦的荒原上,拖拉机隆隆往前开,遇到树林山丘折回来,犁过的黑色处女地就成了生产队的农田。
我们队的农田离村子四五十里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在农田附近,搭了几间简陋的木头房,成了金山的地营子。耕种季节,壮劳力住在地营子,秋天收完了庄稼,大队人马再回村过冬。
六月中旬,机器播种的小麦大豆出了苗,野草也开始疯长,我们带着行李和农具,坐了一天的马车去地营子,路不太好走,很长一段是树林中的小道,两米左右宽,刚容得下一辆马车行驶,我们坐在车上,不时低头躲闪左右低矮的树枝,不停拍打团团袭来的蚊子小咬,时而车轮陷进泥坑,我们跳下车去推。
北方的夏天,日长且明亮,早晨四点多日出,晚上九点多日落,我们每天铲地(锄草松土)十多个小时。有的地一陇有四五里长,一天只能锄一个来回。
清早比较凉快,但是每个人的周围蚊子小咬黑乎乎的一片。我们随意拍打吸饱了血的蚊虫,脸上汗水血水尘土混在一起,成了大花脸。正午烈日当空,脸晒得通红,头发晒得焦黄,补丁叠补丁的衣服满是汗水和泥尘,口干得冒烟,饿得“肚贴背“。偶尔铲地到了河边,众人把锄头一扔,争先恐后跳进河里,让清凉的河水冲去炎热和汗臭。水淋淋的衣裤贴在身上,我们滴滴答答上岸来,继续铲地,湿衣服沾上了泥土,在阳光的暴晒下,成了硬硬的一层壳。
七月,上海的大学到呼玛招生来了,要招30多名,而且只招上海知青。这是自我们下乡来,招的最多的一年,令人振奋。可转念细想,呼玛县有8000多名知青,我的希望非常渺茫——出身不好、非团员、69届初中、不善交际、不能干,唯一占优势的是温习过初中数学。
我们村分到一个大学名额,可以推荐四个人去参加考试。当时的政策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那年还加了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村民一听是招上海知青回上海,懒得参与。贫下中农推荐变成了由知青自己推荐,再由贫下中农(村支部)审查批准。
知青分男女两组开会。因为要文化考试,大家觉得随便找个人去,会白白浪费一个名额,不如找个能考试的去。我们村有四个高中生,都是男的,还有些老初中生是党团员。男组推荐了三名男生后,决定再推荐个女的,有人提议让我去,不至于交白卷。受到推荐的男生私下议论,让我陪他们去考考也无妨。与此同时,女生组也推荐了我。名单到了党支书手上,既然两组都推荐了我,支书立马批准了。
老师的微笑
我这个家庭”有问题“的非团员,侥幸去县城参加了两天的文化考试,三门课:数学、语文、政治。那年门槛低,初中水平就行。我们县,从8000多名知青中,推荐了200多人参加考试,大学最后录取了37人。
考试时,初中数学记忆犹新,因此觉得考题不难,答题很快。语文考试是写一篇作文,忘了是什么题目了,小学的语文教育不错,虽然我认字有限,但能把句子写通顺,错别字也不多。政治,只要稍微注意点时事,能背出最高指示,都可以及格。
第二天考完去交卷,监考老师看了看考卷上的名字,脸上马上绽放出热情的微笑。我暗想,这老师真和善。从上海来招生的两位男老师也平易近人,特别爱跟知青谈话。遇到他俩,我刚报了姓名,他们对视了一下,笑容满面,问长问短。当时我并未放在心上,以为是他乡遇老乡,格外亲切。
八月中收到了家信。母亲在信中祝贺我考得不错,据说数学全县第二,语文、政治名列前茅。读罢,颇为吃惊,远在上海的母亲怎么会知道考试的结果?再往下读,传闻来自我家居住的机关宿舍。
由于呼玛县的上海知青太多,不少上海机关干部被下放到呼玛,帮助当地管理知青。我们宿舍楼里,除了三十多名同龄人去呼玛插队,还有好几位长辈也被下放到呼玛。估计长辈接触的都是当地领导,消息灵通,写家信时随意一笔,我的考场表现顿时传遍了邻里之间。
读完了家信,我有了点信心,如果根据文化考试的结果,择优录取,我应该有希望。
当头一棒
考完试,回地营子干活,开始了心神不宁的等待。录取迟迟没有消息,却等来了张铁生的信。他在信里指责了那些温课的知青。虽然我是在农闲那几个月温的课,并没有影响生产,但是被张铁生这么一搅,像是犯了重大错误,考得好更成了“不安心农村”的铁证。
张铁生的信拖延了审查过程。一天,有人告诉我,队里有“群众”写匿名信去公社告了我一状,说我为了逃离农村,在家补了半年多的课,还请了三名大学教授辅导,是修正主义的苗子。那个年代,打小报告互相揭发成风,面对无名无姓的“群众”,我无能为力。公社也没有人来调查,我连辩白的机会都没有。那段时候,心情特别压抑,上大学的梦渐行渐远。
“白卷英雄”闹得大家都不敢读书了,我把数学书和英汉小词典藏起来,不做数学题,也不背英文单词了,跟周围的人一样,收工后,拿出一副扑克牌,通关算命。人人都盼望“小六子”出现,因为“六”代表“路”,暗示人生有路,生活还有希望。奇怪的是,那几个星期,小六子紧追不舍,同伴们羡慕不已,一致说我路路通,一定能上大学。
转眼九月到了,收割季节来了。地营子没有电话,也不通邮,每个星期,有马车去金山拉一些给养过来,顺便给我们捎来积压在金山的家信。考试后,每周我都翘首盼望马车的归来,希望马老板能带来只字片语,哪怕是传言谣言也行,可是入学的事音信杳无。
我在地里捆麦,手被干枯的麦秸划出道道血痕,金黄色的麦捆,一列列整齐地排在收割完的麦地里。马车来运麦了,我们用长长尖尖的草叉挑起沉重的麦捆,奋力甩上马车,越甩越高,两三个月辛苦换来的硕果,实实在在的,就在眼前,可大学梦却那么虚幻。已经九月了,大学都开学了,我也该从梦中醒来了。
黑夜过去是黎明
一天早上,我推门出去,睡在我旁边的美娟正从外面进来,笑容满面:“你被录取了。”我以为她在开玩笑,她带着笑意的大眼睛看住了我:“真的,不骗你。小头从金山给你送信来了。”
小头是男生,高高瘦瘦,瘦削的脸,就此得到“小头”的绰号。我们队知青多,为了便于管理,村里的党支部不直接找知青,而是通过知青中的党员和团支部七八个团支委来组织安排我们出工,小头是团支委之一。他是67届或68届的老初中,我跟他不熟,但他是我们村“风头最健”的爷们之一,扛着枪巡逻,甩着响鞭赶马车,驾驶拖拉机或康拜因。
我到了伙房,小头不在,炊事员老何叔告诉我,昨天晚上公社的团委书记到金山村去送录取通知书,我被大学,好友卓琪被中专录取了。因我俩都在地营子,小头连夜赶着马车把团委书记送过来。
想到他们在黑夜中,穿过树林,越过山丘,紧赶慢赶的,我甚是感动,要去当面致谢。可是老何叔说小头颠簸了一夜,睡觉去了。
黑龙江天寒地冻,江上不结冰的三四个月里,有小江轮行驶于呼玛县城和漠河之间。听说两三天后,有一艘江轮将经过金山村去县城,我跟卓琪决定马上回金山收拾行装,然后从村里搭乘江轮去县城的知青办,办完手续后,可以从县城坐长途汽车直奔火车站。即便这样,等我抵达上海,也要九月中了。
时间紧迫,我和卓琪说走就走,先步行八九里山路,去公路旁边的三间房生产队,那里每天有一班长途车经过,如果错过了,可以想法搭卡车到十八里岗林场,再从林场走十八里山路回金山。
美娟催我快走,她会帮我把被褥捆起来,让马车第二天捎回金山。我把看过的书、剩下的日用品、缝补过的劳动衣服,分送给地营子的姐妹,背着个帆布书包就上路了。她们送我俩到路口,叮嘱我们别忘了写信。走出很远,回头再看,还有人在向我们挥手。
情深意长
在回金山的路上,不期遇到了公社的党委书记老王,当地老乡叫他“王乡长”。王乡长在金山工作多年,关爱百姓,平易近人,深得人心。从他那儿得知,我之所以能去上大学,还亏得一位上海干部仗义执言。
我们公社有二三十位来自徐汇区的下放干部,知青与上海干部的关系相当密切,有事我们常找他们倾诉,他们总是想方设法替我们排难解忧。
冬天,下放干部跟我们一样,去上海过冬,开春再回黑龙江来。有两年,我是跟公社的上海干部结伴回黑龙江的,一路上跟着他们走走停停,访问了华北和东北的不少城市,旅行使我们熟悉起来。有人开玩笑说,上海干部慢慢地从五七干部(五个月上海,七个月黑龙江)变成五一六干部了(五个月上海,一个月旅行,六个月黑龙江)。
收到检举我的匿名信后,王乡长找上海干部了解情况,原徐汇区组织部长刘阿姨竭力保护我。她对王乡长说,年轻人趁着农闲温课学习,不浪费光阴,说明她好学向上,明明是好事,怎么变坏事了?王乡长非常赞同,遂对检举不予处理。

王乡长、卓琪和我的分别留影
呼玛县的知青,二十多年前曾出版了一本厚达七八百页的书《呼玛知青风云录》。在那本书里,卓琪写道:
在我和稼婴离开金山前,王乡长带着我们去五里岗挖了几棵松树,约1.5米高,手把手教我们种在金山的大路边。很多年以后,从中央电视台 “黄金之路”节目中,看到了金山依旧,看到了知青食堂已萧条,看到了王乡长带着我和稼婴种的松树仍然挺立在路边,不禁泪流满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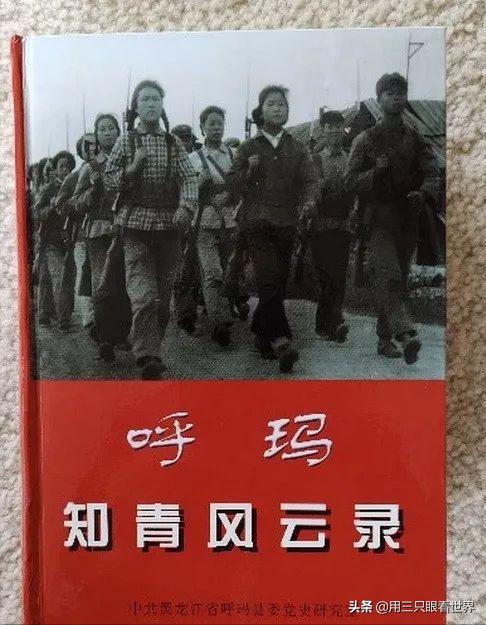
1973年9月10日,中秋节前夕,我离开了金山。中秋节的缘故,队里杀了猪,知青食堂包了肉包子。住在隔壁房间的炊事员翠芳,往我的书包里塞了几个肉包子和白煮蛋,让我路上吃。
江轮是中午时分到达金山的。一位男生赶着牛车,把我和卓琪的行李拉到江边,全宿舍的女生前后左右伴随着我们,沿着走过几千次的村中大路,来到江边。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几乎所有在村里的知青,不分男女,都来了。不少男生,虽然跟他们共同插队了四年,因为沿用中学分男女生的习惯,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时隔五十多年了,依旧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江轮离岸的时候,女生在拼命挥手,男生定定地站着,目送江轮渐渐远去。我的鼻子酸了,内心五味陈杂,在黑龙江的四年,日夜盼望离开这里,真的走了,这山、这水、这村、这些跟我朝夕相处、亲如家人的姐妹,竟令我如此不舍。
也就是在那一刻,我悟到了谦卑和感恩。岸上的兄弟姐妹中,比我能干比我聪明的多了去了,我无非是运气好,天时地利人和。尤其是在适当的时机遇到了借数学题消愁的马克思。
二十多年前回上海探亲,正逢插友在酒楼聚会,依旧沿用插队时的老规矩,男女生分桌坐。在一桌老汉中,找到了小头,上前敬酒,送上迟到了二三十年的感谢,小头却一脸茫然。我不得不把他黑夜驾马车四五十里的感人故事重述一遍。他真诚地看着我,淡淡地说:“真的?我全忘了。”
作者:庄稼婴,生于上海,曾在黑龙江插队,自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任教于上海外贸学院。1982年移居美国,获加州大学博士,现为大学教授,迄今在中美高校教学、管理四十五年。
来源: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