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伶文
地里一片金黄,稻穗沉下去,叶尖微卷。要是头二年,壁上的镰刀早就涩涩作响,取下来重新打磨了;稻篰谷箩畚斗该补的补,该换的换,也收拾一新;小道大道机耕路早已填平夯实。一切仿佛嘉宾云集,焕然一新地等待一场盛大的喜宴。这一年,喜庆依在,但并未出现隆重忙碌的前奏,仿佛迎接的新娘已经是再婚的女人。
这天早上,夜间的雨珠在新娘金黄的卷发上还没散尽,一个赤头光臂却长裤着地的男孩提着鱼竿出了大院。大院“C”字形,竹丛包围,竹丛外环着水塘,正南面留有一个出口,里面住着十六七户人家。男孩趿着黄色厚跟的拖鞋,这是最新的款式,穿上能见高,有了半大个人的感觉。那条灰蓝色的军裤,一看就是大人穿旧了给的,裤管空荡荡,下边挽了两圈还见长。他急步上了机耕路,不回头,不顾盼,匆匆的仿佛是逃脱大院里谁的眼睛。当他离开竹丛的视线一远,就颠臀晃脑,三脚两跳,哼起不成调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这般乐滋滋,大概是去鱼缸里捞鱼。
他没提鱼篓,也没鱼篓,以后也没。他从没想过要一个鱼篓,从没跟院里的巧手篾匠阿喜提过。阿喜为左邻右舍编过草篮稻篰菜筐饭箩子,也给人编过鱼篓子。他说鱼篓太惹眼,如果没钓到鱼,回来时提着没下水的空篓在人前晃,太丢人。他又不喜欢把篓子浸湿来忽悠,更不愿提着个小水桶咿啊咿啊地晃荡。他只在裤兜里藏了一个二尺来长的网袋,这是三年前,母亲用墨绿色渔网线织的。之前,母亲织过一个,有一尺长,拉开一尺来宽,用来织毛衣时提毛线球的,偶尔也用来揉洗芋头、土豆,或上街提点什么的。让他用来装鱼,他说袋子太小装不了几条鱼,又嫌弃单股线不牢固。母亲说:“你爸钓鱼也拿这个。你这小鬼,摆什么谱?”没办法,有总比没有好,也比竹串子好,他就赌气用着。一个月不到,一天,他嘻嘻哈哈地提着三条猫鱼儿从河边回来,跟母亲说跑了两条。母亲一看袋子,果然有两格子的线磨断了。母亲哪知道这是他平时洗土豆时故意往石棱上狠磨的结果。母亲只好为他再织一个,用了粗粗的双股线,袋子还大得拉开口来装得下一个大南瓜,这下他满意了。网袋团起来拳头般大小,往兜里一塞,不张扬;有鱼的时候晃到人前,鱼鳞亮闪闪能扎眼,不像竹篓子,走近了也分不清里面有没有鱼。
他刚钓鱼的头一年,跟别人学做了一个竹串子。那是最简单的串鱼工具:一根尺把长的渔网线,两头各系一根削得一头尖一头圆的细竹条,竹条比筷子略短。出门时,两根竹条一合,线一卷,兜里一塞,很隐蔽。钓到鱼后,用其中一根尖的一端从鱼鳃穿过鱼嘴,再不管哪根竹条一横,鱼就挂上了,甩到水里也跑不掉。另一根竹条往岸边一插,就安稳了。可这串法太残忍,把鱼鳃鱼脸撕出血来,晃到家时,鱼早死翘翘,想救也救不活了。
他自创过救鱼的方式,但对这种被虐杀的鱼不起作用。他能救的是那种因缺氧而晕厥的鱼,一般发生在天热时,养在水盆里的鱼直仰肚皮,背鳍褪色,胸鳍尾鳍不闪不动,嘴唇翕合艰难,鳃盖不见张开。他的呼吸仿佛也替鱼艰难起来,于是给鱼换上凉水,按住鱼的下鳄及胸鳍处朝鳃方向均匀有力地挤压,仿佛给人做心肺复苏。看着鱼嘴在挤压下机械地一张一合,他会像个急救医生一样时而焦急,时又欣慰。几次反复后,放手看看,果然,鱼慢慢能自主呼吸了,及至鳃盖鼓动,他才罢手。随后,他得意地看着被自己救活的鱼,十分快乐地欣赏着它们的自由摆动。鱼也努力吐出一个个圆圈来感谢他的救命之恩。然而,真能活过眼前的鱼也是凤毛麟角,大多只给他一个回光返照罢了。
这天,阳光比昨天亮,稻子比昨天黄。要是去年,这孩子也有烦恼了,因为夏收夏种的盛宴马上开始,他得跟着父亲下田,割稻、打稻、踩稻茬、挑稻秆,一样也漏不掉,再磨人的就是每隔一段地得拖打稻机。每当打完三五米地的两堆稻,那笨重的铁疙瘩就在水田里陷得半膝盖深,父子俩怎么用劲都拉不出来。如果不用机器,用脚踏的,踩完两堆稻子,人也弓成虾狗弹了。烈日下,那苦那累,半天他就受够了。生产队时,父亲一直做大队会计兼代课教师,还是赤脚医生,从没经受过水田里这等苦力。在儿子的记忆里,父亲就是邻居眼中的“先生”,向来清瘦,力薄多病。自每家分到水田后,父亲多少也得亲自下地,有时还带着母亲。头两年农忙,村里有劳力的青壮年都在家,父亲花钱讨帮工也容易。这一年体壮力足的外出多了,每家自个人手也不够,出钱也没人帮了,出太高的钱,一季就是白种。后来,村里就发生这样的事。有一季夏收,曹老七从外省回来见台风就在眼前,而地里只剩他家的稻子,那稻子稀得跟三毛的头发似的,讨人割只会赔本,下一季又等着插,他干脆一把火烧了。
去年夏收,父亲只好带上全家下田干活。当父亲咬牙切齿,忍着一身疼痛,把谷担挑到谷场,或父母一起扛谷箩到谷场后,母亲与姐姐就得晒谷子,到中午,还得挤出时间做饭。所以,在田里打稻,多半是父子俩。喘息之间,父亲会自责自叹:“人家下地干活,孩子跟在后面就是拔猪尾巴,你不行,你爸没力气,看你也小气薄力的,吃不了苦。”这孩子又比谁家的孩子都懒,嘴皮子薄,话特别多。父亲有一回恼他,说他贪吃懒做嘴唠嘈。这烈日下,父亲倒是得个好机会提醒他要好好读书,读好书考上国家户口,才不受耕作之若。一个还读小学的孩子,每天泥里水里疯玩,哪会在意父亲的苦口婆心。即使这白日里累得精疲力尽,晚上趴着床也睡死了,过了农忙早就忘了农耕的苦。所以,大人的话是耳边一阵风,上学依旧“鞋紧袜不紧”地上着。
这年夏季,他不在意农事辛劳了,看到稻谷金黄,既不再有前些年饥饿时那白花花香喷喷的期盼,也不再一把泪一把汗,仿佛那只是一串串一堆堆与他无关的杂物,无关他的忧喜。因为他家的二亩半水田暂时转让给了别人,父母带着十五岁的姐姐,二月里就去了海南补鞋。
别看父母没在身边,这孩子独个儿生活了近半年,竟然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他还得照顾鳏居的爷爷,爷爷的饭四家叔伯之间轮流值,一年里每家轮到三个月,轮到他家值饭时,他也没给爷爷落下一顿。他的生活过得井然有序,跟院子里其他有父母在边的孩子没两样。父母在边的孩子就像母亲说的老母鸡翅膀下的小鸡黄,而这时,他要独挡一面,没想到,他做到了。左邻右舍的阿嫂阿婶阿姆阿婆都夸他,说他比父母在家时还懂事,如同变了一个人,像半个大人了。
有一回,白胡子老爷爷揣着他送来的饭菜,问他:“你爸爸妈妈在家时,我都没见过你这么好。他们不在家,你倒这么懂事,什么都会做。是什么道理呢?”
“爷爷,我不能告诉你。”他乐哈哈地笑,“我告诉你,你又会骂我不听话。”随后转身,又突然想起,回头对爷爷补充了一句:“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嘛!”
“嗯,老七家的那个猢狲王就没你好了,父母不在家,那猢狲王不但不给他奶奶饭吃,还用苕帚打她,真是作孽啊天杀的!”爷爷对着一碗白米饭,和一大碗炒熟的茶豆自语着,那茶豆上放了两条清蒸的鲫鱼。
多年后,他得出一个结论,那是他的骨子里,有一种奇怪的逻辑:有人管,就不听,偏偏不学好。没人管,要好好对自己。这样,就说明他的优秀不是管教出来的,而是自己把自己教育出来的,是自我觉悟而成。如果自己管不了自己,这个人就毁了。自己管出来的,才是真正的优秀。这就是他性格中的一种倔和独立吧,有个算命先生就曾说他,看他坚毅的嘴角就知。这种倔强多年以后,还在他的骨子里蔓延,发酵。
父母与姐姐刚出去的几天,夜里,他到大伯家睡,睡也不踏实,总想着父母会突然回来。白天上课,他也没心,一放学,飞奔回家,院里、屋里、菜园里、河埠头,一声不吭到处找,总以为父母在家。几天后,父母从海南来信,说那边气候好,活也有,可能一年半载不回家,让他安心学习、安心生活,好好照顾自己,孝敬爷爷,听大伯的话,听院子里大人们的话……他才从整天的臆想中清醒过来,竟能很快就放下了思念,并且要求独自睡在家里,什么也不怕了。
阳光下,路面上撒着前两天从路边和水沟里割下的杂草,一蓬一蓬的牛筋草、抓地龙、空心莲子草,拖泥带水,还有稗草、牛膝、辣蓼……他几乎叫得出这片天底下所有杂草的名。他每天与草打交道,大人们告诉过他,几乎经耳不失,过目不忘。除了上学,他不是割嫩草烧枯草,摔跤打仗,就是钓鱼捉蛙,拉绳斗草,早晚被草汁花液染得一手绿一手青,一脸紫一脸赭。更因前些日子里,他翻看了一本从抽屉里挖出的《浙江民间常用草药》,图文对照,可把他乐的。
几年前跟姐姐打猪草,总是很难把草篮填满,所有的田埂荒地干净得像大院里的道地。苜蓿地里有一片片刚露头的油草(千金子),但小孩们不敢靠近,更不敢插足,那是生产队里的苜蓿地,瓜田李下,让大人看见挨骂。河塘深沟里有一些节节菜、牛毛毡、鸭跖草,孩子们也不敢去采,怕翻个跟头丢了命。他们只能在麦地和油菜地的边缘,拖着能装下自个人儿的草篮草篰,寻到三星两点的田荠,半躲半闪的马兰,纤细得可怜的奶浆草,和豆瓣一样的小青艾,如同在牛耳孔里剪茸毛一样。而打猪草的孩子大人随处可见,所以往往到日落,打的猪草也盖不严草篰的底。回家路上,只好砍一些又硬又长的猪不理杂草垫在下面,比如白茅、牛膝、羊蹄。年纪大,胆子大的孩子在回家路上往往独自寻去,然后从地里偷几把苜蓿,甚至把麦苗埋在篰底。
可这三五年一过,田头地角到处是草,什么都有,什么都茂盛,油油绿绿,水水嫩嫩,仿佛一哄而上要长成一片森林,而打猪草的人,满地满野找不到一二个了。他琢磨其中的原因:是有手脚有门路的人都出去了,还带走了不上学的儿女;是养猪的少了,又是家家户户粮食多了,便宜到让人不知珍惜,也不为猪食发愁了。

就在他一路辨识这些被弃在路面上等着暴晒的杂草,想着书上说的药用,朝着早就计划的蛤蟆塘蹦去时,不远处,扛着锄走在田埂上看稻子的老根头朝他喊:“小文子,你又钓鱼啦,小心鱼怪鬼跟着你。”
按村里辈分,小文子得叫老根头叔公,但他们并非一个大院,就生分些。若是从前,小文子一定口无遮拦,点了百子炮似的甩过去:“你娘放屁,你才鱼怪鬼跟牢。鱼怪鬼只会跟你个独眼龙,才不会跟我,我是鬼见鬼怕,妖见妖溜,阎王见了就躲的孙悟空,你是个独眼龙……”说着,然后做一个猴样,朝老根头怪笑。老根头并非独眼,只是天生左眼皂荚果般圆又大,右眼小虾般弯又细,所以小孩子背地里叫他“独眼龙”。老根头喜欢寻小孩子开心,也不会计较他们骂他。
这回儿,小文子只是歪歪大脑瓜,咧咧嘴,对着老根头哈哈哈一笑,一句话也没应。这孩子比别的孩子头大,头发没别的孩子黑;脸也没别的孩子黑——虽然他与别人一样天天在太阳下晒,不戴草帽不戴笠,怪的是,只要下过一两天雨,他的皮肤就回白回嫩了;他的眼珠子仿佛也没别的孩子黑,有点褐色,但似乎比别的孩子多了一道怪怪的亮,像有月光落在幽深的水井里。所以,在大人们的眼里,同样一堆泥孩子混在一起,就他与别的男孩不同,遗传了父亲的书生气。
避开老根头的捉弄后,他却在心里琢磨,这些年钓了多少鱼?有一千根?一万根?再不到二个月,他就上初中了,前天接到录取通知书,昨天就给父亲写了报喜的信,放到村部里等着邮递员了。父亲在家时,就教会他写信寄信了。可他只知道“一千”和“一万”的数目是不得了的多,并不能弄清若“一千”和“一万”条鱼摆在面前到底是什么场面。他只钓了五年的鱼,却是村里有名的钓鱼小能手,但用“一万”肯定是太夸大了。他想自己害了这么多鱼,这么多小命,难道以后真的会有小鱼怪鬼跟上?然而,这念头只是蜻蜓点水,一闪而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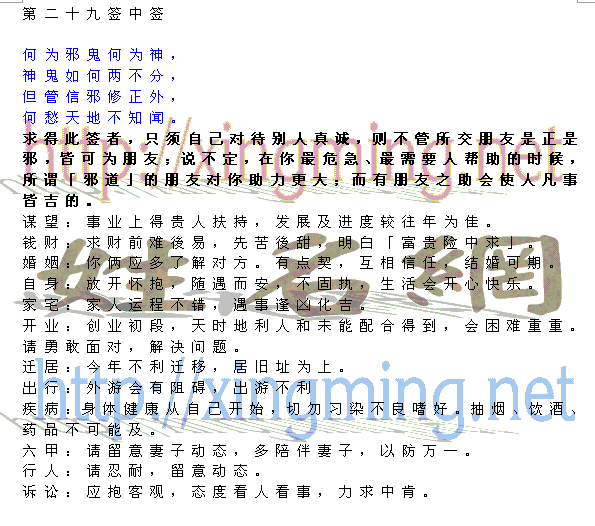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