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从4 月24日起,《中师生》公众号开始连载四川作家曹清萍老师的长篇小说《中师生》。此书在2015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全书43万。作者在书的扉页写道:献给中师生和为共和国基础教育事业献出青涩青春的人们。四川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向荣教授在该书《序言》中说:《中师生》书写了一代中师人的群像。一群二十多年前的青年男女从远处走来,为乡村教育演绎着虽然普通但却绚丽的昨日故事。

标题:冷修竹报到泸县师范前一天,做了一个梦(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曹清萍
插画作者:刘露
新月斜斜地挂在天边,柔和的月光倾斜下来,照在银色的沙滩上,照在粼粼的海浪上。天空深远,云朵缱绻,点点繁星在天边眨着眼睛,偶尔和飘过的丝丝黑云捉着迷藏。浪花轻抚着岸边,天和地都是那么透彻的蓝,没有一丝丝杂色。耳边拂过的海风轻轻柔柔,岸边的芦苇便悉悉索索起来,点点海鸥起起落落。
天,地,静谧着。
狭长的大堤延伸向大海,海水轻击着堤岸两侧的基石,引得沉睡的海鸟一个激灵,鸣叫声里箭一样跃起,成为一个点儿消失在天边。冷修竹赤足走在大堤上,任海风撩起她长长的黑发,享受着海边的静谧。不料天地一片诡秘,海风骤然而起,芦苇丛哗啦啦一片倒向岸边,乌云铺天盖地滚滚而来,海浪咆哮着翻腾着呼啸而至。她抬腿就跑,脚就像踩在棉花堆上一样,怎么样也迈不动腿。
水近了,浪来了,挽起的裤腿散落下来没入水中,水及腰,至颈,没脑,她卷入了漩涡里。表面风平浪静的漩涡将她的身子旋转着,往地心深处拼命拽。身体越来越沉,不能呼吸,不能呼喊,渐渐失去知觉。偶有一瞬间她双臂乱舞,双脚乱蹬,艰难地吐出呛入的海水,奋力呼救,声音却发不出来,被喉咙堵塞着,呛得眼泪流出也没发出一声求救信号。
身体往下沉,往下沉,眼睛睁不开了,眼前模糊不清,越来越多的水草缠绕着四肢,四肢僵硬,困乏无力。海底鱼群向她游来,凉凉的,滑滑的。突然间黑黑一大片小鱼小虾风驰电掣般奔来,将她盘旋,翻滚。她眩晕起来,一股酸水从肚脐眼儿处往上冒,眼看就要在喉咙眼儿处喷薄而出,游鱼全作鸟兽散不见了。
身体沉入海底。
海底那口垒着高高石台的井逼到她眼前,顿时她脑袋晕旋,眼珠向外凸起,不断逼近的井让她不能呼吸。井近了,井水深不可测,曛黑翻滚,从井底慢慢升起缕缕白雾,盘旋着往她的眼前蒸腾。瞬间,白雾渐散,波涛涌来帆船点点,江水送来了一块绿洲。碧绿的菜地间走来一个瘦高的男生,他左手甩着白衬衣,右手抱着一个篮球,哼着:“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哦,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菜地尽头跑上来一个红裙女孩儿,上气不接下气地叫着:“等等我,等等我……”他却自顾自地往前走。
追上,追上了,女孩儿伸出手拉着他,倚靠在他肩头,甜甜地笑着。他用力摔开她的手,怒斥着她,倒退而行,猝然倒地,四仰八叉。女孩儿大哭着扑上前,摇动着他的身子,他却如磐石纹丝不动。许久,她伸出食指到他鼻翼间,顿时惊恐万状,仓惶逃跑。
绿洲漂过来了,姑娘越跑越远,小伙子却躺在冷修竹脚边。
冷修竹想叫住那个女孩儿,口张不开;想伸出手去掐他的人中,绿洲一下子顺着江水飞逝而去,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突然间乌云滚滚,狂风大作,黄沙漫天,遮天蔽日,他成为白点随着黄沙消逝了……
“冷修竹,起床了。这个懒虫,快点起来了!”妈妈的叫声从厨房传出来,惊魂未定的冷修竹从床上一跃而起。心咚咚咚跳过不停,眼球鼓胀,想睁开却酸涩无比。双手不住地颤抖,才明白又是双手放在胸前做起了恶梦。
燃烧的木柴味儿和着猪油炒藤藤菜的烟味进入了冷修竹的房间,呛得她直打喷嚏。本想快点把衣服穿好,可刚拉过枕头旁边的衣服,就感觉浑身无力。这是怎么啦?今天可是报到的日子,好日子,鲤鱼跳龙门了。可是刚才的梦不是好梦啊!虽然有梦死得生的说法,这个男生是谁,自己不认识,干嘛在自己即将踏上人生新的旅途之前出现,过两天得好好翻翻那本小册子《周公解梦》,破解破解其中的谜数。
“快点啊!咋过还不起床?”妈妈的叫声比刚才提高了八度。冷修竹知道这是火山爆发的前奏,如果不快点行动,火山爆发后至少半个小时的唠唠叨叨那就够呛了。三下两下衣服穿好了,胡乱吃了一碗干饭,就背着一个彩色编织条编的背筐,和提着纸盒箱子的爸爸一起来到石坝上等候班车。
天还蒙蒙亮,四周黑魆魆的,青蛙也次第鼓噪着,水田里还散发着未干的稻草的腐烂味儿。从石坝边吹来一阵凉风,让八月底的清晨有了秋天的味道。
父女俩在一个叫加明的地方下了车。加明是泸州和隆昌县接壤之处,中间只隔了一座名为界牌的大山。山连绵起伏,巍巍峻峭,怪石嶙峋,树木茂密,杂草丛生,白雾缠绕着半山腰,云蒸雾霭的山顶只有天空放晴方能见庐山真面目。濑溪河像一个勇士从半山腰的缺口奔腾而出,呼啸着来到山下,便似宁静的少女舞着曼妙的舞姿,在和风细雨中襟飘带舞,逶迤前行。山下一马平川,阡陌交错,袅袅炊烟的村庄点缀着碧绿的田野,大大小小的工厂依偎着高高的河岸。望着高高烟囱里冒出的浓烟,修竹突然之间感觉到家乡的落后。
界牌山是一个隘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站在山上,望着辽阔的大地,当年沙场秋点兵的盛况如在眼前,击鼓声、喊杀声、马嘶声奔腾而来,不免产生指点江山的豪情壮志。曾经的军事要地,现在驻扎着一支军队,据说军队去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只留守了极少部分的士兵看守军区大院。
泸县师范就坐落在濑溪河旁边,当地人叫它共大,据说这里曾经办过共产主义大学。学校呈长方形布局,坐北朝南。一条水泥路将学校和公路连接了起来,路旁两侧矗立着高大的红樟树。校园是典型的四合院布局,红砖青瓦。
冷修竹在高年级同学的指引下报到注册后,便来到女生院。说是院子,其实就是一幢有两层楼的筒子楼,加上一条通往厕所的水泥道。筒子楼红砖青瓦,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产物。楼道两面是房间,人就从楼道中间的巷道出入。底楼阴暗潮湿,常年散发着霉味,二楼也就是顶楼夏热冬冷。在学生上课的间隙,筒子楼便是老鼠的乐园,是老鼠的天地,它们肆意嬉戏玩耍,寻找食物撕咬衣物。特别是在学生放假时,它们可以在床铺上纸箱里寻偶做爱,繁衍后代。
爸爸让冷修竹去水管处接了一桶水回来,便拿起扫把去挽屋顶上的蜘蛛网,顺便把全间屋子长满霉的白生生的床架子打扫起来。然后选了一张上铺,麻利地铺上棕垫和草席,挂上蚊帐。冷修竹靠着对铺的床柱子,看着爸爸忙碌着,自己却不知道从何帮忙。爸爸侧着脸望了她一下,笑笑问她:“要不你来干?”她摆摆头,笑着说:“还是你干吧!我看着也是幸福啊!”
冷修竹看着水泥地板上积满了水的小坑,埋怨道:“这么潮湿的屋子怎么住人啊!不得风湿病才怪!”
爸爸望望地面,叹息一声说起来:“唉——没办法,不过比我们当年强,当年我们住瓦房,下雨天啦经常就是端着水盆在床铺上接屋顶上漏下来的水……开学后,跟体育老师商量商量,提两桶石灰来放在床下,屋子就没有那么潮湿了。另外不要把装满水的桶放在床下,屋子也尽量不打湿。唉——”
叹息一声开头,叹息一声结束。
爸爸转回头挂蚊帐,双膝跪在床铺上,伸长手臂将蚊帐的顶绷直,试了几次失败后,放下右手握成拳头,不断敲击着后背。她突然发现爸爸的背已经不再笔直了,难道爸爸已不再年轻了?凑近一看,爸爸的头上已经出现了白发,清癯的脸颊上眼角有好几道很深的皱纹。她不禁叫道:“爸爸……”爸爸转过身子,双眼询问着她,她忙说没什么没什么。
待放置好箱子整理好被子枕头后,爸爸跳下床,拍拍手,望着她正经道:“新的人生开始了,还是那句话,你在学校要学会吹拉弹唱琴棋书画,像万金油一般,以后才能胜任学校的每一个工作岗位。你要自己好好照顾自己,我还得赶回去晒谷草。”说罢就离开宿舍,冷修竹追出来,只看见了爸爸清瘦的背影,泪水就包在眼眶里了,哽咽着叫不出声儿。
校园里有无数高大的红樟树,它们郁郁葱葱,遮天蔽日,枝干相互交错,树叶儿伸出小小的头,绿得发亮。火辣辣的阳光炙烤着大地,树梢将它们接收,给了校园一片阴凉。耐不住酷热的蝉也次第鸣叫起来,将静寂的校园着实喧闹了一番。
冷修竹踩着透过树梢斜射下来的光斑,漫步在清静的校园,甚是惬意。来到实验楼下的池塘边,池边的橘子树慵懒地伸展着枝条,累累果子压弯了树枝。荷叶圆圆,荷叶绿绿,遮天蔽日。清风徐来,荷叶像是被一只温柔的手臂爱抚过,泛起一层柔柔的绿波,徐徐的,从一端到另一端,轻轻起伏,连绵不断。那绿波不似松涛排山倒海的呼啸,不似风荡春花娇媚生姿,有的只是无声无息的轻轻摇曳。似一段深情的绿韵,像一首无言的情歌,是只有风荷才能奏出的“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雅韵。
荷叶间闪现着朵朵荷花,或含羞待放,或初绽笑脸。绿叶红花交相辉映,蜻蜓在叶上盘旋飞翔,在花蕊上驻足观望。
小鱼儿轻轻划过一道水纹,还没有让冷修竹看清楚它们的影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圈一圈的波纹微微荡漾开来,看来鱼儿真不少,冷修竹蹲下身子,坐在靠近水池的石阶上,手脚探入水中,盼望着有一两只鱼儿游过。
滑滑的,凉凉的,一只在她的脚尖上划过,另一只轻抚着她的指头儿,红红的小嘴一张一翕,鼓着双眼看看这粗壮的荷茎。几只鱼儿过来了,一群过来了,它们追逐着,嬉戏着,游弋着,挠得冷修竹的手脚痒痒的。这些金黄、绯红的金鱼让她那么喜欢,她不敢动一动,怕惊扰了它们的欢乐,惊扰了它们的美梦,直到它们累了,倦了,寻找别的乐园了,她才收回自己。
沿着弯曲的石板路,来到了音乐楼。白色的墙砖在阳光下那么耀眼,崭新的楼房与古色古香的校园不能相映成趣,好像老祖母怀里抱着的新生婴儿。楼房一共三层,每层前前后后共二三十间琴房。透过沾满灰尘的玻璃往小鸽子屋一瞧,从门到窗是六步,从窗到门也是六步,破旧的风琴靠着墙壁,缺胳膊少腿的木头凳子独自躺在风琴下方,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琴房外是一片坡地,坡地上种满了橘子树桔子树,树下的枯草在秋风中摇曳着。树叶儿墨绿,桔子橘子大小均匀,它们挂满了树梢。冷修竹站在树下,闭了眼,眼前仿佛是一个天高云淡皓月当空的夜晚,满树的红灯笼照耀了琴房,在曼妙的乐曲声里,一群学生从琴房飘然而出,他们来到树下,载歌载舞……
梅晓风和她爸推开了门,“吱呀”一声将冷修竹惊醒。她睁开蒙眬的双眼,看见了一个清丽的女生,扎着高高的马尾,一脸的阳光一脸的灿烂,漂亮的鹅蛋型脸上嘟着的樱桃小嘴微笑着,那眼睛啊!简直就是一汪清泉,一汪流动的清泉。明目皓齿,眉清目秀,再看那身材,高挑匀称,亭亭玉立。她穿着一套海军服,白上衣蓝色短裙,蓝色宽幅衣领上两根白条尤为显出她的瘦削。不由得看看自己的红衬衣黑长裤,相比之下就老土了,便自嘲地笑笑,若无其事地望着窗外走廊上来来往往的学生。
年轻人都爱美,特别是年轻的女孩儿,看着美的事物养眼养心。她们对视着,前一分钟还是陌生人,相互打量间,眼里就交流着彼此对对方的第一感受,刚才还生硬的光束在几个回合后就柔和下来,会意的一笑让年轻的心近了。
梅爸爸忙着张罗床铺,梅晓风将画夹递给爸爸,便提着桶走出屋子,动作麻利,像一阵风一样。冷修竹望着他们父女俩,心里拿自家爸爸和梅晓风爸爸比较着,他们显然有很多地方不一样,虽然年龄差不多,衣着上差别不大,俩人的精神劲儿可不同,此君沐浴着阳光般灿烂,彼君承受着生活的压力眉眼不展。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一话跃入耳际,忙打住了比较进行时。
梅晓风爸爸忙完后交待两句就离开了,她将纸箱里的衣服重新折叠起来,看看冷修竹,笑笑,说:“我是梅晓风,你呢?”
“哦——我?冷修竹。”
“呵呵。日暮歌碧云,天寒思修竹。”
“我们没有学过这句诗吧?”
“我爸爸国画上的题词。”
“经常背诵?”
“嗯——”
在冷修竹不断的“佩服”声中,她们聊起了自己原来的学校和同学,口无遮拦地说起了路上的见闻和自己的家人。
寝室在底楼,加上很久没有住人了,到处散发出一股霉味。寝室里还空着几间床铺,其他同学还没有到来。冷修竹想打扫一下屋子,梅晓风不屑地说:“不打扫,人没有到齐,打扫也白搭。”冷修竹只好作罢。
冷修竹提议去街上买脸盆,梅晓风也有东西要买,说话间就冒着烈日去街上了。她们没有打太阳伞,没有防紫外线的意识,在家晒谷子时间比这长很多都不用戴草帽,更何况这点太阳。
梅晓风拉着冷修竹,这个店铺介绍介绍,那种物品解说解说,俨然是个本地通。街不大,就一条主街,全是泥石路,顶着大太阳在街上走一圈,不久就大汗淋漓。肚子感觉饿了,她们就在紧挨河边的一家面馆要了肉丝面,全然不顾女孩儿的斯文,狼吞虎咽起来,几大箸就进肚子了。
她们来到桥头,只见汹涌的河水从上游咆哮而来。梅晓风说:“这河叫濑溪河,上游是隆昌的古月湖,遇上古月湖泄洪时,加明就要被淹,现在你看这河水大吧,这不是泄洪,是前几天下了雨,涨水了。平时它可是温柔宁静的少女,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懂吧?”
桥是石拱桥,中间一大孔,两肩上各挑两个小孔,典型的赵州桥结构。桥是进出泸州的必经之路,多少出泸州上隆昌上成都的车都经过此处。
冷修竹看了看表,已经两点过了,她们就慢慢走回学校。路过书店,看见了墙壁铁丝上挂的胶纸张贴画,梅晓风嚷着喜欢周海媚和潘虹,就挑选了她们的画,冷修竹买了山口百惠和林青霞的。画上的四个美女都是大头像,没有风景,只有笑容可掬的脸和娇媚的上身。山口百惠和林青霞是含蓄的笑,宛若人间仙子;周海媚和潘虹是甜蜜的笑,就像邻家小姑娘。在刚刚时兴追星的年代,这样的人头画是大凡爱美的大姑娘小伙子都要张贴在自己房间的。
她们拿着卷好的画,敲着路旁的稻穗,信步走在回去的道路上。来时走的是石子公路,回时走田埂小路。路两旁的稻子发散出的清香让她们除了感觉一阵阵的热浪外,还再次感受到家乡田野的味道,冷修竹不由得想起了爸妈,眼眶渐渐湿润起来。
回到寝室,见到了陆陆续续到来的同学,王秀玲坐在床上,边梳头边和冷修竹打招呼,见冷修竹不怎么热情,只好撇撇嘴收住了笑容。宋雪梅双手搭在床沿上,低头望着地面,双脚在水泥地上蹭来蹭去。着粉色连衣裙的李琼,双手抱在胸前,忧忧愁愁的,倚靠着床柱子望着窗外。
梅晓风和冷修竹爬上床铺,把画张贴在蚊帐中间,寝室门“哐嘡”一声开了,进来一个满头大汗的女生。她将木箱扔到屋子中间,就坐上去喘着粗气,扬起手掌,左右开弓,硬是在闷热的寝室里扇起了风。上铺的两个女生盯着她,直到她将灯草席一扬扔到对面空铺去。
她望望大家,笑笑,说道:“我叫刘大燕,你们不妨自报家门吧!”参差不齐的报名声在李琼望着窗外冷冷的一声李琼中结束了。
下午五点半洗澡,六点开饭,七点上自习。大家在家里都自由散漫惯了,这一下要遵守作息时间就得马不停蹄地行动了。
洗澡让冷修竹为难了,她没有在集体澡堂洗过澡,那么多年轻的身体在一起肯定要相互打量,虽然早有心理准备,还是感觉难为情。就是那次录取师范生体检时,女医生让几十个女生把衣服脱了,胆儿大的女生照着她说的办,但是很多女生还是扭扭捏捏不脱衣服,大家相互觑着。直到医生大骂开了,大家才不情愿地褪去外衣,又在医生的大骂之后才褪去内衣。大家都低着头,不敢看别人的身体。医生拿着长尺子扳着女生的身体,从正面一个一个盯着检查。漫长的等待在医生的一句“穿上衣服”中结束,大家迫不及待地扯过桌上的凳上的衣服,埋着头飞快地穿起来。这件事儿大家回家后都不好意思给好朋友提起,生怕别人取笑自己。
女生二寝室七个女生早早地提上水桶去食堂锅炉房排队,待水装满后直奔澡堂。路程不远,但是单手提水还是很吃力的,总得歇两次才能提到。四处搜寻角落,期望能找到一个不易被别人看见的地方。天如人愿,时间尚早,来的人还不多,冷修竹和梅晓风她们俩就在澡堂最里面的角落找到了落脚之地。褪去身上的衣服,慌慌张张地将洗澡水浇到身上,香皂一抹,泡沫还没揉搓出来,赶快冲洗干净。简直就是逃之夭夭。
出得澡堂,两个都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快步跑向寝室,端着饭碗就去食堂打饭。稀饭馒头,还行!稀饭,夏天农村天天吃;馒头就是稀罕物了,难逢难月吃上一次,今天至少得吃上三个馒头过过瘾。冷修竹吃第一个馒头时简直就是狼吞虎咽,根本没有吃出啥味儿,吃第二个时才慢慢下咽,品出了点点甜味儿。梅晓风在旁边扯着嘴角,不断说注意形象注意形象,冷修竹抬头瞪着她,没好气地问她怎么不吃,她指指馒头上的黄块儿,解释碱太重了不好吃,冷修竹伸手拿过她手里的馒头,嘀咕着:“穷讲究!你不吃我吃。”梅晓风啧啧几声佩服佩服,便喝起稀饭来。
一脸的汗水,一脸的新奇,女生二寝室七个女生浩浩荡荡前往教室。
教学楼前原来是一块农田,后来改作乒乓球场。为了便于雨天行走,学校将田中分,垒起了一个工工整整的高高的水泥十字架,十字架贯穿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教学楼依然是红砖青瓦,一共是三层,每层四间教室。教室紧靠着院墙的北面,教室外长长的巷道是面向南方,楼下是一字溜的乒乓台。底楼是三年级,越往上年级越低。学生们在一间教室里一坐就要坐三年。
到得楼前,只见底楼、二楼的栏杆前整整齐齐扑满了男生,白衬衣白体恤们在欣赏着新来的马尾辫们,指指点点,不时发出不怀好意的笑声。所以但凡是新生入校的日子,他们定不会放弃这样大好的日子。他们吹着口哨,伴随着“哇塞”声声,让再勇敢的女生也不敢迎着他们的眼睛前行。对于只能低着头快步往前走的女孩子,男生们由远及近地检阅着她们,不时伴以评论,女孩子们只能三三两两硬着头皮,一路嘀咕着穿越火线,到达三楼早就气喘吁吁了。
冷修竹她们几个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一节粉笔头从天而降,刚好砸到冷修竹的眼睛上,她“啊”的一声赶紧蒙着自己的眼睛,梅晓风见状,瞪着楼上的男生,大声骂道:“哪个干的缺德事?”楼上男生“喔——喔——喔——”齐声叫着,根本没有人理睬梅晓风的骂声,气得她气不打一处来。她跺着脚骂道:“那么怂啊!你们家没有女人啊!欺负女生算什么本事!”白衬衣白体恤们叫得更起劲儿了,一个洪亮的声音出来了——你们男生在干嘛?回教室去!别欺生!这下二楼上安静了,梅晓风安慰着冷修竹上了三楼。
教室静极了。大家三五个挨着坐下,静默着,都不想在这陌生的环境里大吵大闹给他人不好的印象,空气由此凝固下来。冷修竹伤心地望着窗外,不时揉揉眼睛,责怪自己怎么那么倒霉啊,开学第一天就遇到这样的事,这些高年级男生不知道以后还要怎么捉弄这些低年级女生,简直不敢往下想。梅晓风在她旁边坐下,嘴里还在喋喋不休地骂着那群男生,这让冷修竹内心稍微好受一点,有同学能在自己受窘时两肋插刀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水田就在楼下,稍远一点是濑溪河,是公路,是远山。话说登高可以望远,这高瞻远瞩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真让人心情舒畅,刚才还埋怨教室不该在三楼的她于是就非常感谢命运之神让她读八九级,非常感谢学校领导英明的抉择——一年级住三楼,一住就三年。
班主任老师来了,一个鲁迅般的先生来了。整齐的偏分头,脸色黝黑,八字须,步履轻快。他环视了一下大家,感觉气氛凝重,就手托下巴,爽朗地笑了起来,八字须在大笑中展成了标准的一字须。待大家都露出笑脸后,他介绍自己后就开始讲师范学习的重要性——也许三年以后你们出去教小学,但是还是有可能教初中高中,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大家是可以志存高远的。
老师清清嗓子,语气严肃起来,说道:“我对你们是充满期待的,但是也得将学校的纪律向大家开诚布公。一是得遵守学校作息时间,如起床、吃饭、学习;二则得遵守学校纪律,不能打架斗殴;三则,当然说到后面的越发重要……”
他停顿了下来,望着大家。大家也抬起头,望着他,期待着他的越发重要的话语。
“那就是——不能谈恋爱……”
教室里出现了一阵气息漩涡,五十五名学生张着嘴巴想发出“喔——”却不敢发出只能转化为气流。七个横排的气息在教室半空中结合,缠绕,升腾,再逸到窗外。片刻,大家低下头,抿着嘴笑笑,可能好多人心中不屑起来——谁要谈啊!
冷修竹扬起上眼睑,眼珠子往上微微抬抬,看到了老师环视大家后的偷笑。老师摸摸八字须,“哼——哼——”了两声,就让大家自我介绍。
老师要求大家按照位置用普通话依次介绍,这可让冷修竹为难了。她是从小学到初中从来没有用普通话回答过问题的,心理紧张得不行了,脸涨得绯红,手也开始发抖。听到前面有的同学流利的话语,她更紧张了。有几个男生说了川普话,老师笑笑,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四川人说普通话。”同学们哈哈大笑起来,教室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轮到一个男生了,他低着头,无论怎样也开不了口,老师一次一次鼓励他还是不能开口,老师只好摇着头说:“今天宽待你,你可以用四川话。今天是第一次,就特殊点,以后慢慢练习,这普通话是你们必须要练就的。”就像听到特赦令一样,他轻松地介绍了自己。冷修竹想:已有先例,有前者不能没有跟者,先糊弄过关再说。接着有好几个同学也这样介绍,轮到冷修竹时,她就平静了许多,“我是冷修竹……”。标准的四川泸州话一出,就只见她迫不及待地坐下。咚,咚,咚,心房剧烈地跳动着,后面同学的介绍她一个也没有听进去,只顾着双手来回摩挲。
漫长的课堂似乎永远也不结束,只有等待,等待,等待……
晚自习下课铃声一响,学生们从每间教室蜂拥而出,口哨声、呼朋唤友声,此起彼伏,宁静的校园顿时沸腾起来。晚风习习,冷修竹梅晓风跑步回寝室,再到筒子楼两端大门仅有的水龙头处洗脸刷牙。大家都一窝蜂地拥挤着,都想早一点洗漱完毕,以免九点半学生会干部来检查寝室纪律时被扣分。
静校号拉响了,灯光熄灭。厕所里慢慢儿人少了,舒舒服服解决了内急,把牢底坐穿的精神让她们在吃喝拉撒的一大难题上胜利了一次。
拐过一道女儿墙进入筒子楼,冷修竹看见一间寝室的门上着了锁,她扯了一下走在前面的梅晓风,梅晓风停下脚步,顺着冷修竹手指的方向看去,见到了一扇紧闭的木门,一把锈迹斑斑的锁耷拉在门扣上。
“这间屋子没有人住吗?”冷修竹问道。
“不知道——”梅晓风一脸茫然。
“会不会——”冷修竹抬头望着寝室番号“117”,面露狐疑。
“管它的!”梅晓风不屑一顾地回答。
“会不会——”面露狐疑的继续猜疑着。
“别乱猜!”梅晓风略有一丝丝紧张的语气回答。
说别乱猜,可是两人的脚步都加快了!逃也似的跑回寝室。寝室空气异常闷热,小小屋子住着七个人,连一把电扇也没有。大家嘴里骂着学校不关心学生疾苦,身体享受着筒子楼的闷热,勤快的同学摇起了纸扇,不勤快的四仰八叉,等着从小窗流进的一丝丝凉风,起先把蚊帐放下的同学也撩起了蚊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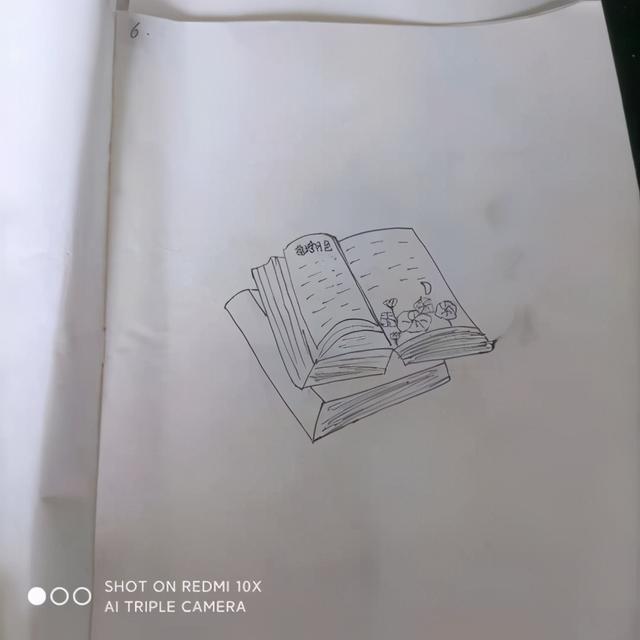
第一节是由班主任老师兼任的文选课,老师还没到来,大家已经拿出书本预习起来。看得入神时,老师轻轻说:“见你们在看书,我不打扰你们,稍事休息,今天我们学习《荷塘月色》。”咦,老师们平时都板着一张脸进教室,“上课”“起立”“同学们好”“老师好”中国式的课堂前奏曲,今天没有,代之以亲切关爱式,让大家着实温暖了一番。
《荷塘月色》不是第一课,但是老师提前上,肯定是因为这篇文章很美。老师为大家泛读了文章,在讲台周围边走边读,完全沉浸在自我陶醉的状态中。然后为大家讲到了“通感”,再赏析蛙鸣一句,他讲道:“据有关研究者说清华近春园的荷塘没有青蛙的……”据说——对名家名篇的研究大家们用了“据说”一词来介绍,看来真实情况就有疑问的。这是冷修竹第一次在课堂上听说,原来的课堂上老师的介绍、讲解都很肯定,就像数学上“1+1=2”一样是千真万确的,毫无疑问可言。相比较而言,文选老师的课让她有点点感觉大家风范。
课间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阴暗的天空下,朦朦的细雨连成一片,如花针,如细丝,飘落在树叶上、小草上、屋檐上。晶莹透亮的小水滴从瓦槽上滴落下来,宛如千万条银色的瀑布,宛如丝线抚摸庭院中的琴弦发出的呢喃。凉风从窗户的缝隙中钻了进来,带着雨丝,带着泥土的气息,扑进了每个人的心田。远处教师宿舍楼上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迎光则微明,背光则幽黯,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雨越下越大,敲着鳞鳞千瓣的瓦,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
“冷修竹,快出来,看看戴望舒的《雨巷》。”梅晓风呼唤着。
“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 ……”梦幻般的轻吟声里,冷修竹看见一位撑着红纸伞的着天蓝色长裙长发飘飘的丁香姑娘,默默彳亍着,冷漠,凄清,又惆怅。她独自漫步在悠长的寂寥的雨巷。滴答、滴答、滴答,雨声伴着丁香消逝了……
在开学的第一天,冷修竹逢着了戴望舒梦中痴痴以求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唯美的画面便定格在她的脑海里。
上午最后一节是音乐课。音乐课要到音乐阶梯教室去上,阶梯教室在实验楼的底楼,宽大,能坐两三百人。冷修竹她们一跨进音乐室的门就惊呆了,原来丁香姑娘就是音乐老师啊!琴声响起,教室一下子就安静下来。教师示意大家翻开音乐书封面,进入眼帘的是校歌,大家默念着:“经历风雨云霞,桃李开遍天下……培育英才,振兴华夏。看,在我们辛勤双手下,开出满园鲜花,开出满园鲜花。”
随着老师的琴声,大家哼着简谱,唱着歌词,园丁培育花朵仿佛就在眼前,三年后在讲坛传播知识的图景也展现在眼前。
眼眶湿润,热血沸腾。
端着饭碗,冷修竹想到了“117”,便拉着梅晓风回筒子楼。到达筒子楼,却胆怯地朝走廊尽头望去,梅晓风嘟哝着:“就知道你想干嘛!”
冷修竹笑笑,停下了脚步。梅晓风摇摇头,叹息道:“又狐疑再三了,前怕狼后怕虎的!想看,我陪你去就是,你这个人啊——”
说完就昂首前去,冷修竹亦步亦趋跟着前行。
梅晓风将饭碗背在身后,贴着门缝往里看。昏暗的筒子楼深处传来一个声音——看什么看?有啥好看的!
吓得梅晓风饭碗掉在地下,再看冷修竹时,只见她拔腿就向有亮光的厕所跑。
“冷修竹,等等我!”梅晓风顾不得掉在地上的瓷碗,跟着奔跑而去。
站在台阶上,两人喘着粗气,一个一句“吓死我了,妈呀”。
冷修竹问道:“刚才是哪个吼的?”
“不知道——”梅晓风捂着胸口回答。
冷修竹胆胆怯怯地问道:“不会是鬼吧?这大白天的,怪吓人的!”
“哪里有鬼!走,我们去看看,是哪个让我们八魂儿丢了七魂儿!”梅晓风可不给冷修竹思考的机会,拉着她就往筒子楼走去。
阳光稍强的地方,脚步走得剔剔挞挞的。越往里走,楼道越昏暗,脚步便慌乱起来。随着一道道关锁的木门往身后移动,心怦怦怦跳得越来越厉害,脚步随之加快起来,逃也似的跑到操场。
两人弓着身子,互相望着,眼里交流的是“遇着鬼了吧”。